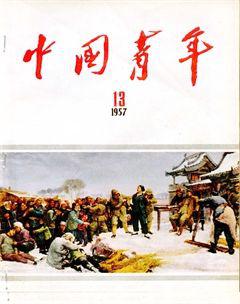美,到哪兒去找?
于果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魯迅
現在我們還可以生動地回想起來,我們過去是怎樣受了革命文藝作品的啟發和教育,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們不能不懷著感激的心情,想起在解放前,像“鐵流”和“毀滅”這樣的文藝作品,在我們的革命隊伍中所起的巨大影響;而廣大的青年,在解放后,也正是通過團組織的介紹和推薦,通過文藝作品里面的保爾·柯察金,馬特洛索夫,劉胡蘭,吳運鐸這些英雄形象,更快地接近了黨,接近了革命的。我們青年團的各級組織,已經愈來愈重視運用文藝作品向青年進行思想教育這個工作了。
但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了,我們開始面臨著一個新的形勢,而文學藝術領域內百花齊放方針的提出,要求我們必須用更審慎、更細致的態度和方法對待文藝工作。今天的情況是:舞臺上百戲雜陳,圖書館里中外古今的作品紛然并列,在青年面前突然開放了一個新的非常廣闊的天地,他們所接觸到的已經不再只有革命文藝這一種了。同時,人們對文藝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希望閱讀和欣賞到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比較更強一些的作品;也希望團的各級組織進一步加強對青年的文藝閱讀和文藝欣賞的指導工作,使他們從文藝作品中受到更深刻的教育。
過去的成績是不容抹煞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指出,在運用文藝作品向青年進行思想教育的工作中,在對青年的文藝閱讀和文藝欣賞的指導工作上,我們對文學藝術的教育作用的理解是比較狹隘的,我們對文學藝術本身所具有的特點是重視得很不夠的,而我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是比較簡單、粗糙的。這樣,實際上也就給青年帶來了相當有害的影響,使他們不善于正確地對待各種文藝作品,而弄得眼界十分狹窄,趣味非常偏枯,甚至形成了一種急功近利的,比較膚淺庸俗的審美觀。
文藝從屬于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但在具體的作品中,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往往不是那么直接地顯露出來,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在為一定的具體的政治斗爭任務服務,都是在宣傳某一項具體的政策。我們常常聽人說起,過去在革命根據地的時候,做民運工作的干部怎樣懂得發動群眾,一個支援前線動員參軍的中心任務來了,往往就會有人提出:演個戲吧!這樣,問題就解決了。這種情形在當時自然是可能的,但卻不一定所有的文藝作品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完成這樣一種任務。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實際上是多方面的,是曲折、復雜的。文藝和科學一樣,都是生活和現實的反映,不同之處在于科學用概念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文藝卻總是通過個別的、具體感性的形象,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來加深人們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對于任何事物,人除了實用的需要外,還有審美的需要。所以別林斯基說:在這兒,藝術和科學是同樣不可缺的,科學不能代替藝術,藝術也不能代替科學,高爾基還說過:“人按其本性就是藝術家。他隨時隨地都竭力想使自己的生活美麗。他想要不再作那種只是吃吃喝喝,然后就無意識地、半機械地生產子女的動物。”所以,文藝的根本作用,是教人認識生活,是加深人們對生活的理解,是豐富和提高人們的精神世界。法國亨利·列裴伏爾在“美學概論”一書里,曾這樣闡述:
按照馬克思的著名的說法,藝術,在某種意義上講乃是人給予自己的最大的喜悅。藝術高度地表現出人對自己本身的創造。藝術就是喜悅(即某種比滿意、愉快、精神上的樂趣更有意義的東西)。藝術過去和現在都使人擺脫限制和束縛他們的羈絆。藝術過去和現在都提出人類崇高的理想——值得仿效的典型、范例。
所以,不應該忽視文學藝術的特點,而把文藝作品的教育作用簡單化。
但是,過去當我們運用文藝作品向青年進行思想教育的時候,卻往往把文藝作品的教育作用簡單化了。我們實際上忽視了經常的文藝閱讀和文藝欣賞的輔導,特別是忽視了審美教育。向青年介紹和推薦文藝作品,我們也總是力求配合當前的政治運動;這種作法當然不能否定,而且有時還是必要的,但問題在當我們介紹和推薦之際,往往不能從具體作品的具體分析出發,進行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評價,而是枝枝節節,只抽出一點,生搬硬套。例如在貫徹婚姻法運動中,“中國青年”曾向讀者介紹了六篇“關于婚姻問題的短篇小說”,告訴青年說:“在這些生動的小說中,人們可以具體地看到:封建婚姻制度是怎樣不合理。……另外,我們在這些小說中,看到許多自由結婚的夫妻,生活是多么愉快,……‘結婚的主人公——田春生和楊小青就是如此。他們是自由戀愛的,相親相愛,有著共同的理想。就在約定在區上領結婚登記證的那天,春生為了抓特務,小青為了給旁人接生,誤了約定碰頭的時間,本來雙方互不知道這些事,
但一經說明,不但不生氣了,而且更增進了他們的愛情。這充分表現了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的優越性。”(見一九五三年第五期“中國青年”:“介紹幾本有關婚姻法的書”)強調作品中的某一問題結合其種實際情況來教育青年,自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僅僅抓住一點,勉強借題發揮,實際上往往就會把文藝作品原有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弄得簡單化,甚至庸俗化了。就這樣,還來不及細細品味,咀嚼,很多優秀作品一陣風似地流行過去了,而很多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并不很高明的作品,也可能夤緣時會,忽然不脛而走,盛行一時。閱讀某種文藝作品,既然往往只是一時的風尚,這就使得有些青年對著文藝作品,總要不斷地追問:這本書對我們有什么現實的教育意義?它對我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幫助?這樣,如果學生認為只有“三個穿灰大衣的人”這本小說才對他們“有現實的教育意義”,而商業工作人員必須從“我們切身的事業”這本小說中來了解“國家商業工作人員工作的意義、重要性和那些值得歌頌的事”,這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青年中間,像這樣一些論調:“‘水滸的英雄,只不過是劫富濟貧,沒有什么直接的教育意義”,“魯迅的作品以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過時了,對現在的學習和工作沒有什么用處”,“‘普通一兵也沒有什么用處,因為現在已經沒有戰爭,將來我也不想當戰斗員”……等等,實在不是偶然出現的。
“如果賈寶玉是正面人物,請問,叫我們向賈寶玉到底學習什么呢?”這樣的問題也并不可笑,因為這正是我們幾年來沒有恰如其分地運用文藝作品向青年進行教育的結果。例子俯拾即是。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的“中國青年,”在答讀者問中,就曾這樣說明“究竟為什么要推薦‘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道:“文學作品的職責就在于表現現實中先進人物的性格,來教育人民、教育青年,從而培養和促進這種性格的成長和發展。從這一點看來,這篇小說是可以盡這樣一種職責的。”顯然,對文學作品的職責這種比較狹隘的理解,是相當普遍的。但文學作品的職責,果然就這么簡單嗎?難怪在“我們向娜斯嘉學習什么”這個問題下,只好羅列這樣可以加在任何文學作品任何英雄人物身上的五個條條了:一,相信真理,堅持真理;二,嫉惡如仇,斗爭到底;三,沉著勇敢,不驕不傲,不計個人得失;四,深入群眾,為群眾服務;五,相信黨,依靠黨,走黨的路線……。(見1956年第2期“中國青年”;“讀‘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對于文藝作品這種簡單、機械的解釋,事實上已漸漸引起很多青年讀者的困惑。當他們涉獵了更多的文學作品,他們就不能不提出了懷疑。最近,何其芳同志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得很好:“曾有人要求我們的文學描寫出一些值得大家仿效的正面人物來。這是文學可以而且應該負擔的一種任務。但如果以為文學的教育作用就只有這樣一個方面,那就太狹窄了。歌頌先進的人物先進的生活,揭露消極的不合理的事物,以至抒寫作者個人的情感,只要寫的好,都是可以教育人的。別林斯基論普希金的詩的時候,曾經說他的情感里永遠有一些特別高貴的、溫和的、柔情的、馥郁的、優雅的東西,因此在教育青年人,培養青年人的感情方面,閱讀他的作品特別有益。在把文學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理解得很狹隘的人看來,這也許很像一個新聞。然而這卻是事實。”(見“文學研究”第二期:“回憶、探索和希望”)
在指導青年閱讀和欣賞文藝作品時,空洞的說教多,具體的分析少,這也是當前的通病。流行在報刊上的很多文藝批評,對作品往往是不從具體內容的具體分析入手,而是玩弄概念,從抽象到抽象;并且常常用一定的條條框框去硬套,做出簡單的,枯燥、干疥的論斷。有個中學生曾這樣形容她的文學教師對白居易的詩的講解:“這首詩,在描寫方面有非凡的藝術性;在語言方面有鮮明的形象性;在結構方面有嚴密的邏輯性;在具體的比喻上有充分的科學性……總之,他的詩是他那個時代特點的具體反映,里面有高度的現實性,人民性,概括性,還有獨創性……”(見6月8日北京日報第三版:“笑不出來”)這恐怕不是什么笑話,而是實有的情形。我們常常會碰到一些大學里中文系的畢業生也有這樣的情況,他們讀了不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的文藝批評論文,但卻不大涉獵具體的文學作品,雖然談起美學來似乎頭頭是道,可是往往不從具體作品的實際內容出發。我們經常會碰到諸如此類的問題:這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這是哪一階級的典型形象?這個作品說明了什么社會本質?它的主題是正確的嗎?等等。這些問題當然可以提出,但成問題的是,青年讀者滿腦袋裝的往往只是這樣一些名詞和術語,他們有那么一套一成不變的條條和框框,他們所滿足的也只是這樣一堆概念。在文藝作品面前,他們幾乎是還沒有打開書,就已急急忙忙尋找結論,只要勉強可以套上去,就從此心安理得,不再繼續探索了。
文藝批評中那種對待作品的法官式的判決,流風所及,也給了青年很大的影響。往往一篇作品發表后,首先投書給報刊提出抗議的,正是一些天真的青年讀者。“難道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嗎?”“難道我們的英雄就是這樣的嗎?”他們對作者總是動輒責難,對作者的“歪曲了生活”、“歪曲了英雄形象”表示十分憤慨。例子也是俯拾即是的。一個二十一歲的業余作者寫了一個以“姻緣”為題的短篇小說(見1956年第2期“遼寧文藝”),雖然這不過是一篇短短的習作,但發表后立刻引起很多讀者的紛紛批評,除了指責“小說所反映的是非本質的現象”外,還宣判了作者的三條罪狀:一,破壞工農聯盟;二,宣傅城鄉對立;三,散播迷信思想。實際上這篇小說只寫了一個安心農業生產的農村姑娘,不肯盲目流入城市,而愛上了另一個也安心農業生產的農村小伙子罷了。爭論既然已達半年,迫得沈陽作協不能不召開“關于‘姻緣及其批評的座談會”(1956年12月3日遼寧日報),問題才算告一段落。在評論作品時首先從文藝創作上的一般理論原則來對照作品,如是否創作了正面人物,是否描
寫了矛盾沖突,而不從作品實際出發,不對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正是過去一般文藝批評的特征,而這樣的文藝批評,恰恰助長了一些青年對待文藝作品的簡單、粗暴的傾向。
文學藝術的創造過程,本來是一個形象思維的過程,藝術家一般總是采取著自己獨特的途徑,用不同于科學家的方法,來反映生活和現實,并且總是力求把非常豐富的,生動活潑的生活本身,以充滿對新鮮事物的感覺,具體而飽滿地再現出來。在現實中,生活是完整的東西;在文學藝術中,也必然要求以渾然一體的形象,集中地再現出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一切色彩,音響,光澤。作家當然要在作品中表現一定的主題思想,但是這個主題思想,往往是寄托在作品的形象整體中,作品每一個細節,都起伏著作者思想的呼吸,整個作品是一個有生命的整體。文藝正是通過這樣的藝術形象,來啟發人們的美感,從美感上對讀者進行教育的。這種教育,全憑藝術上的感染力量,所以它只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往往不可能獲得立竿見影、馬到成功的效果。文藝作品最忌斷章取義,因為藝術形象不能割裂開來,加以肢解。抽出作品的一枝一節,進行枯燥乏味的說教,是最殺風景的事;因為這等于揮動無情的斧斤,把藝術家辛辛苦苦塑造出來的一片完整天地,砍成一塊一塊碎片。這樣,實際上是破壞了作為藝術作品對讀者所激發出來的美的情緒,破壞了藝術作品所飽含著的詩意,也破壞了作品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別林斯基就曾說過:“有人以為,指出一部藝術創作的基本思想何在,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這種人是錯了;這是件困難的事,這是只有那種與思想能力結合起來的深刻的審美感才能作到的事。……詩的思想——這不是三段論法,不是定理,不是規則,這是活的情感,是澎湃的熱情。”所以,在引導青年進行文藝閱讀和文藝欣賞時,必須充分估計文藝本身的特點,小心翼翼地探索那些藝術形象的意義。“說藝術只表現人們的感情,也是同樣不正確的。不,它表現他們的感情,也表現他們的思想,然而,并不是抽象地,而是借著活生生的形象來表現的。”(普列哈諾夫:“論藝術”)不從活生生的形象出發,只憑幾條空洞的原則尋找一些空洞的結論,是徒勞無功,反而有害的。
優秀的文藝作品具有勾魂攝魄的藝術魅力,對青年的思想感情有著強烈的影響,但是必須反對魯莽滅裂的作法,反對狹隘地理解文藝作品的教育作用同時,必須經常對青年進行審美教育,培養他們的藝術趣味,擴大他們的知識領域。共青團的各級組織應當注意文藝的特點,善于運用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來豐富和提高青年們的內心生活,讓他們真正能夠從中外古今各種文藝作品那里,汲取到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精神力量和戰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