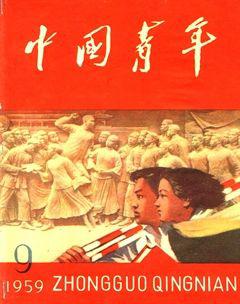回憶“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轉變
一、流亡法國,接觸社會主義思潮從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運動止,這是一段艱難困苦的斗爭歲月。當時,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革命黨的組織陷于土崩瓦解,中國天空上滿布著黑暗的陰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著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為革命后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制獨裁;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蠶食和鯨吞;不是統一、富強,而是軍閥們的爭權奪利、魚肉人民。
1913年七月,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廣東、四川等地的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反袁起義。我們深悔從前未能堅持建立革命政權,而把政權輕易地讓給袁世凱,現在不得不在力量懸殊的情形下起來作斗爭。我們還想憑著勇氣和熱情來挽救流產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義各軍準備不足,心志不齊, 又未及時號召民眾起來反對袁氏違法亂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軍事行動上,結果在袁世凱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起義好像曇花一現而失敗。僅存在南方幾省內的一點革命軍事力量也被摧折殆盡。
起義失敗后,我還留在上海。我并不認為革命從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凱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想隱蔽在上海,繼續為革命做一點工作。但是袁世凱并沒有放過我,指名說我是四川重慶熊克武反袁起義的策動人,對我下了通緝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腳。于1913年十一月亡命法國。
我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兩年多,思想上非常苦悶。“中華民國”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國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樣糟糕,革命愛國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軍閥攆到了外國,革命失敗得真是再慘痛不過了。我時時刻刻惦念著中國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會再一次迅速地燃燒起來,把丑惡的軍閥統治燒個干干凈凈。1914年春季我沒有人學,癡心指望著很快地能再有一個回國參加斗爭的時機。但是過了半年,國內沒有一點革命發動的跡象,而且哀世凱還修改了民元約汝,解散了國民黨以及國會,擔任了終身大總統,許多北洋派爪牙也紛紛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來袁世凱氣焰囂張,不可一世,我的歸國希望暫時也不能實現,于是決心先埋頭讀書。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時,決心要學一門科學,選的是電氣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學畢業,考入第六高等學校,邊學習邊作革命工作,1911年畢業,未入大學即回國參加辛亥革命。我原來學的是工程技術,但由于國事日非,只得經常從事革命活動,深深感到“所學非所用”,于是進了巴黎法科大學,改學政治經濟學。
亡命巴黎的兩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觸了不少人物,長了不少見識。這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交戰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彼此瘋狂地屠殺,整個歐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個大屠宰場。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已暴露無遺。同時,社會主義思潮風起云涌,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流派,盛行一時。1903年我在日本東京曾經讀過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感到這種學說很新鮮,不過那時候一面在學校緊張地學習,一面著重做革命的實際活動,對這種學說也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放過去了。這時,又重新看到這種學說,感到格外親切。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里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的美麗遠景。這個遠景雖然是美麗的,但是如何能夠突現它?我們當前應該做些什么?我仍舊是茫然的。我曾經和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談起這些問題,李石曾認為:“我們只要搞教育,宣傳互助、合作,傳播這種美麗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別人就好了。至于總統、皇帝及其他官職和議員,讓人家去當沒有關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說:“教育、宣傳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組織工作也要做,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團結和培養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總統,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魯巴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我從以往的革命實踐中感到這種不要組織革命團體的主張根本是行不通的。僅僅有一個美麗的理想,而沒有一套實現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國雖然接觸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流派,但是它們并沒有給我指明一條拯救中國的光明大道。
二、軍閥腐朽統治的一個實例
1914年以后,中國的政局發生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趁著歐洲大戰的機會出兵山東,并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而接受了這些條件,秘密地簽了字。1915年底袁世凱假弄公民投票,強奸民意,而公然稱帝,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時候,反對他的各種社會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來。191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護國軍首先起義,各地紛紛響應,袁世凱的皇冠不久就滾落在塵埃里。1916年六月六日,這個竊國大盜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活活地氣死了。
袁世凱統治垮臺,對我的通緝令自然失效。隨后,南北和議達成,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我就和蔡元培一起從法國回國,1917年二月我到達北京。我到北京有一個任務,因為歐洲大戰開始以后,法國人力不足,需要大招華工,袁世凱政府和法國訂立了一個關于招募華工的條約,內容對中國工人非常不利,經手人粱士詒從中撈了很多踐,根本不顧工人的利益。這時候我們已在法國組織了華法教育會,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到法國去的大批華工中進行教育,并希望國內貧苦學生能出來留學,還組織了勤工儉學會。由于袁世凱政府與法國所訂的條約對工人很不利,我們出來力爭,費了很大周折,與法國改訂條約。規定中國工人和法國工人同工同酬,總算為工人們爭回了一些權利。我就攜帶這個條約草案回國,要求北京政府批準。
回到北京一看,中國的政治局勢還像從前一樣。袁世凱雖然死了,但是北洋軍閥繼承著袁氏的衣缽,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開了爭權奪利的斗爭。政府中貪污腐敗風氣,依然如故。華工新約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個月還沒有批準的信息。
有一天,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來訪問我,他問我:“聽說你帶回一個招募華工赴法的條約,批準了沒有?”我說:“還沒有批準。”接著我詳細地給他解釋了這個條約比前一個條約要好的多。他說:“你沒有在北京住過嗎?你是學生嗎?真是迂夫子!這里的事,非錢不行。如果有錢,再壞的條約也能批準。如果沒有錢,再好的條約也批不準。你這種事至少可以賺幾百萬,你就是拿一二百萬出來也不算什么?”我說:“我們就是為了反對賺工人的血汗錢,才辛辛苦苦爭回了一些權利。我們沒有錢,不但不愿拿錢去運動,就是人家拿錢來運動我也不行!”說著說著兩個人就大吵起來。他臨走時說“你執拗得很,讓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這個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長派來的。在軍閥官僚統冶下,什么好事也辦不成,不鏟除軍閥統治和官僚制度,中國決無得救的希望,這是對我的一次嚴重教訓,我立志要和惡勢力斗一斗。當時我沒有任何其他辦法,還幻想通過個人關系去說服外交部長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個同盟會員,總不會和貪污官僚一樣。他身為外交部長,是會有批準條約的權力的。那里知道:官僚機構,重重疊疊,相互牽制,伍廷芳雖然答應批準條約,可是外交部內上上下下的官僚們都想撈一點油水,仍舊拖延不動,事情就這樣拖下去,沒有得到結果。
我這時一面在交涉條約的事情,一面又進行第二個任務,就是辦留法勤工儉學,設立了一個留法預備學校,同時又給四川同事去信請他們也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分會。1918年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傳到了湖南以后,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潮。我們希望在這個動亂的環境中能夠培養出一些人才。但是這時我目睹國內的混亂和腐敗,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證明,在軍閥統治下,連教育工作也不會讓你安定地做下去。這時北洋軍閥正在進行爭權奪利的斗爭,總統黎元洪和國會議員站在一邊,背后有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多數省份的督軍站在另一邊,背后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之間圍繞著對德宣戰問題,展開了勾心斗角。段祺瑞嗾使督軍團包圍國會,脅迫黎元洪一定要通過對德參戰案,以便借此機會,大借外債,擴充實力;黎元洪為了對抗段祺瑞,勾引頑固派張勛進京。其實張勛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六月張助進了北京,就搞了一出“宣統復辟”的丑劇。當時,北京城內,兵荒馬亂,到處搶掠捉人,凡是與辛亥革命稍有點關系的人都紛紛避難出京,我也只得暫時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隨后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復共和”為名,趕走張勛,獨攪政權。這時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民元約法”被軍閥完全撕毀了。南方為了護法,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成立了軍政府,于是出現了南北兩個政府對立的局面。
三“南與北一丘之貉”
1917年七月,伍廷芳和海軍部長程壁光率領海軍南下,孫中山先生也到了廣州,主張“護法”,在廣州組織軍政府,非常國會選孫中山為大元帥,聯合廣東、廣西、云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對抗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1917年底熊克武驅逐了劉存厚,統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參加軍政府,我于1918年二月到廣州見了中山先生,隨即又回北京把所負華法教育會的工作進行了交代,六月才去廣州任職。原來軍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滇系軍閥的力量,我們當時以為滇桂軍閥與北洋軍閥有矛盾,可以利用他們來為革命服務,而且他們實力較小,不像北洋軍閥那樣跋扈難制,有可能團結他們,使他們服從中山先生的領導。不久就證明:這種想法是十分錯誤的。軍政府成立后,野心勃勃的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軍閥勾結,并且跟我們大鬧幕后磨擦。軍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終于被排擠,1918年五月由廣州回到上海。他在辭職通電中痛斥桂系軍閥說:“南與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這時真是傷心忿恨到極點了。
當1918年六月我再到廣州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已經到上海去了。七月間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為七總裁之一,我當時曾到上海勸中山先生就職,他未同意,我又勸他可派代表去應付,他答應了。我們當時仍想團結各方面的力量來抵制桂系,以圖補救大局于萬一。我們所能團結的力量有南下的國會議員和海軍,有各省軍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部隊——陳炯明所統率的粵軍,還有廣東的一些地方派人軍。桂系特別把陳炯明部視祝作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消滅它,陳炯明部被迫退駐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粵,情形很危險。這時軍政府內部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我們揭露桂系和北洋軍閥勾結的事實,反對桂系排擠粵軍,極力保全陳炯明部。在會議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學系政客爭吵起來。桂系軍閥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換我的代表職務,到了1919年他們策劃成南北和議時,我就不再當代表了。
參加護法,使我十分深刻地體會到中山先生所說“南與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們當時苦心孤詣所要保全的陳炯明又何嘗不是與南北軍閥同屬“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后,陳炯明利用國民黨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驅逐桂系,重返廣州,并且隨后又背叛了中山先生。這個叛徒要知道當時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們又如何竭力保護他,他真應該慚愧而死。在當時軍隊是私人的財產和工具,軍隊的活動完全聽命于他們的統帥,不知道有國家民族,我們也沒有可能去根本改造舊軍隊,使它成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個人的作用,力圖爭取有實力的統帥。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了推翻清朝而遷就袁世凱,后來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后來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陳炯明,最后陳炯明又叛變了。這樣看來,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們是我們應該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這是藏在我們心中的迫切問題,這些問題時刻攪擾著我,使我十分煩悶和苦惱。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剛發生的時候,1918年我在廣州,由于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封鎖消息,我們還不知道俄國已發生了一個開辟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偉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長期被封鎖住的,后來我就讀到了約翰·里德寫的“震動寰球的十日”,這本書對十月革命的過程描寫得很生動。通過這本書,我了解到我們北方鄰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個工農政府,偉大的俄國人民已經擺脫了剝削制度,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從前我在法國接觸了社會主義各種思想流派,深深為社會主義理想所吸引。今天這個理想居然在一個大國內開始實現了,心中感到無限興奮和鼓舞。1919年,我資助幾個學生到蘇聯去學習,希望他們能為中國帶來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來聯系中斷了。直到1920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維舟同志,他本來在四川軍隊中工作,由于四川軍內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參與,便交出了所率領的軍隊,到蘇聯去工作和學習了一年,1920年八月間,他回到北京,對我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蘇聯的狀況,使我對這個新起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當時蘇聯正處在國內革命戰爭的困難時期,物質非常缺乏。王維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東安市場召集許多青年學生,開了一個“俄災救援會”,向各方募捐,一下子就捐募到幾萬元錢,買了許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來王維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幾萬元。那時候中國人民對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來支持蘇聯,所以我們的募捐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發生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的時候,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參加和會。大家希望可以通過巴黎和會,收回日本在山東所占奪的權利。美國總統威爾遜也發表了花言巧語的“十四條”,其中也有主張民族自決的詞句,偽裝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慘遭遇。當時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大多抱著幻想。可是和會上帝國主義的弱肉強食,毫無公理和陰謀欺詐等等,再一次地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民。日本帝國主義蠻橫地堅持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和我賣國賊訂定的一切條件,偽善的美帝國主義不僅幫著日本說話,反怪中國何以在山東問題上有“‘欣然同意”的簽字,以逃避他的責任。結果,和會決議:德國在山東權利一概讓與日本。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卻得到“戰敗國”的待遇。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消息傳來,全國憤激。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首先發生了愛國示威運動,懲罰了賣國賊,各地紛起響應。雄偉的工人和學生的隊伍走上了街頭,全國范國內激揚起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浪潮,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席卷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沖激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蘇了,開始散發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動腐朽的惡勢力,都顯得那樣猥瑣渺小,搖搖欲墜。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總是看著上層的軍官、政客、議員,以為這些人掌握著權力,千方百計運動這些人來贊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眾運動的對比下,上層的社會力量顯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眾中所蘊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驚天動地、無堅不摧的。特別是一向被人輕視的工人群眾也發出了怒吼,像上海那樣的大都市,六月五日開始一聲罷工、罷市令下,整個城市的繁華綺麗頓時變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于九日免去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官職。工人階級的奮起,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動派于死命的偉大生力軍。這時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革命的性質完全不同了。
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生一種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
五、新道路的起腳點
1919年,我被西南軍閥排擠,退出軍政府,十月底回到四川。就在這一年,我讀到了一本日文叫“過激派”(日本對布爾什維克的惡意的稱呼)的書。
人讀一本新書,通常總是根據自己過去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經驗來吸收新書中的內容,作出判斷和選擇。所以同樣一本書對于不同環境中不同的個人,往往會發生不同的影響。當時中國革命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革命實踐的發展使我日益明確地感覺到舊民主主義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遠動的發生給我啟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徑。我渴望了解蘇聯革命的經驗,“過激派”這本書,恰恰滿足了我的需要。我反復地閱讀它,結合著自己過去的經歷,深深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作了一次詳細的批判和總結。我體會最深刻的有以下四點:
第一、工人和農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用辛勤的勞動哺育了整個社會。但是他們自己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世世代代過著貧困的生活。而地主、資本家,游手好閑、不事勞動者,卻過著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這些人絕跡?布爾什維克主張“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擁護這個主張。的確,對于這些社會上的寄生蟲,一定要強迫他們去勞動,讓他們“自食其力”,社會才能夠安定和繁榮。
第二、布爾什維克認為: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工人階級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夠得到解放。這個道理在從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從前雖然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于極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為了要解救民眾的苦難,但是總以為革命只能依靠少數知識分子職業革命家,沒有看到廣大人民中所蘊藏的偉大革命潛力。經過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權,經過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發揮了沖擊舊制度的偉大力量。在國際和國內的新形勢下,讀了這本書,深深感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識分子和軍人中進行活動,恰恰是沒有把下層民眾動員、組織起來。所以革命顯得軟弱無力,反動派一且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要改變辦法,革命新辦法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依靠下層民眾。
第三、我從前讀無政府主義的著作,覺得他們不要組織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年聽到孫小山先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黨員要有絕對服從的義務,不能自由行動,組織手續很嚴格,入黨時還要按手指印。我覺得他的辦法比無政府主義強的多,但是黨員入黨時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點舊式會黨的氣味。究竟怎樣才好呢?我始終抱著疑問。布爾什維克主張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一個堅強的、有紀律的、有戰斗力的共產黨,作為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革命隊伍。這個主張使我多年以來所未能解決的疑團,渙然冰釋。
第四、辛亥革命時,我們對掌握政權和改造國家機器太不注意了,當時為了遷就袁世凱而讓出了政權。有些人(如宋教仁)還幻想用議會斗爭的方式來控制住舊的國家機器,結果反動派就能夠利用現成的政權和舊國家機器向我們進攻。布爾什維克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工人階級在革命中必須粉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才能夠鞏固革命的勝利。這正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像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相傳下來的以官僚制度為核心的舊國家機器,是許多罪惡的根源,其勢力根深蒂固,即使經歷許多次的革命風暴,但在官僚國家的蔭庇下,萬惡勢力仍會死灰復燃。以往我也常想這個問題,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個道理。布爾什維克關于政權和國家的理論,解決了我的問題。
我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就是在這些問題上有了一點新的體會。這些體會當然是很籠統膚淺的,但卻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腳點。說起來真是可憐,我那時渴望能夠看到一本馬克思或者列寧的著作,但是我東奔西跑,忙于應付事變,完整的馬列主義的書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從一些報刊雜志上零星地看一點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那時候,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還是不多的,階級觀點也不明確,還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社會各階級。我當時只是認為:重要的是要把這些知識貫徹到行動中去,身體力行,為革命做一點貢獻。
六、利用“自治”講臺做宣傳工作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運動”的朝流,給我提供了初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會。“自治運動”是怎么回事呢?原來當時的政治局勢是十分混亂的,在全國范圍內,是北洋政府和廣州政府南北對峙的局面;在北洋政府內部有皖系、直系、奉系的對立;在廣州政府內部有革命派和滇系、桂系軍閥的對立;甚至一省之內也有許多小軍閥割據稱雄。當時北洋派大軍閥以“武力統一”為名,攻打南方各省,發生連年混戰的局面,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人民生活,極為痛苦,特別是湖南省受戰禍最慘。段祺瑞的爪牙張敬堯作了督軍,橫行霸道,連小學都封了。因此,湖南群眾起來組織了驅張運動,逐走了這個蟊賊,出現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謂“自治”,就是由本省人制定省憲,選舉省長,管理本省事務。這種主張當然不是挽救中國危亡的根本辦法,因為當時人民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結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層分子壓迫本省的下層人民,但在北洋軍閥“武力統一”的叫囂聲中,它卻不失為是抵制北洋軍閥的一個有效武器。由于當時人民群眾對北洋軍閥最為痛恨,因此這個反對北洋大軍閥的“自治”口號,受到人民群眾一定程度的支持。當時各省參加運動的人很復雜,有馬克思主義者,有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有資產階級,但也有為保全并擴充自己地盤的地方軍閥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后不久,“自治”潮流就卷進了四川。當時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亂,1920年二月,屬于國民黨的四川省長楊庶堪及謝持等為了爭奪權力,聯合了滇軍、黔軍,攻打同屬于國民黨的督軍熊克武,熊敗退至保寧。下半年熊克武又聯合舊川軍劉湘、楊森等部進行反攻,驅逐楊庶堪等。勝利后熊發表了解除四川督軍職務的通電,經協商后分為三軍,以但懋辛、劉湘、劉成勛為一、二、三軍軍長,協同維持川局,使局面暫時安定下來。劉湘及其所屬的楊森各抱野心,隨時企圖奪得全省政權,主要是反對熊克武,四川全省弄得各軍面從心違,四分五裂,動蕩不安。北洋軍閥的軍隊這晨駐扎在陜南、鄂西,注視著四川的形勢,隨時準備大舉入川。在這種具體形勢下,“自治”就變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來統一全省以反對北軍入川的政治運動。
我對于四川“自治”的態度是:不同意把“自治”當作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但是在當時具體形勢下,應該抱贊助態度,并積極參加這個運動。因為:第一、“自治”可以抵制北洋軍閥,也有利于制止本省的混戰,創造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第二、“自治運動”提供了向人民進行宣傳教育的機會,不應該拒絕這個機會,應該利用它把群眾的覺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參加這個運動,那末,地方軍閥就會去控制這個運動,使運動成為他們達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運動中對于地方軍閥一定要進行揭露和斗爭1920年底,我們開始了組織活動,1921年四月一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聯合會”,一百多個縣每縣都有一、二個代表來參加,我們通過這個組織系統,了解了四川各縣的許多情況。我也借著這樣一個公開的講臺,開始宣傅馬克思主義,經常寫文章,做講演。“全川自治聯合會”的宣言和十二條綱領就是由我起草的。其中以“建設平民政治、改造社會經濟”為總目標,強調民主政治以反對軍閥專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對社會寄生蟲;提出“民眾武裝”以反對軍閥武裝;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農生活。十二條綱領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權”、“編練民軍”、“保障人權”、“普及教育”、“公平負擔”、“發展實業”、“組織協社(即合作社)”、“強迫勞動”、“制定保工法律”、“設立勞動機關”、“組織職業團體”等,每一條綱領都詳加解釋,許多觀點開始擺脫了舊的束縛,初步反映了馬克思、列寧的一些主張。這個宣言和綱領曾經登載在當時創刊的“新蜀報”上,各縣進步青年看了,十分歡迎。我從前許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見解變得更新奇了。
我通過這個自治機構,初步傳播了一些進步思想。大會開幕時,全省人心振奮,可容千余人的重慶商會大禮堂,座無虛席,門窗外還有許多人佇立而聽,許多人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盛會。可是會開不過十多天,劉湘、楊森就企圖收買自治聯合會,以作為他們的御用民意機關,自治聯合會中的成員本來就很復雜,有些卑鄙的人已經被他們收買。我覺察到這種情況后,就把大家發言擁護自治、起草省憲的意見作成決議通過,并宣布“我們聯合會的宗旨是促成省憲,不能代替民選的省議會,我們大家已決議實行自治,起革省憲,任務已經完成,至于起草省憲的權力應該交給省議會”。這個意見得到多數人的贊同,于是就把起草省憲之權移交給省議會,而把自治聯合會解散了。我當時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省議會還在國民黨多數的控制下,還不至被反動軍閥隨意操縱。軍閥劉湘、楊森費了很多心機,用了許多錢收買代表,結果仍舊是人財兩空。他們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輯我。
四川“自治運動”本身,并無成效可言,但這個運動卻使我有了一個面對廣大人民講話的機會,使我把新近體會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傾吐于廣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熱烈的反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收獲。而且通過“自治”的失敗,使我又有了兩個教訓:第一是進一步體會到在軍閥統治下毫無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國,必須首先用武裝的革命來推翻封建軍閥統治。第二是自治聯合會那種地域性的臨時的組織極容易為敵人破壞,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革命的戰斗的組織來領導革命。這時候我心里非常強烈地要求組織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的政黨。其實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我遠在被封鎖的四川,并不知道。
全川自治聯合會解散后,我就到成都把制省憲任務交給省議會,然后到南充、綏定等地講演,1922年初我又到了成都。
七、整頓成都高師,組織工人農民
1922年夏,成都高等師范學校鬧風潮,校長去職,學生和當局請我擔任高師校長,我義不容辭地擔任了這個職務。我在校內進一步展開了宣傳和組織活動。
我費了很大力量來辦這個學校,從前學校中紀律非常松弛,課程內容也陳腐不堪。我到校以后,采取革新的措施,聘請了許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來擔任教師,并加強學校紀律,扭轉了散漫的風氣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習,對教帥和學生的學習、生活盡力關心照顧。經過一番整頓,學校面貌大大改觀,師生員工團結得很緊密,樹立了一種嶄新的學風。同學們有秩序,有朝氣,追求知識,孜孜不倦,議論政治,意氣渙發,成都高師成了進步勢力的大本營。
五四以來,四川省的新文化運動很快地就開展起來。除了成都高師學生創辦的“星期日”等刊物進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許多外地的新書報也紛紛傳入,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惲代英等都曾到四川進行宣傳活動,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隨著形勢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會老會員的身份,盡可能地推進新思潮的擴展,除了在校內工作外,并利用個人與四川上層社會的歷史關系,為革命同志作掩護。如1922年,惲代英同志在瀘州被川軍賴心輝部所扣押,我知道后就打電報去瀘州,保釋代英同志,并請他到成都高師任教將近一年,惲代英同志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他在成都高師期間,把馬克思主義的宜傳活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在這時,我們還派人深入到工人和農民中去做宣傳和組織工作。成都市有一個兵工廠,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內還有許多分散的絲織工人,我們派學生去分片聯系,組織工會,發動罷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鄉村的農民中,也有學生去進行活動,組織農會。當時成都經常發生罷工事件,我的一個老朋友跟我開玩笑地說:“只要把吳玉章捉來殺了,罷工就不會發生了。”的確,當時四川的一些軍閥對我很頭痛,但是因為我和同盟會、國民黨的歷史關系,更因為當時群眾偉大力量的支持,反動派也奈何我不得。
當宣傳和組織工作開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以后,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也就愈來愈迫切。這時成都高師內已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我當時年已四十四歲,當然不能參加,于是與楊暗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組織了“中國青年共產黨”,作為領導革命斗爭的機構,并發行“赤心評論”,作為機關報。由于四川地處僻遠,一直到這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也不知道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即將開始了。
八、參加中國共產黨
1923年,劉湘、楊森勾結吳佩孚進攻四川,1924年一月楊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師,我就交卸離校。當時“五一”勞動節快要來到了,我們一些人懷著興奮的心情籌備一次盛大的紀念會,許多青年人通過工會組織在工人中做了許多宣傳鼓動工作,紀念大會一切都巳準備就緒。突然,四月二十九日,有人告訴駐在成都的軍閥楊森,說“五一”紀念會是吳玉章的“陰謀”,要組織工人、農民和學生推翻楊森,奪取政權。第二天,成都市內實行戒嚴,空氣非常緊張,楊森的軍隊紛紛從各地調回成都,我們預定的會址“少城公園”也被軍隊看守起來了,并且揚言要捉拿吳玉章。
在這緊張的時刻,成都工人階級表現了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精神,他們不顧反動軍隊的武裝威脅,仍在公園內召開了紀念大會。我當日本欲參加大會,由于同志們力阻,未能親身參加;近郊農民也被反動軍隊阻止,未能入城會師。
“五一”事件以后,我在成都立不住腳了,隨即離成都和劉伯承同志一起離開四川,取道貴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國工人運動的浪潮洶涌彭湃,國共合作已經開始,廣州革命政府日益鞏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無比的興奮鼓舞。當時孫中山先生為召開國民會議的事已赴北京。我也于1925年二月趕到北京去。本擬見中山先生,他國病重不能接見,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后,見到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負責人之一趙世炎同志,才了解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和活動情況,我就在這時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寫信去四川,要楊暗公同志等把“中國青年共產黨”取消,個別地參加中國共產黨。
我入黨的那年已經四十六歲,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進。從我少年時代聽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起,就為國家的憂患而痛苦、而焦慮、而奔走;我們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尋找一條出路。許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為此而獻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運動以前,還沒有找到一條光明出路。感謝十月革命,它的萬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們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武器一經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立即發揮出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在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我才能夠通過自己的具體歷程完成個人思想上的革命轉變,參加了共產黨,從一個民主革命者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這四十年國際國內的歷史,生動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和生氣勃勃。現在國際形勢方面,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大踏步地奔向共產主義的前程;在國內方面,社會主義建設正在一日千里地躍進,偉大的祖國日益強大,日益繁榮了。讓我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斗旗幟吧!它已經引導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它正在引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并將引導我們走向建設共產主義的更加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