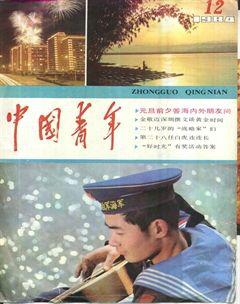大后方
楊益言 劉德彬
正在這時(shí),忽聽一聲喝叫:“讓開點(diǎn)!”林濤側(cè)目斜視,只見幾個(gè)憲兵掮著皮箱在人叢中開路,后面一群人趾高氣揚(yáng),通過憲兵、別動(dòng)隊(duì)的警戒線進(jìn)入機(jī)場(chǎng),向停機(jī)坪走去。其中,有幾個(gè)穿著筆挺的西裝、蓄著仁丹胡子的日本人,還有幾個(gè)身著黃呢軍裝,披著大氅的達(dá)官貴人。其中一個(gè)穿凡爾丁中山服,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瘦矮子,突然離開了這支特別隊(duì)伍,后退兩步,凝視著林濤正要招呼的來人。幾個(gè)正在巡邏的憲兵突然也在這人身前身后停住了腳步。林濤要迎接的那位中年人對(duì)這突然的變化象看在了眼里,又象根本沒有看見似的,還是邁著剛才那種穩(wěn)健持重的步伐,默默地走著。瘦矮子挾了挾眼鏡,揚(yáng)了揚(yáng)手杖,忽然高興地歡叫道:“Hel1o(哈羅)Dr華(華博士)。”來人側(cè)過頭來,瞬間臉上露出了驚詫的神色,隨之竟三兩步迎上前去,抱住了對(duì)方瘦矮、用襯肩墊得很高的肩頭:“想不到,多年不見,今日能在此相逢,真是幸會(huì)。老同學(xué),今非昔比,榮耀高升啦!”
林濤不覺一怔。此刻,林濤和這兩位久別重逢的交談?wù)咧g,僅距數(shù)步之遙。林濤對(duì)來人和瘦矮子的談話不僅聽得十分清楚,而且,從來人向他投來的目光中清楚地看出了要他鎮(zhèn)靜、耐心等候的示意。林濤強(qiáng)自按捺住猛烈狂跳的心,遙望著那些優(yōu)先進(jìn)入機(jī)艙的當(dāng)今權(quán)貴們,同時(shí)用眼睛的余光看見瘦矮子把一張雪白的名片遞給了來人。來人接過名片,立刻高興地念道:“重慶大學(xué)秘書長(zhǎng)柏森?這就是你呀,改名了。”瘦矮子笑道:“Dr華,你可還是豐采依舊,豪情似昔喲!哈哈!”隨著,又壓低了聲音:“前幾年,聽說您到華北去了……”來人笑道:“鄙人東西漂泊,一事無成,說來慚愧!所堪告慰者,不過是賤體粗健罷了。”瘦矮子立刻緊挽住來人的手臂,懇切地說道:“當(dāng)茲世事多難之秋,我倒想有一言奉告:老兄何苦再在他鄉(xiāng)飄零?何不就在此間結(jié)廬,為桑梓教育事業(yè)服務(wù),一舒勞頓?老兄才智過人,弟所深知,略展抱負(fù),何愁不能在此創(chuàng)立一番事業(yè)?請(qǐng)千萬不要拒絕家鄉(xiāng)人的殷切希望吧!我馬上搭機(jī)去南京教育部開會(huì),半月內(nèi)準(zhǔn)回,您回鄉(xiāng)省親之后,請(qǐng)一定光臨寒舍,一定!”一名憲兵悄聲伺立在瘦矮子身邊,示意瘦矮子得趕快登機(jī)了。瘦矮子這才放開來人,向停機(jī)坪走去,邊走邊招呼道:“半月后,一定恭候大駕!”
“原來這就是重大秘書長(zhǎng)柏森。”林濤注視著柏森鉆進(jìn)飛機(jī)以后,正要回頭,只見來人早已走過了憲兵、別動(dòng)隊(duì)的警戒線,出現(xiàn)在自己的面前。來人坦然自若的神情,手中提著的準(zhǔn)確無誤的接頭暗號(hào),使林濤很自然地開口說道:“哎,大舅!路上可好?你不認(rèn)得我了?”
“喲,長(zhǎng)這么高了!真是,你不喊大舅,我認(rèn)不出來了。”
來人的答話,更使林濤相信:他正是林胡子要找的人。林濤高興地接過來人的皮包,就向通往河坎的浮橋走去。
他們剛走過浮橋,就聽見嘹亮的軍號(hào)聲響了起來,一群腳登麻耳草鞋、身穿灰布軍衣、腰佩盒子槍的川軍正在整隊(duì)集合。一名青年川軍將領(lǐng),身后跟著兩名弁兵,微露笑容,迎面向他們走來。“這是劉副官,”林濤悄聲向來人介紹了一句:“我們坐他的車進(jìn)城。”軍官停下腳步,向來人招了招手,說:“大舅請(qǐng)上車。”
話音未了,一輛黑轎車已停在跟前。幾十名剛才集合的川軍,早已爬上了另一輛卡車。來人和林濤、劉副官剛坐進(jìn)車?yán)铮I車立即發(fā)動(dòng)起來,緩緩向山城駛?cè)ァD且惠v滿載川軍衛(wèi)隊(duì)的卡車緊緊跟在后面。那些神氣十足嚴(yán)密把守著浮橋兩頭的別動(dòng)隊(duì)員,這時(shí)才回過神來,若有所失地望著這支小小的車隊(duì),緩緩爬上河坎的陡坡,向市區(qū)開去。
在望龍門附近一處僻靜的街口,司機(jī)把車停了下來,來人象完全理解林濤、劉副官的安排似的,無言地緊握了一下林濤的手。劉副官敏捷地打開車門,讓林濤下了車,立刻關(guān)上門,又走開了。林濤一閃身,穿過一條有著百十層石梯的小巷,當(dāng)他再次出現(xiàn)在大街上時(shí),他看見他剛乘坐過的那輛黑色轎車和滿載川軍警衛(wèi)隊(duì)的敞蓬卡車,已經(jīng)繞過小什字,正通過這一段繁華的市街,向上半城駛?cè)ァ?/p>
林濤在人叢中站了一會(huì)兒,確信身邊沒有“尾巴”以后,才從另一條小巷折回下半城,準(zhǔn)備過江到汪山去參加同學(xué)們的郊游。他到了長(zhǎng)江渡口,心中還掛念著那不知來歷的人,他為何而來?又到何處去了?……
離開繁華的市區(qū),那小小的車隊(duì)加快了車速,沿著成渝公路飛駛。但剛轉(zhuǎn)過一個(gè)山灣,車隊(duì)便開始減速,在一片參天大樹蔭蔽之下的一座大院前停了下來。卡車上的士兵,迅速下了車,隱到樹林深處去了。
弁兵開了車門。來人、劉副官走下車來。車邊,是一條濃蔭遮蓋著的光潔的三合土路。路的盡頭,是一座灰色的小樓。劉副官陪著來人向樓房走去,兩個(gè)弁兵在身后緊緊跟著。
繞過一處用松枝編成的屏風(fēng),便是一座經(jīng)過精心布置的花園。光潔的三合土路兩旁,星羅棋布地點(diǎn)綴著一些小小的亭榭、假山、花臺(tái)。灰樓旁的幾棟平房,無疑是廚房和侍從人員的住所。這些小巧玲瓏的房舍,隱藏在一片蔥翠欲滴的芭蕉林和竹林后面,幾乎很難一眼看盡。路旁,沒有一片落葉,沒有一株雜草。四周靜悄悄的。庭園中心,有一個(gè)雅致的噴水池,從那噴口噴出的水花,在陽光的照耀下,五彩繽紛,十分瑰麗。那噴泉口不大,噴射的水也不高,不知是由于山峰巖石和參天大樹的阻攔而形成的共鳴,還是由于別的什么緣故,那水聲竟似激流奔騰般嘹亮。
跨上臺(tái)階,就進(jìn)入了灰樓的正廳。廳里的陳設(shè)無疑是上等的,一色的紅木嵌鑲黑色云母石的大椅子和茶幾上擺設(shè)著精制的茶具、煙具,但這些東西上面落了一層厚厚的塵埃;墻壁上的玻璃框里,嵌著一張主人的放大照片:頭戴大盤圓帽,身穿陸軍上將軍服,目光炯炯地逼視著廳門,但那鏡框四周卻結(jié)滿了蜘蛛網(wǎng)。
劉副官推開一間小客室,等候弁兵奉上煙茶以后,便和弁兵一起退了出去。
來人坐在一張寬大的沙發(fā)上,緩緩地吸燃了煙。象一切謹(jǐn)慎而又經(jīng)驗(yàn)豐富的人一樣,他似乎對(duì)現(xiàn)在置身的復(fù)雜環(huán)境早就有所了解,對(duì)可能出現(xiàn)的一切早就有準(zhǔn)備,一點(diǎn)不用擔(dān)心似的。他把身子向沙發(fā)靠背上一靠,向著空中悠閑地連吐了幾口煙圈。過了一會(huì),門外傳來了腳步聲,房門應(yīng)聲敞開,一個(gè)花白胡須齊胸,手持龍頭拐杖的人,健步進(jìn)入客室。來人緩緩地站起來,迎了上去。花白胡須的老人,丟開拐杖,一下子抱住了對(duì)方:“你來了!怎么也想不到。這里沒有外人,華興文同志,你想得到嗎?說呀!”
來人摘下金絲眼鏡,詳細(xì)看看林胡子的面龐,說:“我當(dāng)然想得到。”
“是組織上告訴你的?”
“不是。”
“那你怎么想得到會(huì)在這里相逢?”
“胡子,你還記得三年前在張家口講過的話嗎?”
林胡子自然記得三年前和華興文分手時(shí)的事。那天夜里,抗日同盟軍的中共地下黨支部,發(fā)現(xiàn)這支隊(duì)伍已經(jīng)被蔣介石、日寇的陰謀徹底破壞以后,支部正在一棟小屋布置撤退的事,不料,小屋被國(guó)民黨特務(wù)包圍了。大家立即拔槍在手,準(zhǔn)備突圍,可是發(fā)現(xiàn)特務(wù)已封鎖了突圍的唯一巷道,情勢(shì)十分險(xiǎn)惡,如果再延誤幾秒鐘,特務(wù)大批涌到,所有參加會(huì)議的同志都沒有生還的可能。正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巷道外突然響起了清脆的槍聲,守在巷口的特務(wù)被迫轉(zhuǎn)身還擊,同志們立即乘機(jī)發(fā)起沖鋒,一齊沖了出去。轉(zhuǎn)過一個(gè)街口,林胡子才發(fā)現(xiàn):在巷道外突然從敵特背后開槍,只身營(yíng)救大家脫險(xiǎn)的不是別人,正是同盟軍作戰(zhàn)參謀、剛從外面返回的華興文同志!接著,他們便在漆黑的夜幕中,各自東西,分別轉(zhuǎn)移了。在暗夜里告別的情景,雖然事隔三年,林胡子仍然記憶猶新。他更清楚地記得,他將轉(zhuǎn)移何方,當(dāng)時(shí)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決不可能向華興文講什么。他決定到四川來,還是一年以后的事。那時(shí),四川中共地下黨遭到了空前嚴(yán)重的破壞,為了站穩(wěn)腳跟,重建組織,上級(jí)黨決定選派一個(gè)和四川黨毫無關(guān)系的同志去四川,這才派了他來。因此,聽到華興文的問話,自然使他驚詫。
華興文卻盯住林胡子的眼睛問道:“你還記得,你說過:‘東方不亮西方亮,離了北方有南方嗎?”
“難道這幾年你走遍了全中國(guó)?”
“那倒沒有。北方,我走過;南方我去過。到了這里,在你進(jìn)門之前,我就聽出來了,那是你特有的腳步聲告訴我的。”
“原來是這樣。”林胡子忙著請(qǐng)對(duì)方重新落坐。
華興文一邊坐下,一邊卻皺起了眉頭,說道:“說真的,你想通了,我可還有點(diǎn)想不通呢!”華興文把眼睛向客廳外掃了一眼,小聲說道:“我不明白,你為什么安排我們?cè)谶@里見面?”
林胡子知道:華興文來渝以后,只接觸過林濤、劉副官。林濤根本不知道這個(gè)地方。因此,不禁反問道:“劉副官給你講過什么沒有?”
“沒有,在車上他什么話也沒給我講過。”
“那你知道這是什么地方?”
“我當(dāng)然知道。”華興文說道:“車子一轉(zhuǎn)進(jìn)這大院,我就發(fā)現(xiàn)了,這庭園,不是三五年能經(jīng)營(yíng)得起來的。中央軍進(jìn)川還不到二年,蔣介石立足未穩(wěn),修不起這樣精美的庭院。它的主人無疑是地方軍閥了。你知道,我也是在山城長(zhǎng)大的,我當(dāng)然熟悉家鄉(xiāng)的環(huán)境。這里離鬧市不遠(yuǎn),轉(zhuǎn)過山口,從樹林中望出去,這庭園對(duì)面的山峰,就是虎頭巖。這小客廳旁邊,布滿塵埃、蛛網(wǎng)的正廳,特別是墻上懸掛的那幅肖像,都證明了這庭院的主人,正是當(dāng)今的西南王、四川第一號(hào)軍閥劉湘!”
“對(duì)!就從這里說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