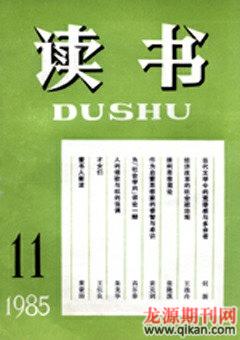讀《傾蓋集》所見
程千帆
近年出版了好幾部值得注意的現代詩歌總集,其中《九葉集》和《傾蓋集》是我所特別重視的。這不但因為詩人們各自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段所表達的特定時代感打動了我的心靈,而且是因為他們的成就同時引起了我對于詩歌發展史上一些問題的思考。《九葉集》的詩人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新詩的表現方式上作了非常可貴的嘗試,他們的確顯示了一些為前此新詩苑中所無的特色;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種特色似乎沒有得到它應該得到的發展,以至于幾十年后,人們還拿朦朧詩當成一個爭論的新話題。至于《傾蓋集》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它是一部現代人以嚴格的古典詩詞格律寫成的作品,卻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九葉集》把新詩的表現方式推向了一個新的更加成熟的階段,而《傾蓋集》則賦與了古典詩歌以新的活力,使它能夠成為詩人們表現今天生活的自如的手段。在這里,我想專門來談一談《傾蓋集》。
時代在變,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也在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的變化往往是復雜的,多面的。我們當然會從現實生活出發去肯定那些新涌現出來的美好事物,從而也產生了新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但不可忽視的是,由于文學本身的實踐,它們也往往會使人們認為已經產生的觀念,有重加審定、估量和改變的必要。五四以來,以古典詩歌的形式反映現代生活是曾經被完全否定過的。其理由,簡單地說,是因為它是用與現代口語有或大或小的距離的文言來寫的,而文言則被認為一定是不適宜于表現現代生活的。但是半個世紀以來的創作實踐卻無法掩蓋這種說法的簡單化和片面性。我們當然不能把毛澤東、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所寫的詩詞作為文學史上一種獨特的因而是例外的情形去處理;即使如此,也無法否認,在近幾十年中,的確還是出現了不少的以古典詩歌形式寫成的佳作。這樣,對古典詩歌形式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似乎就有了可能而且必須加以重新審定的必要。《傾蓋集》的出版也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探討。
本書的出版說明寫道:“古諺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本集九位作者之間,有的是時相過從的朋友,有的是朋友的朋友;他們的年齡、經歷、工作雖各不相同,但是在過去動蕩的年代中,有過共同的憂慮和喜悅,這正是他們把他們近年的若干詩作編成合集,并取名《傾蓋集》的原因。”詩人們共同的憂慮和喜悅是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對社會主義祖國和人民的深切關懷而產生的強烈的愛憎和憂樂。當偉大的祖國和人民遭受著深重的災難、侮辱和損害的時候,他們是憂慮的、痛苦的和悲憤的;而當祖國和人民擺脫了不應當承受的惡劣命運時,他們就無比地歡樂了。當然,詩人們也會寫到自己的私生活,諸如友誼、愛情和愛好,但是這些又莫不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聯結在一起。這是大書在我國歷史上的屈原的哀樂、杜甫的哀樂、陸游的哀樂的繼承和發展。
九位詩人收在這個集子里的作品多少不等,寫作的起迄年代也不相同,但其中的多數都寫于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時期以及其后撥亂反正的幾年當中。詩人們自身的遭遇和祖國人民遭遇的一致性,決定了他們必須而且樂于用自己的筆去反映那個使人永遠無法淡忘的荒唐歲月。那一場所謂“觸及靈魂的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真與假、善與惡、美與丑的殊死斗爭。每一個人,無論他自己愿意或不愿意,自覺或不自覺,都得在歷史舞臺上充當自己所規定的角色。當那些野心家、陰謀家、叛徒們的邪惡勢力壓在祖國母親和她痛愛的兒女們的頭上,要把他們推進無底深淵的時候,廣大人民拿起自己所能拿到的武器起來戰斗了。憤怒出詩人,忠義出詩膽。出于忠義和憤怒,詩人們寫下了許多非常動人的作品。這正是恩格斯所說的“真正藝術家的勇氣”的表現。
詩集中對于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悼念,對于張志新、遇羅克等烈士的哀挽,對于參與丙辰清明悼念活動的廣大人民的贊揚,顯示了詩人們強烈的愛;對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譏刺與鞭撻,以及粉碎四人幫后歡欣鼓舞的情緒,還有對于那些趨炎附勢、“高舉”“緊跟”者流的鄙視,又都表達了詩人們深切的恨。這都是顯而易見的。
我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九位作者原來都在一九五七年那場擴大化了的運動以及其他政治運動中蒙冤受屈,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理所當然地承受了比普通人民更多更重的苦難,千磨萬劫,九死一生。這是當時活生生的現實。然而,他們的靈魂卻從來不因長時間的重壓和扭曲而變形。在極其艱苦的體力勞動中,在備受鄙薄歧視的情況下,仍然在不屈不撓地努力尋求過一種正常人的生活。他們就是這樣生活下來了,并且是不喪失人類尊嚴地生活下來了,一直到恢復名譽。這是奇跡。而這個奇跡之所以能夠出現,則在于他們對于祖國和人民具有無比的愛和無比的信任。他們深信:自己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總有一天會被證明是無辜的。這是極可珍貴的和不可戰勝的愛國主義和樂觀主義感情。
正由于他們是如此地熱愛生活,所以即使在艱難的歲月里,也在從事于詩歌創作。在這些詩作中,幾乎具備了傳統詩歌中一切的題材,重大政治社會生活之外,還廣泛涉及了山水登臨,花鳥題詠,論史論詩,評書評畫,愛情和婚姻,會合與離別。這,似乎都是習見的,然而卻無不浸染了詩人們在特定生活環境當中的特定心情。這就使得《傾蓋集》中的作品具有了鮮明的現代情趣和色彩,與前人此類詩篇有所區別。
以上泛論了這部詩集的主要特色,這是九位詩人所共同具有的。但這些共同具有的特色卻又是通過每一個人自己所獨有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手段表現出來的。風格是個性的外化。如果作者是富有個性的,而其所擁有的藝術手段又能夠表達這種個性,那么,他就必然能夠具有獨特的風格面貌。這絲毫也不排斥對于一切傳統中美好風格的吸收和融鑄。然而,表現在作品里的終究是屬于每個作者自己的新的東西,正如葉老在本集題辭中所說的:“各自擅風神”。
現在試著極其簡略地談一點自己對于每一位詩人和他的作品的體會,無非是管中窺豹,希望不變成佛頭著糞。
王以鑄《城西詩草》:作者精研西方文史,但詩中卻一點也看不見這方面的影響和痕跡,真是不愧老子說的“良賈深藏若虛”。五言古詩這種形式似乎是他所最喜愛的。從《咸寧雜詩》和《飲酒》中,看出他對于陶詩致力很深。陳散原詩云:“陶集沖夷中亢烈,道家儒家出游俠。放翁晚節頗似之,皆奇男子無分別。”龔定庵詩云:“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已無多。”王以鑄心目中的陶淵明乃是這樣的陶淵明,而不只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請看官們千萬記住。
呂劍《青萍結綠軒詩存》:作者新詩寫得很好,寫舊體詩又同樣出色。這使人不禁想起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使人玩味的史實。當初,魯迅、沈尹默、劉半農、聞一多等是寫舊體詩的,后來都改寫新詩;而朱自清、何其芳、金克木以及作者等則原來是以寫新詩見長,后來都改寫舊體詩。這說明這兩種詩歌形式不但無妨并存,而且可以一人兼擅。詩歌中的新舊兩體,如果不被認為是互相促進的,至少也不應當被認為是互相排斥和妨礙的。把一部文學發展史看成是一部文體變遷史,顯然不符合事實,也不能說明問題。呂劍是一位有強烈歷史感的詩人,他的登臨、詠史諸作特別能體現其胸襟的廣闊,使讀者神觀飛越。
宋謀
荒蕪《紙壁齋詩選》:作者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但是并不認識,待相識時,都已經老了。一卷《紙壁齋詩》使人恨相見之晚。其中多著意時局,有元微之所謂“直道當時事”之意,而出之以微文譏刺,則頗似劉夢得、蘇東坡;以七言律詩見長,用筆簡煉而又動蕩,也是劉、蘇遺韻。《伐木》六篇寫大苦難中的窮快活,精神面貌頗為壯麗。贈友諸篇,各如其分,見功力,也見交情。
孫玄常《瓠落齋詩詞鈔》:陳次園贈作者詩云:“玄翁學道指根源,吟詩繪畫妙無前。”這兩句詩足以概括他的成就。其所作詩詞深深地打上了工于書畫的印記。題畫和登臨諸作色澤鮮麗,寄托遙深,如“浮萍身世任西東,慣看關山雪霽夕陽紅。”不愧是情景交融的勝境。雖然遭遇也同樣坎坷,但性情沖澹,少有憤激之詞。題香山紅葉云:“霜紅晚節人間重,莫比三春二月花。”可以移作玄常的自我鑒定。
陳次園《朝徹樓詩詞稿》:作者博學,兼通中外文哲諸科,詩風流美,能備眾體。題畫、論書的篇章與孫玄常可稱難兄難弟。譯詩別開生面。辜鴻銘以后,能以古體譯西詩的人,應該推蘇曼殊,但蘇譯經過章太炎的修飾,古雅有余,風神不足,趕不上陳譯之動人。其所譯的克雷洛夫寓言詩,亦莊亦諧,不愧為辜譯《癡漢騎馬歌》的后勁。《少年游商調》等闋,出色當行,乃是詞中雋品。
陳邇冬《十步廊韻語》:作者故鄉山水甲天下,山川靈秀清峭之氣對他的創作不能沒有影響,所以他的詩詞,明麗奧峭,兼而有之。其詩設想遣詞都擺落凡近。“夜氣
舒蕪《天問樓詩》:作者長期住在一間不見天日的準地下室里,如果借用前人的舊名,自署為活埋庵,倒也合適,他卻偏要自署為夫問樓,這也就是他的人生態度。三十多年當中,舒蕪一直在艱難和酸辛當中打發他的日子,但卻頑強地寫下了一些有價值的著作和美好的詩篇。這恐怕就是莊子所說的“畸于人而侔于天”吧!其詩風出入唐宋,情深采壯,五古、七律更是所長。但是我特別愛好丙辰清明悼周恩來的五律四首,典重深摯,使人讀后很容易想到陳后山所作的司馬溫公挽詩,倍增對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好總理的懷念。其《天問樓圖》是方鴻壽所作,我曾題詩一首,附錄于下:“樓自名天問,庵仍比活埋。青燈戀紅學,熱淚惱寒灰。擢發罪難數,行吟老益才。先王遺廟在,呵壁未須哀。”今年初他才搬出了天問樓,他在那里住了九年。
聶紺弩《咄堂詩》:用傳統觀念看來,作者是詩國中的教外別傳。正由于他能屈刀為鏡,點鐵成金,大膽從事離經叛道的創造,煥發出新異的光采,才使得一些陳陳相因的作品黯然失色。明朝的倪鴻寶也曾做過類似的嘗試。二人雖然同樣具有忠憤之氣,同樣在用一種打破傳統的手法來表現它,可是倪究竟是明朝末年的封建士大夫,他看不到今天這樣廣闊的世界,也放不下和人民保持距離的架子,不敢將人參肉桂牛溲馬勃一鍋煮,所以也不能充分地將當時的現實生活,和從這些生活中產生的奇思妙想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而聶卻較成功地做到了。他的詩初讀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讀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讀則使人感到振奮。這是一位駕著生命之舟同死亡和冤屈在大風大浪中搏斗了幾十年的八十老人的心靈記錄。他的創作態度是真誠的,嚴肅的,而決非開玩笑即以文為戲的。“欲織繁花為錦繡,已傷凍雨過清明。”他雖然是在說蕭紅,實際上也是說自己。他又說:“老欲題詩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我希望紺弩這一顧慮是多余的。前幾年我曾以詩相贈,現也附錄于后:“紺弩霜下杰,幾為刀下鬼。頭皮或斷送,作詩終不悔。艱心出澀語,滑稽亦自偉。因憶倪文貞,翁殆繼其軌。”
“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評賞既畢,有詩為證。詩曰:
大澤窮邊落日黃,疲氓倚耒偶相望。
妙哉逃死九遷客,各自攜歸一錦囊。
袖手孤吟吐光怪,軒眉大笑話荒唐。
崢嶸歲月征詩史,天女修羅共作場。
又曰:
神交豈但同傾蓋,傾蓋論文若有神。
自昔妙才多鑄錯,斷無畸士不相親。
能歌漢道昌皆李,即解儒冠溺亦秦。
元
一九八五年七月寫于南京—連云港
(《傾蓋集》,王以鑄、呂劍、宋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