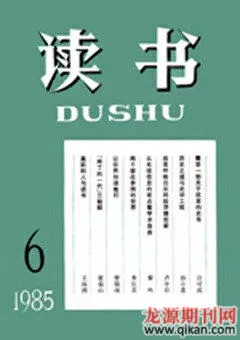東西文化比較研究隨想
葉曉青
前些時候瀏覽了一些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有關論著,不由得具體地想到了一個比較研究者所面臨的困難。當然,對于一個樂觀主義者,問題就成了“比較研究者所需要克服的困難”了。
首先,從事這項工作的基本條件便是學貫中西,他的工作要經得起專攻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兩方面的行家的挑剔。其次,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文化事實上都是多元的,而在進行比較時往往只能把中國(或西方)作為一個整體才便于同另一種文化相比,這樣在技術上很難顧及文化的多元性。例如,當你在比較中國古代和古希臘對科學的不同態度時,你可能會就最一般的特征說,中國人是為人生而求知識,而古希臘人則是為智慧而求知識,但這時也許會有個非常博學的專家對你說,并不盡然,古希臘也有類似中國的科技倫理觀的。文化比較研究中的問題,往往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結論也會多樣化。對比較者來說,從技術上考慮,常需要模糊細節,但這一模糊卻往往經不起挑剔,所以,不容易被認可是研究者遇到的一個真實困難。
第三便是單一文化背景給絕大多數研究者帶來的局限性。不論中國學者還是西方學者都是從自身文化出發去感受、理解對方的文化,因而彼此常常不能準確地理解對方的文化。比如,有的西方史學家對于中國史學家劃定的某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標準就大不以為然,其理由是,辦教育、辦工廠以及去國外留學并不能使人成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把那些從小受到感情壓制、受到父親嚴厲管教而長大后又以這一套管束子女的人叫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未免太過火了。西方史家著重一個人在什么樣的文化背景中成長,以及由此而來的情感、趣味和對生活的態度和方式,而中國史家則取歷史人物成人后所選擇的政治理想與立場。應當說雙方都有道理,在近代中國,民主這個概念是舶來品,以西方標準去看待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生活的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者,自然不會很合乎西人的要求;而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那些希望中國進步,力求改革現狀的人們的確與恪守傳統、拒絕變革的保守派不同(雖然他們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中,他們之間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如果不是以政治立場去劃分就太不公平了,除非根本不承認中國近代有過資產階級,這是中國學者不能接受的。這個例子并不出現在比較研究中,但卻可以用來證明文化間的隔閡是很難逾越和擺脫的。現在西方對東方文明的傾慕和東方(或者說中國)對西方更加倍的熱情,實在都是由自身文化感受出發的,是由自身文化的苦惱而來的。雖然這是那么自然,但為了對民族前途作長遠考慮計,研究者應當站得高些,盡可能擺脫單一文化背景的局限性,這局限不僅表現在知識缺陷上,更表現在選擇的偏激情緒中。
就一般意義而言,對中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是中國人,但也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西方人的某些議論很新鮮,說到了我們自己平時從不注意的事,令我們新鮮的是看問題的視角不同,視角的不同來自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那些我們太習以為常的事,太熟視無睹而不再發生感想的事,其實也并不是當然如此的事,而我們因著文化的力量而并不覺得,這正是自身文化的獨特之處。文化背景的難以擺脫就在于此。一個想擺脫或有意無意認為自己正在擺脫或已經擺脫自身文化背景的人,他的言辭可以是激烈的——在他也以為是真實的,但他仍會不自覺地流露出所反對的東西。當近代民主思想傳入我國后,中國人對此的接受更多出自理論上的選擇,這種選擇多半出自于對中國現狀的憂患、出自由此而來的理智的權衡,甚至也可能出自純屬個人的偶然因素,如某些人激烈的反封建的言論和行動,往往出于一樁不如意的婚姻,象這些選擇由于缺乏相應文化背景的支持,重新退回去也很容易,許多近代人物的趨新趨舊前后迥異似乎使人難于理解——其實正是很自然的事。說這些并非悲觀到認為進步無望,建設新文化的無望,只因為聽到一些同志認為自己可以不受傳統文化背景影響才產生了上述感想。我們大家都認識到封建傳統觀念的有害,但又并不是所有有害的傳統都那么容易被自己所認識、所驅逐,如果冷靜一點,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這樣的經驗,我們常說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習慣勢力太討厭,但我們自己何嘗不受影響,何嘗不曾下意識地用這些去挑剔過別人。我絕對不否認同時代人之中的差別,就象我上面說的應該對近代中國的各色人等作公平劃分一樣,我只是想說要擺脫有害的傳統觀念,首先要意識到傳統文化背景對每個人的影響。不過說這些似乎離開了文化比較研究作為學術的主題,但我們也應看到,比較研究當前在中國之開始為人們所重視,本不單是出于純學術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