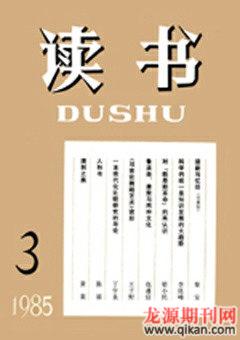傳統與時風 感情與考證
王依民
《李白和他的詩》是一部評傳性的研究專著。
李白是中國詩史上的一座高峰。探討這座高峰的形成原因,是歷來研究者都下過很多功夫的。就探討其中文學本身原因而論,回溯他的傳統就幾乎必然地成了研究的中心課題。事實上,學者們確曾正確地指出了李白所接受的莊子、屈原、漢魏六朝樂府,阮籍、謝靈運、鮑照等的傳統。但是也不必諱言,我們的研究者相對地忽視了當代的文學風氣對李白的影響。針對這種現象,本書著者指出:“對一個作家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當代的文學。甚至專門模仿古典的詩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也由于他當代的風氣。傳統的作品往往也通過當代(或是作品,或是理論)才對作家發生影響。”(13頁)著者將這一原則貫徹于全書,尤其在前二章,詳細研究了與詩人交游的親朋、僧道、官吏——這些人同時又都是詩人——的思想傾向、生活態度、藝術趣味以至遣詞造句的特點對李白的影響。這種觀察角度,不僅特別符合李白的實際情況,而且帶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同西方文學批評的注重將作者置于文藝思潮代興之中相比較,中國傳統批評更注重的是傳統淵源,即使是對文學流派的考察,也更多的注意他們共同的傳統師承,而較少顧及他們之間的平列影響。這樣的批評只能說明一部分問題。在那里,傳統和時風的關系還未能得到恰當的處理。費爾巴哈在批判黑格爾的歷史觀時指出:“自然中的各個發展階段決不是僅僅具有一種歷史的意義:這些發展階段乃是環節,但卻是自然界同時并存的整體的各個環節,并不是一個特殊的、個別的整體的各個環節,個別的整體本身又只是宇宙的一個環節,亦即自然的環節。”(《黑格爾哲學批判》,引自《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文學傳統也不僅僅是從屬和繼承,不僅僅是排他的時間,同時也是寬容的空間,是并列和共存。一時的文學風氣是傳統的特定演變,它既是文學傳統的產物,又是革新文學傳統的產物;作者正是在文學風氣影響下繼承和創造,同時又以自己的努力參與這文學風氣的形成和發展;傳統通過時風發生作用,而時風隨即成為新的傳統。所以,在考慮傳統影響的同時,我們更應充分認識“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作,也總在某種文藝風氣里創作。”“風氣是創作里的潛勢力,是作品的背景”(錢鍾書《舊文四篇》)。這個規律,不但適合李白,也適合一切藝術家,包括“讀書破萬卷”“無一字無來歷”的杜甫這樣自覺繼承傳統的詩人。思想傳統和一時的思想潮流的關系也是如此。
在對于感情的分析和本事的考證之間關系的處理方面,本書也給我們有益的啟示。作為評傳,自然需要很多關于詩人生平和創作的考證,著者在吸收詹瑛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也作了不少精審的考證工作,但在處理“事”與“情”的關系、處理考證與感情的位置時,著者正確地把重點落到對李白內在精神的探索上,而沒有為考證而考證。這種態度在第五、六兩章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如對《蜀道難》的研究(第165至167頁,第185至189頁),除了對關于此詩創作緣起的四種說法進行了詳盡的辯證之外,又進一步指出這首詩“反映了李白對于他生活道路上的種種困難所持的基本態度,也可以說是反映了他的人生觀中重要的一面”,主張同時“采取象征的解釋”和“就事論事地當作實際的蜀道來解釋”,這是很通達的態度,是符合文藝規律的作法。任何藝術作品,都濃縮著作者部分或全部的思想傾向,生活態度和內心感情若拘泥于本事,就會“死在句下”。詩人在抒情詩里顯現的心象,不僅僅是個人的“一種情感,當它和某一種更高的認識聯系起來以后,它本身就發生了變化;我們可以稱之為情感的升華。當它和一定的政治思潮聯系起來以后,它就往往變成一種生活態度或生活作風”(164頁),這種升華的感情在具體的詩里,“他的思想因為和具體的人生體驗相結合而使我們覺得親切;……他的瞬間感覺便因為他平日的經歷、思想和認識而顯得有意義”,“便超出狹窄的個人情感的范圍而更有普遍性了”(193頁)。借用容格的話說,詩人的情感應是“集體的情感”,而這正是李白以及其他偉大藝術家之所以能歷千年而藝術魅力不衰的奧秘所在。著者正是牢牢地把握住了李白的內心世界及其它的深廣的社會、歷史內涵,我們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這部著作是嚴謹的學術成果和詩的結合體。
(《李白和他的詩歌》,胥樹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