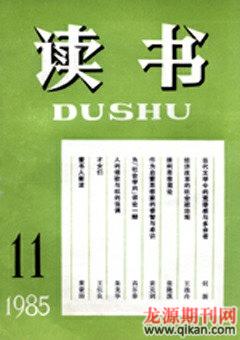我和《中學生》
胡 繩
《中學生》雜志創刊在一九三○年,那時我是個初中三年級學生。我對《中學生》的印象很深。它創刊時,我就是它的讀者。五十多年前它的創刊號封面,我還記得。我很早就在《中學生》上投稿。那時《中學生》上有《讀者之頁》的欄目,我在那個欄目里投過稿,寫的什么題目,用的什么名字,記不起來了。
《中學生》是我的老師。我從《中學生》上學到了不少東西,有文化的知識,又有生活的知識。最近有位老同志寫了一首詩給我,其中有兩句“最難法國公園夜,織女牛郎共舉杯”。他注釋說: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個公園里,我和他一同看天上的星座,我教他認識了牛郎星和織女星。我認識這兩個星,就是在初中時候從《中學生》上學來的。那時《中學生》上每期有一篇教人認識星象的文章,記不起是哪位作者寫的了。我和幾個同學按這些文章的指點,認識了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牛郎、織女等等。
因為給《中學生》雜志投稿,我認識了葉圣老。一九四三年葉圣老五十歲時,我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一篇祝圣老五十壽辰的文章,講到他教我寫文章,給我改文章。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中學生》雜志從上海搬到內地,先后在桂林、重慶出版,也起了很大影響。我在上面寫了一組講歷史的文章,一九四六年,開明書店給我出版了一本書,叫《二千年間》,就是由這些文章編成的。最近,我讀到葉圣老的《我與四川》這本書,書中有他在抗戰時期在重慶、桂林時寫的日記,那時我也在重慶、桂林。這使我回想了許多事情。圣老在重慶,曾由我陪同到曾家巖中共辦事處,恩來同志和董老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抗戰結束后,圣老到了上海,《中學生》又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恩來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雜志分成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三類。第一線象《文萃》那樣的雜志,是很快就會被國民黨查禁的。第二線是一些還可以維持一個時期,到了某種時期,也有被禁止的危險的一些雜志。《中學生》和開明書店屬于第三線,應該盡可能存在下去。總理這個安排,我和葉圣老談過,請圣老盡力維持開明書店,維持《中學生》;在國民黨統治越來越嚴酷的情況下,《中學生》多登些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文章,還是可以在青年中起促使他們進步的作用。后來《中學生》一直維持到上海解放,在這最困難的時期,給了青年有益的教育。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去香港,仍然同在上海的圣老有聯系。我寫了一組談思想方法的文章,陸續寄給圣老,他給發表在《中學生》上;后來出了單行本,叫《怎樣搞通思想方法》。
回顧起來,我和《中學生》的關系可說很深,它既是我的啟蒙的老師,又曾給我機會,讓我為它作了些工作。
全國解放以前,各個時期都有很多青年學生受過《中學生》的教益,《中學生》給了他們許多著著實實的有益的知識。那時《中學生》雖然不是直接鼓吹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但是在促進青年思想進步,推動進步文化方面,確是起了積極的作用。在那艱苦的歲月里,葉圣老和其他幾位先生為培植這個雜志花了很多心血,他們的功績是不可埋沒的。
(本文原載即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與開明》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