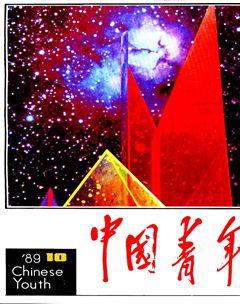候詠的世界
劉宏偉
據知,侯詠跟田壯壯、張藝謀、吳子牛等人同屬影界青年新星,可一般的觀眾卻只知后幾位而鮮知侯詠。當田壯壯聲名大震之時,又有多少人知道侯詠與他合作達6次之多?侯詠拍攝的影片蜚聲海內外—他拍的《盜馬賊》獲第三世界電影節頭獎,他拍的《晚鐘》獲1988年西柏林電影節銀熊獎;他拍的《獵場札撒》被法國舉行的國際真實電影節特選為開幕式放映的影片。世界著名攝影大師伊文斯對侯詠的攝影深為喜愛。但是,侯詠的名字對于廣大觀眾來說,卻仍然如同一位擦肩而過的路人一般陌生。
這大概是電影界所有攝影師的共同命運:人們記住了他們拍的片子,卻從來不知道,也不關心他們的名字。當攝影師的藝術造詣與導演的才華融合為一體的時候,攝影師便消失了,消失得那么漂亮、那么自然……然而侯詠對此似乎不怎么在乎,他說他所選擇的職業,是用一只眼睛去看世界—將五尺身軀放在攝影機后面,閉上這時已顯得多余的左眼,把自己周身上下全部的靈氣都運動到右眼球上;然后,通過小小的取景框去看天空,去看大地,去看山川,去看河流,去看生命,去看死亡,去看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應該說,攝影機鏡頭賦予他的眼睛一種特殊的物理屬性、一種常人的眼睛所沒有的屬性。這種屬性是攝影師的職業屬性,就像透過鑰匙孔去看一間房子里發生的事情,一切的神秘、隱秘在攝影鏡頭面前都蕩然無存。借助于攝影機,他們簡直就像一個全知的上帝—他們看見世界萬物在眼前繁衍生息,看見蕓蕓眾生在眼前行七情六欲……
侯詠生成一副文靜秀氣的姑娘模樣,可他拍攝的《獵場札撒》、《盜馬賊》卻以粗獷豪放的氣勢顯露著他那男人世界的陽剛之氣。認識了侯詠,你就會覺得粗獷并不等于粗心。拍攝前,侯詠就對未來影片的每一個鏡頭反復琢磨。筆者曾看到他隨身攜帶的一本厚厚的筆記本,里面寫滿了他幾年來所拍影片的種種設想。面對這些字句,令人不由肅然起敬—原來,偉大的藝術便是這樣起步的……拍《盜馬賊》時,為使撒吉祥紙符的鏡頭得到預想的效果,他和同行們買了數十萬張吉祥紙符;為了拍好拉撒詞,他將攝影機綁在牛皮筏子上,在波濤洶涌之中順流而下;為了拍好神箭臺被燒著的一場戲,他和伙伴們把神箭臺搭了燒,燒了搭,折騰了好多次……
要想從事真正的藝術工作,沒有一點兒認真的勁兒是不行的。
侯詠拍的處女作影片是《九月》。作為第一次獨立拍攝,他的確也曾想過一鳴驚人。那時他剛從電影學院畢業,是騾子是馬,到了遛一遛的時候了。他還真的仔細盤算過:假如我把這部片子拍得奇特新穎、攝影造型別具一格,準能觸動電影界。
但他抑制了自己這種膚淺的虛榮心,決心扎扎實實地拍第一部片子,為今后的攝影事業打開第一道大門。最重要的是,《九月》描寫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少年宮輔導員平凡的一生,沒有震撼人心的場面,沒有傳奇的情節,只是一個具有紀實色彩的普通人的感人故事。這種故事不需要那種攝影造型的沖擊力,需要的是樸實無華的攝影風格。
《九月》拍出后一些人感到失望,說是不像一個年輕人拍的,因為拍得“太老成”了。侯詠聽后卻暗中竊喜,他對自己說:侯詠,你的第一部片子成功了,因為你完成了自己的創作構想。
應該說,這部片子給他定了一個不低的起點,使他逐漸找到了一種紀實的感覺,用攝影手段造成的一種真實。在拍《獵場札撒》時,他就盡量找這種紀實的感覺,把影片拍出一種真實的氛圍。后來輿論在評論這部電影時,也多稱贊這種客觀的紀實風格。大概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法國的真實電影節才專門選這部片子作為開幕式放映的片子。
有位十分了解侯詠的朋友曾經對筆者這樣描繪侯詠:“即使是一卷手紙放進膠片盤中,侯詠也能用它拍出精彩的鏡頭。”同樣還是這位朋友,也對筆者說過這樣的話:“要不是為了藝術,整天跟侯詠這樣不善言談的人在一起,簡直就是受罪。”
侯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人緣極好。他其實是十分缺乏交際中的言談能力的。他說他這個人最大的弱點就是不會說話,尤其是怵在眾人面前發言。筆者曾跟他一起參加過電影界的一個研討會,親眼見他發言時鼻尖冒汗、滿面羞赧。起初以為他是過于謙虛,后來才知道此君最不善此道。問及原因,侯詠認為是由于家庭環境所致。
侯詠有個不幸的童年。6歲那年,正值“文革”開始。因為父親當過國民黨軍隊的連長,人家要揪斗他父親。父親是個要強且愛面子的人,正式揪斗那天,父親上街買了一把菜刀。晚上,父親看了一眼正在床上睡覺的侯詠,帶上菜刀出門去了,從此再沒回來……父親對于侯詠,只是一個模糊的記憶;可家中抑郁的氣氛,卻深深地影響著侯詠性格的形成。
可以說侯詠是在一個女性家庭中長大的,媽媽和兩個姐姐是他全部的親人。他是家中唯一的一個男人。父親死后家里生活很苦,可母親仍然拿出微薄工資中的一部分為愛好繪畫的侯詠買紙買顏料。母親把對已逝的丈夫的愛,完全交給了侯詠。侯詠永遠忘不了那件可以稱作他第一次寫生的小事:上小學時,侯詠畫了一輛電車,可他怎么也弄不清電車上的“辮子”是朝前還是朝后。母親笑而不答,卻抱侯詠來到大街上。一輛電車從母子面前緩緩駛過,年幼的畫家興奮地在母親懷中大叫:“我知道了,是朝后!”
如今,侯詠已在攝影藝術上樹立起了屬于他自己的豐碑。前不久中國攝影藝術學會成立,他被推選為理事,是所有理事中最年輕的。
侯詠雖少言寡語,內心卻極不安分。他在攝影藝術界的地位已經奠定,且更有一身令片子拍得精彩絕倫的絕活兒。可侯詠卻不滿足眼前所擁有的一切。他內心常常涌動著一種沖動,一種期望直接表達自我感覺的沖動。為了這種愿望,他開始自己寫副本,自己導劇本。侯詠所在的深圳影業公司的領導相信侯詠的才華,欣然同意侯詠改做導演工作。
于是,一位優秀的青年攝影師消失了;但不會太久,一位優秀的青年導演也許將脫穎而出,像他當年的攝影藝術給我們帶來的驚喜一樣,在導演藝術的領域里,我們還將會重新產生驚喜交加的藝術快感。
侯詠在自己的世界里勤奮地跋涉著,那腳步似乎永遠不會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