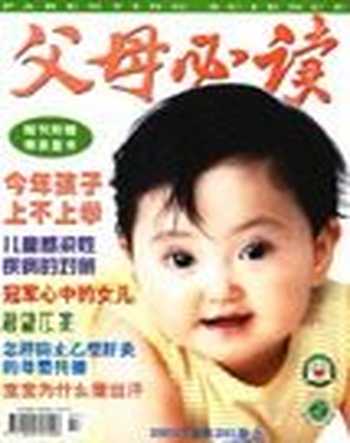都是方向惹的禍
[臺灣]黃乃毓
人到異鄉,有些原本很難的事會變得比較容易,例如開口說外文;也有些原本很容易的事反而變得很困難,例如以下我要談的這件事。
葛瑞格第一次來臺灣時,我帶他去我工作的地方,他忽然想上洗手間,我想起我們的公共廁所為了衛生起見,都已使用蹲式馬桶,而這個老外從來沒有見過蹲式馬桶,當然也沒有使用過。于是我以當過幼教老師的細心和耐心,仔細地將如廁動作分解說明,講解完畢還充滿信心地告訴他:“你去吧!很簡單的!”
他進去了好久,都不見出來,我又不能跑進男廁所一探究竟,只好一邊納悶一邊等。約有幾分鐘吧?他終于出來了,滿身大汗,滿臉紅通通的,不像剛去上廁所的人,到像剛上過酒家。
“怎么啦?很簡單吧?”
“好困難哪!我最后就沒上了。”他有點懊惱地說。
“沒上,那你在里面那么久干什么?你有沒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做?”
“你講得很仔細,就是沒告訴我那個蹲式馬桶凸出來的那個半圓型的東西是做什么用的。”他邊說邊比劃。
“那個東西與你無關呀,你不必去理它呀!”
“我不能不去理它嘛。我照你說的方法蹲下去,它碰到我的屁股,我只好站起來,往前挪一點,再蹲下去,還是會碰到,我又站起來,忘了拉褲子,褲子溜下去,我連忙抓起褲子,皮夾居然掉下去,我趕忙撿起皮夾,拿出衛生紙擦拭,褲子又往下滑,手忙腳亂的,等我好不容易位置調整得差不多時,我的鼻子已經快碰到門了,我累得不想上了。”他努力描述他的狼狽。
我認真地聽,努力地想,恍然大悟,原來那蹲式馬桶的使用時是背對著門,而葛瑞格長這么大,用的都是進門后必須轉身的坐式馬桶,進門轉身,是上廁所的習慣動作,所以他想都沒想,就“背道而馳”。
我想象著他的“乾坤大挪移”,忍不住大笑,想到他反復地站起、蹲下、站起、蹲下,好像新兵訓練,心疼之余,仍有不解。
“你這樣折騰半天,難道沒有想過要掉轉方向?”
“我當然想過!但是我研究了一下,蹲式馬桶的水孔也是在后方,應該沒錯呀!”他對他的“研究結果”似乎認為合情合理,又補充一句:“蹲累時真想在那突出的部分坐一會兒,哎……”
我們一直將此事當為笑談,他每回又說又比,總令聽者捧腹,打破一下陌生的拘束,沖淡一些沉悶的尷尬。前陣子,當他又在描述這段隆重的“入境問俗”禮時,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另一件事。那是我在美國念書時,有門課的一項作業要學生寫一篇“書面指示”,就是以文字按步驟教別人使用一樣東西。
這個作業的難度在于寫完后要在班上實際運用,教的人不能以動作示范,只能按照自己寫出來的指示念給同學聽,看看他們是否懂得該怎樣做,如果他們都做對了,表示你的書面指示寫得很清楚、詳細;如果他們不懂你要他們怎么做,表示你交代不清,必須修改。
我以“筷子的使用”為題,自信我的技巧與經驗足以教那些美國同學。然而我們小時候幾乎沒有特別學用筷子,大家都借觀察、模仿、嘗試,自然而然地會使用筷子,所以我竭盡所能,將“使用筷子”這個動作分解到只要智商只有五十的人都可以照做的地步。
試教的時候,我帶了幾雙筷子,又捏了幾個小紙團,好讓同學練習夾東西。當我把指示念完,看看同學似乎都遵循得不錯,夾紙團夾得也很開心。惟一令我納悶的是:他們把筷子拿反了,方的一頭朝下,圓的一端在上,看起來很別扭,我的疏忽是忘了在一開始就告訴他們哪端在上,哪端在下。可是他們為什么不想一想呢?難道連最基本的commonsense(常識)都沒有嗎?
當然有啦,這些聰明過人的同學告訴我:“方的在下比較好夾東西,圓的筷子不好夾,一用力就會讓‘獵物滑掉!”
我的那篇報告也成了我的笑談,每次說給臺灣同胞聽,他們都說:“老美未免太笨了,連上下都搞不清楚,畢竟筷子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結晶啊!”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起此事,也發現在我們的教育里,常常是教了一大堆知識技巧,卻很少談方向,教“研究法”的老師花許多時間教學生如何做研究,卻不教學生如何找研究方向。許多學生千辛萬苦地做完研究,往往會自問:Sowhat?(又怎么樣?)也會發現無解。老師的教導里更不乏如何做人,卻不曾交代人何去何從。教科學,給學生許多知識,卻很少去研究宇宙奧秘的根源;教藝術,給學生許多理論,卻很少去碰觸心靈最深處的美感;教文學,只在字句間操弄,也很少讓學生去思考人為何是惟一會使用語言的動物。
全世界教育內容像我們這么豐富的國家恐怕也不多見了,我們好像學問很多,但是我們沒有方向,我們是一群勤奮的跑者,卻常常因為無方向感而亂跑,變成“知識越多,秩序越亂”。一個只教選手跑得快,卻不教如何判斷方向和選擇跑道的教練,是不是好教練?一個教學生只會努力讀書,卻不告訴他人活著是為什么的老師,是不是好老師?
葛瑞格蹲馬桶前后不分,老美同學拿筷子上下顛倒,都無傷大雅,但是人生定位不清,到頭來就是很不好玩的事,您想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