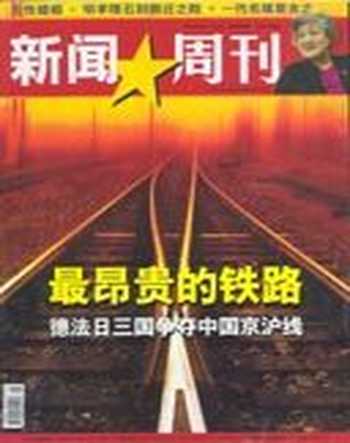中國公民在行動
人們并不只是關注自己口袋里錢多錢少,人們也會關心自己身處的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公民就是從這里誕生的。
公民行動使得中國人找到了張揚個人權利的生存方式:人們以主動制止惡法惡行的手段來抗惡
納稅人、市民、農民工、移民、公民,這些概念可說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極為流行的概念。這些概念左沖右突,都是想有所突破國家和個體的生存桎梏,轉變觀念,解放思想,并相輔相成地在中國社會匯成一種真正的歷史巨流。這個歷史巨流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公民國家。
盡管“公民國家”的內涵外延尚是一個空白,在國內,上述概念也未獲得國家政治層面的成人品質;但是在社會層面,中國人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公民”一詞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的中國,是進步的契機,是最有意味的當代人格,是連接歷史和未來的個體生存狀態。
志愿者的出現、非政府機構和非營利性機構的活動,使“發財致富”的時代沖動得到了良性的補充,它們的存在及示范,有力地表明,人為財死,人是經濟動物,人以成本算計自己的存在等一度流行的世俗哲學并不放之每個人心中而皆準。志愿者利人也利己的生活方式,表明社會個體對流行的活法兒并不買賬,人們對時尚生活或集體意識并不畢恭畢敬或亦步亦趨。
人們并不只是關注自己口袋里錢多錢少,人們也會關心自己身處的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公民就是從這里誕生的。正是對這種生存秩序的關注,中國人開始關心自然、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開始關心婦女、兒童權益,關心工人、農民的國民待遇,關心自己的居住環境,關心市民的利益。從上世紀年代開始,無數的中國公民在行動,無數的中國公民行動參與了社會的進步發展。
中國人向來以“一盤散沙”飲譽全球。以往人們回避公共生活,無視生存秩序。在外人以為絕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環境里,中國人世世代代習以為常,六朝的貴族手捧黃金珠玉餓死,宋明的書生清談性理避世,只能在最后一刻以死報君王,無數的蟻民只是以血肉之軀構筑讓人觀賞的“長城”。《義勇軍進行曲》在面對國人的反抗特性時,極為精準地說到,反抗是被迫的,吼聲是最后的。也許正是這種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才使得歷史上演一幕幕以暴抗暴進而易暴的悲喜劇。
但是,在當代中國,這種情況有了改變,公民行動使得中國人找到了張揚個人權利的生存方式:人們以主動制止惡法惡行的手段來抗惡。公民行動是一種社會層面上有效的抗惡方式,它可以示范,它可以普遍展開,它激發的是生命的善意:理性、良知、權利和責任。正是公民行動使得渺小卑微的個人不再孤立無援。
以生命至善抗惡在中國一直有著久遠的傳統,那種百里捐軀、千里顧命、萬里擔大義的立身處世之道在中國世代不乏其人,在今天其人物事跡更是不可勝數。我們上千年的文明交流史,也使我們中國人從佛教文明中采信了無緣大慈異體同悲的觀念,每個人都跟他人息息相關。
同時,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化史,讓我們明白,對于歷史、社會和生命之惡,應該主動抗擊、制止。
西方文明讓我們熟知鄧恩的詩句,“沒有人是座孤島,獨自一人,每個人都是一座大陸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塊泥土被海卷走,歐洲就少了一點,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樣;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對我的縮小,因為我是處于人類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一位德國牧師的生存經驗讓我們驚悚于心,“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后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后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
在市場化、世俗化的今天,我們的新聞媒體不懈地報道真相,揭示社會的黑暗和罪惡;我們的知識分子一代代傳承著批判精神并不斷深化批判的深度;我們的大學生和社會青年在志愿活動中把自己的青春歲月獻給了邊緣弱勢群體,服務于后者,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我們無數的城市居民聯合起來對抗物業、房地產商的不公正。顯然,這些中國公民行動不僅僅是一種普遍的抗惡形式,而且是一種正當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希望這一歷史巨流最終匯入現代文明世界的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