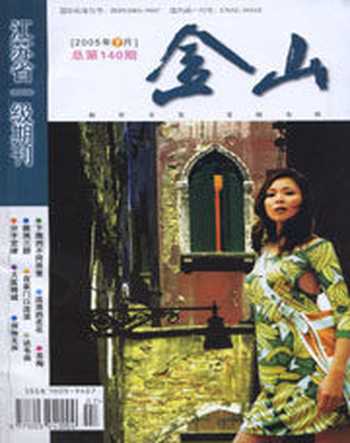徽商三題
孩 子
半年后,徽商的門臉像是杭州城里重建的屋宇一樣,新鮮繁多得讓人目不暇接。但是他們的招牌都沒變,還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無非寫著本店內有××貨物,物美價廉服務守信。
打進杭州
1860年,徽商其實已經逐漸滲透進了杭州城。但是因為本小利薄經營范圍太窄,他們的特色貨品——蘿卜干也與杭州人的飲食不太搭調,所以,徽商只能棲身于杭州城的各個角落,守著一個個小門臉,慘淡經營。他們甚至儉省到連招牌都省了,只貼上寫有歪歪扭扭字跡的廣告,內容無非是本店內有××貨品,物美價廉服務守信。
最先把門臉開進杭州城的是吳士,他的身后跟著一批又一批的徽商。盡管所有人都跟他一樣信奉著“物美價廉服務守信”的宗旨,可是眼看著徽商只是在杭州城的最底層苦苦掙扎著,吳士也只能干著急。
后來太平軍打進了杭州,整個杭州城因此陷入了慌亂。所有人都只有一個想法,趕緊逃,在戰亂面前,似乎只有逃離才是上上之策。而對于降臨到身邊的災難,徽商們似乎見怪不怪。也難怪,他們沒有讓太平軍們眼紅的財產,也沒有足夠惹眼到遭災的原因,加上徽商有四海為家的天性,他們已經把杭州城的各個角落當成了家,不愿輕易離開。面對迫近到身邊的戰爭,徽商們把門臉掩上一半,半遮半掩地繼續經營著各自的鋪子。
既然是躲戰亂,那就意味著要帶干糧。可南方的城市,能帶的無非就是一些干飯團。去郊區到鄉下總不能干啃飯團吧,于是徽商們的蘿卜干史無前例地見到了一線生機。不知是誰第一個想起了還愿意開門經營的徽商,于是全城都形成了一個局面,帶足了飯團準備逃離的人們一呼啦全涌到了那一個個不起眼的小門臉面前,蜂擁著要買以前看都懶得多看一眼的腌蘿卜干。面對越來越多的人群,徽商們很快從興奮轉到了恐懼。
吳士沉吟著,坐在一幫焦急的徽商中間。沒用多少時間,吳士便依照眾人的期待拿出了主意,趕緊漲價,照十倍往上漲!吳士輕揮著手,大伙趕緊的,不然要不了多久他們就能哄搶起來。
見大伙愣著不走,吳士話音一落就先走到自己的小店門前,把胳膊一揮,高喊道:今天蘿卜干漲價十倍,想買的到右邊排隊!混亂的人群驚詫了一下,忽然安靜下來。在戰亂面前有太多的人視財物為糞土,所以不少人馬上排到了右邊,人群在幾分鐘之內井然有序起來。
天黑之前,整個杭州城似乎都彌漫著腌蘿卜干的味道。
一切混亂都過去之后,吳士從每個人的臉上都看出了意外,那意外里有忐忑,也有驚喜。于是吳士遲疑了一會,說,今天早半夜有個江西的米商來找我,他的一百船大米從水路跟太平軍一起到了杭州,如果他天亮之前不能把那一百船大米賣掉,十有八九要被搶去當軍糧了。他說價錢隨便我給,只要我接下這一百船大米。開始我沒接話,他撲通給我跪下了,他說即使扔到西湖里喂魚也要由我來扔,否則他心疼死了連鬼魂都不敢回鄉。
眾人都看著吳士,那意思吳士明白,等著他拿主意呢。吳士磕掉了煙袋鍋里安徽產的煙絲灰燼,小屋子里彌漫著一股清香。我同意了,但是價錢咱不能少給人家。一會大伙按今天銷售蘿卜干的多少計算一下,把米搬到各自的店里去。記著,這米不是咱們的,沒有經過大家伙商量,誰都不許動。
一百船大米在天色大亮之前分解到了一個個小店里去,沒有留下一絲痕跡。
但是太平軍給杭州城留下的痕跡太大了,他們撤走后,整個杭州城凌亂得像個被無數人欺辱過的少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杭州人是整著出去的,零散著回來的,帶回了陸陸續續的哭聲和屈辱。重整家園的第一步是吃飯,但杭州城里每一家的米甕都是倒扣著的,每一戶的糧倉都是空的。搶掠一空的景象就像彌漫在大街小巷里的絕望,綿長而稠重。
又不知是誰第一個發現的,杭州城的各個角落里,那些曾經見利忘義的小門臉上,零落地貼著字跡歪扭的廣告,廣告的內容是本店內有大米,各家各戶可以按人頭來領口糧。不用帶錢,只要記著門臉在哪就行了。
半年后,徽商的門臉像是杭州城里重建的屋宇一樣,新鮮繁多得讓人目不暇接。但是他們的招牌都沒變,還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無非寫著本店內有××貨物,物美價廉服務守信。
但顧客盈門的狀況已經太不稀奇了。
尋找
胡尋似乎就是為了尋找父親才來到這個世界的,母親含辛茹苦為其單取一個尋字,好像胡尋先天就有一副重擔。所以大家都說胡尋生就一副愁眉,長就一張苦臉。果然,從十三歲開始,胡尋就踏上了遙遙無期的尋父之路。
在徽商堆里,胡尋就算是個異類了,看遍徽商,有誰會不務正業、只身一次又一次地上路,只為尋找一個可能久已不在人世的人呢?
于是胡尋很沮喪,在第三次從村口上渡船時,胡尋向母親表現出了這種無望的頹廢。母親的淚忽地就漫了一臉,聲調集中了十幾年來都難得出現的嚴厲:不許你這么想,你父親肯定還活著,雖然這么多年他沒有音信,可是他經常托夢給我的。阿尋,娘知道你苦,知道你怕別人看不起你四處亂走游手好閑,但是只要娘在,一天找不著你父親你一天就別想做自個的事。
胡尋怕看到母親的眼淚。盡管村里像母親這樣的女人遍地都是,但母親似乎是個例外。父親走的時候,胡尋在母親的肚子里分蘗著自己的手指腳趾,似乎就聽到了母親心碎的聲音。徽商的女人都心安神靜地養孩子,等丈夫,唯獨母親不。從胡尋還在襁褓中懵懂地分辨著這個世界時起,母親便不厭其煩地培育著一棵樹,這棵樹根在胡尋的心里,枝葉在天涯海角,名字叫尋夫樹。
胡尋確信母親糾纏的目光粘不住自己的背影了,才伸手抹掉了淚。船夫用帶有幾分復雜的同情問,阿尋,又去找你父親啊?胡尋茫然地怔了一下,謙卑地點頭,呃,是的。
母親當然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這么大的世界找個人有多難。十六歲的胡尋早該是個半生不熟的小商人了,可胡尋三載云游,結果只是學會了幾百種打聽人的方法,還有腦海中不計其數的面孔。那些面孔忠厚、滄桑,無一例外地貼滿著漂泊的無奈。這是徽商的標簽,胡尋可以像個醫生一樣從望、聞、問、切中隨便挑個字便能辨出對方的身份。
其實更多的時候胡尋是被別人打聽,家鄉的山路修了沒有?自己的孩子多大了?家里的日子還過得去嗎?捎帶著,胡尋還要推辭不過地接受人家一點饋贈,緣由是需要帶個口信,或者一紙報平安的帛書。
一年胡尋要回家一趟,母親擔心胡尋的安危,當然,更揪心胡尋搜尋出來的結果。村頭的渡口就代表著一次又一次的分離與迎接。胡尋知道,在行程快結束的那些天里,母親天天站在岸上的那塊青石板上等。村人開過玩笑,說那塊石板叫望子尋父石,石上快被站出兩個腳印了。
離別總是酸楚,但胡尋更害怕迎接。懷中那卷繪有父親頭像的布日漸一日地破舊模糊,母親臉上的風霜褶皺一年濃似一年地密集,可父親的消息一直還在風里、水里,毫無痕跡。
突然一次送別,母親手里多了個包裹。母親有點難為情地解釋,鄉鄰平時沒少幫忙,你的婚事要不是她們都辦不起來。你不是見過張家二叔李家大爺嗎?捎帶著給人送去。
胡尋接過了包裹,目光越過母親的肩膀,后面是一個瘦瘦小小的年輕女人,羞澀嫵媚。
于是胡尋游走在一條新的道路上,無謂的尋找,撕扯般的思念,消沉的步履。唯一讓胡尋有點成就感的是背上的包裹,分散掉的是重量,收獲的是一份份夸張而隆重的感動,有時甚至是老淚縱橫、欣喜若狂。
在母親不能親自站在那塊青石板上等待的時候,換了一個瘦弱的身影,身影旁是幾個新鮮的小生靈。胡尋的兩鬢過早霜白了,風塵的摧殘總是和內憂外患糾合在一道——母親臥床不起,可就是不肯閉眼。胡尋領著膝下幾子一起跪在母親榻前,哽咽著告訴母親,已經大致知道父親所在的區域了。隨后,胡尋讓母親入土為安。
多大歲數沒了母親都是孤兒。胡尋跪在母親墳前忽然領悟到了什么,再次出游尋找父親的腳步卻堅定起來。只是身邊的累贅越來越多,先是一堆又一堆的書信,還有千篇一律的口信,更主要的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幾個兒子慢慢都大了,自己卻沒給他們闖下任何足以生活的路子。
擁著孱弱的妻子,胡尋滿是愧疚,喃喃道,這些年娘是怎么養活你們的啊?妻子有點滿不在乎,你捎帶的那些書信掙的啊。胡尋一愣,這個怎么能收人家的錢呢?順便嘛,妻子辯解,不是娘要的,是人家硬給的。
幾個兒子自作主張,收集來的書信物品漸漸要用車載船裝。胡尋無力阻攔,只好訓斥,我帶你們出去是為了尋找爺爺,順道捎帶這些東西,不許收錢!兒子們是是地點頭,手底下卻忙碌個不停。他們很快追隨著父親的腳步走遍了徽商所在的區域,父親心中那些面孔幫了大忙。
等胡尋意識到什么的時候,已經晚了。幾個兒子不知不覺中建立起了一張四通八達的網,網是無形的,卻覆蓋著徽商。徽商們管胡尋的幾個兒子叫信客。信客的名頭不可遏止地聲名遠揚。
胡尋客死他鄉。
都說是讓他幾個兒子給氣死的,徽商們不屑,做了頭等的好事又能賺錢,他干嗎氣死?
于是徽商史中留下了疑惑的一筆。
徽商的第一代信客在族譜中這樣寫道:胡尋,信客開創者。信客,起源于胡尋一生尋父。有實物為證,望子尋父石上一雙三寸腳窩。
茴香豆
戴根十五歲的時候,跟村里所有的男人一樣,娶了媳婦。媳婦的肚子開始鼓起來的時候,戴根就收拾行囊,要四海為家。
“十三四歲,往外一推。”徽商的祖祖輩輩都是這樣過來的,也因為如此,才有了徽商的名號。生在徽商的窩里,戴根沒辦法不這樣。吳力跟戴根從小一塊光著屁股長大的,但吳力已經做了兩年的信差了。相比較同齡人,戴根已經該慶幸了。盡管媳婦跟在后面哭得死去活來,戴根也沒辦法再摸一把媳婦那黑亮油滑的頭發——戴根已經上了車,車轱轆咯吱咯吱地響著,把戴根一點一點帶遠。戴根覺得自己像片注定要落到水面的樹葉,漂到哪里根本由不得自己。
四海為家就是徽商的標簽,只要你到年紀了,就得出來。生為徽商的后代,咱們成人的標志不是有了媳婦懷了孩子,而是你漂得怎么樣。不混出個人樣,連回鄉接媳婦都沒臉。你看村里還有男人嗎?
戴根發著呆,聽著吳力喋喋不休。戴根其實知道,吳力這趟出去其實就是為了送他戴根,十幾年的交情了,吳力是想讓戴根在頭一回出門就有個老手帶著,能少吃些苦頭。
可是吳力你知道的,平時我不在家她連飯都不吃的,再說她還懷著孩子,我這一走都不知哪年才能回來,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到她的面。吳力,我就想不通,我不想有出息,我就想在角落里守著媳婦過安穩日子,不行嗎?戴根的聲音又有點哽咽,從上車到現在,每說一次話戴根的眼淚就往外跑一次。任憑吳力有著一張巧舌如簧的嘴,在戴根的眼淚面前還是不起什么作用。
車廂外的車夫不屑地“嘁”了一聲,啪地甩了聲馬鞭,車子往前一縱,把戴根閃了個趔趄。
餓了沒?吳力找不著話了。這個戴根從小就跟一般人不一樣,一個大男人,眼里不知包著多少淚,似乎總也流不完。娶了媳婦后還愣是頂著白眼賴在家里過了一年。像他這年紀,在外面的都該能獨立開爿店了。
戴根像是想起了什么,從包里拿出了干糧,又掏出了一包炒熟的豆子。吳力,你先吃著,順便給車夫點,讓他停停車,我想解大手。
戴根跑了,解手時偷偷跑的。戴根這輩子算是完了。生在徽商的窩里,想呆在角落里守著媳婦過日子,就得付出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的代價。吳力長嘆了一聲,其實戴根做的吳力又何嘗不想,可做什么都是要勇氣的,吳力沒有這個膽子。
吳力再回到村里時已經快過年了。戴根的處境比吳力想象的還要差,族里已經把他攆出了村,戴根和媳婦在村尾蓋了間茅草屋,房子低矮到不能直腰進出。孩子已經生了,剛能在地上爬。
見吳力來看他,戴根把臉扭到了一邊,輕聲說,你趁著沒人還是走吧,別丟了你的人。
戴根,我就說一句話,說完了就走。你回來時給我留的炒豆是誰炒的?村里家家都炒,可我從來沒有吃過那么可口的。
戴根愣了愣,仍舊沒偏過頭,我媳婦炒的,她加了茴香,我喜歡茴香那個味,她就加了。
不可能就這么簡單。
她……她們家祖傳的炒法。
那過年我走時能給我帶十斤嗎?我花錢買。
戴根似乎不相信,遲疑著,仍沒轉過臉,你想要就拿生豆子來讓她給你炒,不怕你笑話,我家里半年沒見過豆子了。
不是我要,是外面的人要,他們嘗了都說有家鄉的味道,要花大價錢買呢。這次我先帶十斤出去給他們試著吃,如果行,再回來我可就不要十斤八斤了,可能十車八車都解決不了問題。
戴根終于把臉轉了過來,眼里噙滿了淚,行。
六十年后,戴根進了戴家的宗祠,排位在最醒目的位置。因為戴根已經是方圓百里最著名的大富翁了,他只賣一種小吃,那小吃叫茴香豆。本來徽商里最大的茴香豆經銷商吳力要叫它回鄉豆的,戴根沒同意,戴根說那就是媳婦加了茴香炒的,就叫茴香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