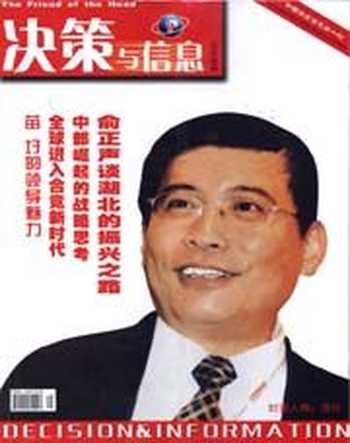努力走出中部崛起的新路子
陳棟生

“中部地區”涵蓋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和山西6省,從性質上看,屬于聚類組合的區域政策覆蓋區。
中部“崛起”的內涵,和以往有所不同。過去,中部省、市崛起的目標屬地方性戰略。現在中央政府“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明顯的將它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崛起的目標與標準,既包含六省如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亦應包括使中部六省逐步成為拉動國家經濟的又一重要引擎,即通常所說的第四增長極。近年,當我們重新審視國家糧食安全問題,當煤電油運全面緊張,成為解決國民經濟進一步增長的“瓶頸”,當資源約束在東部幾個快速發展地區首現端倪之時,中部6省的戰略價值和地位愈益凸現,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帶著現實的體驗,重新咀嚼著“中原定、天下安”這一古訓的深遠涵義。從崛起的內容和路徑選擇看,應充分體現、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經濟增長方式逐步完成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轉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使廣大民眾能投身參與崛起,亦能分享崛起的利益,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實實在在的提高。簡言之,中部崛起要走出一條新路子。為此,要正確對待和處理一系列關系。
政策扶持和內生自增長力的培育
國內外經驗表明,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是靠內生自增長能力,但這不排斥政策扶持的作用,西部地區和東北三省近幾年的初步轉變,也證明了有針對性的政策扶持的重要作用。中部地區許多城市與礦區,國有老企業多、設備與技術老化,歷史包袱沉重,礦業城市資源枯竭、地面沉降,亟待發展接續產業等等。建議比照東三省的政策,提前實施增值稅轉型,國有企業剝離社會職能時,中央財政予以適當補助;國有企業改制時,有條件的核銷呆賬壞賬;利用國債或專項資金支持老工業基地上一批技改項目;對重大裝備科研、攻關設計給予必要扶持;對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給予系統支持等。中部地區的西側(如晉西、豫西、鄂西、湘西)和皖、贛山區,在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方面,和西部有類似處,除鄂西、湘西兩個自治州已比照享受西部地區有關政策外,爭取其他山區亦享受同樣的政策待遇。中部農村人口比例高,大部分又集中在糧食生產區,近年兩個一號文件的各種支農、惠民的政策,有必要更加系統集中地投入到中部農村。
統籌城鄉發展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中部地區國土面積102.73萬平方公里,要崛起,只能首先重點突破。第一個層次是完善與發揮6個省會城市和以它們為核心的武漢城市圈(1+8)、中原城市群(1+8)、長株潭、昌九、皖中和晉中城市群的城市功能,為企業進入國內外大市場、進入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提供便捷、交易費用低廉的大平臺,成為企業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的源頭。第二層次是培育壯大一批區域性中心城市和以它們為核心的城鎮群(圈、帶)。第三層次是發展縣域經濟。
縣作為行政區劃和行政管理的基層層次,處于安民、富民的第一線。“郡縣治、天下安”的古訓,至今仍然適用,如果說大中城市是國家經濟的支柱,那么縣城經濟則是國家經濟的基石。除了緊鄰大中城市周邊的農村,可以直接接收城市的輻射、帶動,城市對其余農村的帶動往往是通過縣,首先是縣的城關鎮和其他中心鎮。中部6省和江蘇、浙江經濟發展比較,大中城市相比有差距,但遠不如縣(含縣級市)域經濟差距之大。按第四屆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進入全國百強縣的,江、浙兩省共48個,幾占一半,而中部地區合計才6個(河南兩個,湘、鄂、晉各1個)。
發展縣域經濟是一篇大文章。在注意縣域經濟發展的同時,還需要狠抓縣域社會事業的發展,最緊迫的是學齡兒童的上學,初級衛生保健與就醫,預防因病致貧、返貧,以及成年人的技能培訓,這對提高勞務輸出的檔次和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影響重大。
對內對外開放和本土創業者的培育
經過20多年快速發展,東部長三角、珠三角、閩東南等地區,伴隨工業密度的提高,一系列要素價格上揚,有的已出現“地荒”、“電荒”、“水荒”和“民工荒”,新一輪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已經開始,這對中部地區發展,是需要及時抓住的機遇。至于境外資金和技術的引入,中部差距較大。按2003年的數據,中部6省當年實際利用外資僅占全國同類指標的11%,進出口總額僅占全國同類指標的4.2%。中部經濟外向度偏低,和中部產業技術進步不快,結構優化升級緩慢,有著明顯的因果關系。在重視引進境外、區外資金與技術的同時,對本土投資者、創業者要同等的重視。對一些發展水平較低的市、縣,一時難以形成引進外資環境的地方,從引進內資起步,逐步完善投資環境。而培育引入外地投資的軟環境,又要從營造有利于本地社會資金投入開發和本土投資者、創業者的形成、壯大入手。
(作者: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