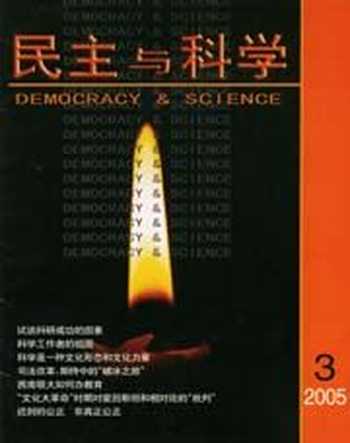婦女難產中的法治思考
馬 嶺
當產婦難產的時候,醫生通常問其丈夫“保大人還是保孩子”?有的丈夫會說“保大人”,有的丈夫會說“保孩子”。孰對孰錯?我們會展開激烈的爭論。
有些人首先會提出問題,丈夫有什么權利做這樣的決定?他說保大人就保大人,他說保孩子就保孩子?他憑什么能夠決定妻與子的生死?誰給他這樣的權利?如果丈夫把妻子當作傳宗接代的工具,根本無視妻子的生命,他選擇“保孩子”,其妻子就被剝奪了“活”的機會;如果丈夫“深明大義”選擇“保妻子”,妻子因此而獲得了“新生”,他就成了她的救世主,她的生命是他“恩賜”的,因為他的明智、大度、仁厚,她才有了“生”的權利,“她”和“他”又怎么能夠平等?
有些人會提出夫妻之間存在法律上的代理關系,但這種“代理”被細究下去后很快就露出了破綻:財產可以代為管理,信件可以代為簽收,房屋可以代為出售,但生命怎么可以代為選擇呢?生命權是不能轉授、不能讓渡的。
還有人最初贊成丈夫作出“保大人”的決定,經過一番討論,大家普遍認識到,不論丈夫作何選擇,由丈夫掌握妻子的生死大權本身就違背法治精神,這與將妻子視為丈夫的財產、可以作任意處置的奴隸制法律沒有本質的區別,從根本上否認了妻子作為人的獨立存在,連生命權都捏在別人手里,自己不能掌握,還談什么其他的權利(人格、自由、財產)?在現代文明國家,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而我們的社會(包括“文明”的大都市)竟然還有這樣野蠻的“規則”在事實上存在,真是不可思議。
有的人會進一步追問,是誰給了丈夫們這樣的權利?大家都認為是習慣,是幾千年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傳統道德、民間習俗在無形中形成的一套“習慣法”。這些習慣在我們的社會中被沿襲下來,我們今天的法律并沒有對昨天的陳規陋習作出及時有效的清理。
在大家基本認同丈夫們無權決定妻子的生死之后,下一個問題是,誰有選擇的權利?
有人認為,應當由產婦自己選擇,只有產婦自己才有權選擇自己的命運,把握自己生命的權利。但也有人反對:產婦什么時候選擇?在她難產的時候嗎?當她在產床上痛苦呻吟、大出血、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我們卻要她作“保自己還是保孩子”的選擇嗎?這是否可能?是否太殘忍?在此飽受折磨之際她能作出明智的選擇嗎?她是否會因無法忍受一時之痛苦而喊出“還不如讓我死了吧”?難道醫生就根據這樣一個“選擇”來行動嗎?我們就這樣讓產婦“獨立”、“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命運還要她“后果自負”嗎?這樣的“獨立”、“自由”是在解放婦女還是在摧殘婦女?顯然,讓產婦在難產時作決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又有人會提出,在產婦清醒的時候呢,比如在生產之前,對生產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包括難產時大人或孩子只能保一個的情況下,由孕婦(這時是孕婦而非產婦》作出選擇,這時她有充分的時間慎重考慮,作出選擇。但還是有人提出了疑問,孕婦在懷孕期間本身就需要受到特別關照,應盡量避免精神緊張,情緒不穩定,如果還要考慮這么殘酷的問題,是否人道?是否對胎兒有不利影響?更有人提出,我們相信大多數婦女會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但如果有孕婦選擇“保孩子”呢?不管是出于愚昧、甘愿做“傳宗接代”的犧牲品,還是為了神圣的愛情而利令智昏、作出瘋狂的決定,或者是出于偉大的母愛,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全孩子……對于這些明顯“錯誤”的選擇難道也要尊重、執行嗎?孕婦為了保住胎兒可以“犧牲”自己的權利嗎?人的生命可以放棄嗎?如果有,安樂死、自殺是否也都可以?有人會從民法的角度提出,民法上一般認為公民無權處分自己的生命,否則就給自殺提供了合法的依據。大家爭論的結果,由產婦自已決定的方案也基本被否決了。
有人會認為,應當由醫生選擇。醫生有豐富的醫學經驗,一般來說較為客觀理性,他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大人活的機會大就應當先保大人,孩子成活的機率高就先保孩子。這種意見看似有道理,但仍然有人會提出不同意見:這種模式的前提是將“大人”和“孩子”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來選擇,而這種“平等”是值得懷疑的:我們不要忘了這時的“孩子”是尚未出生的“胎兒”,而不是真正的“孩子”,其是否享有生命權還值得商討。這里涉及到生命從何開始這樣一個問題,有些人紛紛引用專家們的觀點,“當代醫學公認的標準,應為胎兒完全脫離母體、獨立生存、能夠自己呼吸”;有人介紹澳大利亞維多利亞議會上院處理的美國公民奧斯夫所遺胚胎案,“胎兒在客觀上具有生命形式,但胎兒的生命尚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只是先期的生命形式”;有人介紹了“陣痛說”、“一部露出說”、“全部露出說”、“斷帶說”、“獨立呼吸說”、“發聲說”;還有人引用12世紀的猶太教神甫、醫生兼哲學家蒙尼德斯的“侵犯論”:“如果胎兒的繼續存在威脅到母親的生命,胎兒就成了侵犯者。對侵犯者的打擊不應視為謀殺,因此人工流產對胎兒生命的剝奪也不是謀殺”;有的同學贊同17世紀天主教神甫桑切斯的“自衛論”:“盡管胎兒是無辜的,但如果他的存在威脅到母親的生命,終止他的生存就是一種合法的自衛。醫生類似于被雇傭的保鏢,可以合法地幫助母親消滅侵略者……”對于尚未脫離母體的胎兒是否有生命一直是學者們爭議不休的問題,大家也不可能爭論出一個結果來,雖然在法律上胎兒享有繼承權等民事權利,但生命權是否受法律保護則各國規定不一。部分國家認為墮胎是合法的,即不承認胎兒有生命權,有的國家則規定墮胎為非法。無論如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當胎兒的生命與產婦的生命發生沖突時應以保護產婦的生命為先,在反墮胎最為激烈的美國也承認為了拯救母親的生命,墮胎便是合理合法的,一旦分娩嚴重威脅到母親的生命安全,醫生應毫不遲疑地為孕婦墮胎。
經過一番“各抒己見”,很多人基本上會達成共識;胎兒的“生命”與產婦的生命是不平等的,在二者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考慮產婦的生命,先拍救產婦,“保大人”!對此,丈夫沒有選擇的權利,產婦自己也沒有選擇的權利,醫生同樣沒有選擇的權利。有人指出,如果丈夫有權選擇,他選擇了“保孩子”,醫生豈不成了剝奪其妻子生命的幫兇?如果產婦自己可以選擇,她選擇了“保孩子”,醫生是否在協助產婦自殺?一些人從法律后果上分析,認為“保孩子”不保大人可能致產婦死亡,是對婦女生命權的剝奪,“保大人”不保孩子只不過是墮胎是對婦女生育權的侵犯,這二者有明顯區別。有人甚至懷疑醫生“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詢問是何居心?是否在推卸責任?醫院還有投有法制觀念——把這樣一個人命關天的“權力”交給私人、讓他側去選擇?也有人指出,如此草率地處置生命,并被我們大家熟視無睹,習以為常,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反思、反省的。
既然在產婦難產時,丈夫、產婦、醫生都沒有選擇的權利,那么誰有權利選擇?在這里,不存在選擇的問題,只要產婦一息尚存,就應當不遺余力地搶救。如果硬要說選擇,那么應當由法律作出選擇,法律相對于個人是理性的、明智的、文明,對于人命關天的大問題還是交由法律決定比交給任何私人選擇都更穩妥、更慎重、更公道。法律不會允許丈夫作出對妻子不利的選擇,不會支持產婦犧牲自己,不會給醫生推卸責任的權利。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在產婦難產時,醫生必須全力搶救產婦,不得以“保孩子”為理由犧牲產婦的生命。
我國目前的法律對產婦難產時應當保大人還是保孩子沒有直接、明確的規定,但有人認為,我們仍可以從現有的法律中推論出相關的意思,如我國《婦女權益保護法》第35條規定:“婦女的生命健康權不受侵犯”;《母嬰保健法》第18條規定“經產前診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醫師應當向夫妻雙方說明情況,并提出終止妊娠的醫學意見……(三)因患嚴重疾病,繼續妊娠可能危及孕婦生命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孕婦健康的”這些條文中已暗含著“孕婦的生命安全是首位的,受法律保護”之意,但許多人會認為僅有這樣的“暗含”是不夠的,法律應當作出相應的明確規定,或通過法律解釋將“暗含”之意明晰化,明令禁止在產婦難產時由丈夫或醫生決定先“保孩子”而將產婦的生命放在第二位,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這類事情應當依法進行相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