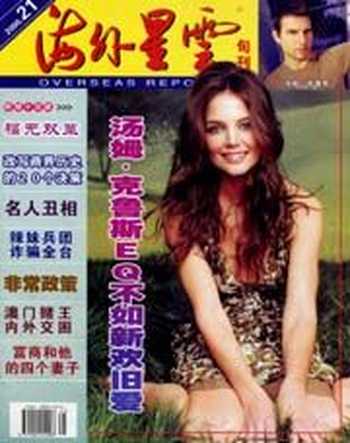天氣預報幾時準
氣象預報很難精準
2004年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一對新人在美東佛蒙特州的一個小島上舉行婚禮。氣象預報說今天是個好天,實際天氣比預報的還要好。
然而,新郎新娘親吻過后,就開始變天了。那陣狂風持續了不過幾秒鐘,卻像龍卷風般怪異不可預測,舉行婚禮的大帳篷被連根拔起,很多賓客被飛舞的尖樁和玻璃擊傷。
繁華或毀滅、活命或死亡,也許就取決于精確的氣象預報。因此,我們要求氣象學家做到幾乎不可能的事:弄清楚整個地球大氣層的戲劇性變化,然后告訴我們,在這里,今天,下午4點30分,會發生什么事。
氣象所涉及的許多物理作用,我們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來都已有所理解,然而,那些力量組合的方式與遵循的變數是如此眾多,精準的氣象預報總是可望而不可及。
資料總是不夠用
想推斷未來天氣,就必須了解當下情形,也就是氣象學家所謂的“目前狀況”。這是氣象學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
美國國家氣象局每天都要接收大量觀測資料,有來自地面觀測站的19.2萬筆、來自船只的2700筆、來自氣象浮標的l.8萬筆、來自飛機的11.5萬筆、來自氣球的大約25萬筆,以及來自衛星的1.4億筆。此外還有通過海外觀測網絡取得的無數資料。然而這一切都還嫌不足。
當今的氣象預報是由電腦模式挑大梁,它需要更多、更整齊的氣象數據,數據必須來自涵蓋全球且延伸入大氣層的網格上均勻分布的各個點,且每小時要更新一次,每分鐘更新一次更好。但現實世界中這是辦不到的:衛星很難看透厚厚的云層,也無法詳細掌握風況;氣象站、氣球、飛機和船在全球分布不均;而很多地方,例如非洲等貧窮大陸上的大片地區,連地面觀測都極為稀少。
借助大氣模擬機
為了彌補那些觀測空白,氣象學家以大氣層近期的最佳圖像為本推算未來,獲得氣象“預報”。
這臺被稱為“數值模擬”的時光機,其實是一種大氣的電腦模式,不是由空氣和水蒸氣組成,而是數據和方程式。方程式描述了影響天氣的關鍵過程,例如氣流、蒸發、地球自轉,以及水在凝結或凍結時的熱量釋放等。當氣象學家在模式中輸入大氣情況的數據并執行方程式后,模式就會預測大氣如何發展。
這項計算極為費力。位于馬里蘭州蓋瑟士堡的“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電腦中心,如今在一臺稱作“藍機”的超級電腦上進行大量數學方程式的運算,該電腦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氣象預報設備之一。這臺新機器很像一座放滿高科技檔案柜的倉庫,目前尚未全速運作,不過到2009年時,它就可以在一秒鐘內處理8.6萬億筆計算。
然而,就算是最精密的電腦模式,也大幅簡化了真正的大氣狀況。某些模式可以推算出16天后的情形,但在那種情況下,精確性已經大為降低,只能預測氣溫是否會高于或低于正常月平均值。這一切都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電腦運算。
“蝴蝶效應”讓問題復雜
還有一種叫做“蝴蝶效應”的東西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一只蝴蝶在地球一側拍翅而產生的微乎其微的風,可能在地球的另一側引發一場風暴。這雖然是夸大其辭,但也蘊含著些許真理:某些微小的因素,都有可能對天氣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
舉例來說,風向的輕微變化可能會讓一場風暴偏離預期路徑好幾公里。在冬季,不及一度的溫差就可以決定是下雨、下雪、下凍雨,還是下霧。那點小小的區別,對數百萬人的影響可大了。
為了因應蝴蝶效應,氣象預報人員仰賴一種稱為“系集預報”的策略。他們以一套初始條件為基礎,做出許多組預報。每一組都加入略微差異的“擾蕩”,例如風速每小時一公里的增減、一度的溫度變化、濕度一個百分點的不同等。這么一來,預報就成了統計學:比方說,50筆電腦運算結果中有43筆指出會下雪,7筆則預測下雨。正因如此,許多氣象預報都使用像“可能”或“很可能”這樣的字眼,且用百分比來表達降水幾率。
氣象學家做預測
電腦沒有最后決定權。電腦模式得出結論后,輸出的信息會被轉換成較易讀的圖表,在美國的話就是送往水文氣象預報中心(HPC)。在那里,血肉之軀的氣象學家根據機器得出的結論再做進一步預測。
某個秋日,氣象預報員布魯斯·泰瑞坐在兩側都是電腦熒幕的工作站前。就那一天而言,泰瑞的任務是判斷雨會降在哪里、雨量有多少。電腦已經交出了它的最佳預測,現在輪到他憑直覺判斷了。他預報,暴風中心將會在凌晨為華盛頓特區帶來大雨,且暴風的前緣會在新英格蘭上方,極有可能帶來降雪。第二天,人們將發現他所言不假。
事實上,像布魯斯·泰瑞這樣的HPC工作人員所做的不是真正的預報,而是提供給下面125家地方氣象臺的“指南”或“建議”。商業氣象預報人員也是運用這些基本資訊來供應氣象“產品”,像是電臺、報紙、電視臺和網站所需的花哨地圖和衛星圖等。有些人甚至專門出售天氣預報給想要找到最佳海灘的沖浪者,或是必須提前收到霜害警報的養蘭人。
天氣預測變火警預測
還有一些預報人員的工作領域已超出了天氣本身,轉而關注天氣對基礎設施、環境和經濟造成的影響。在佛羅里達,研究人員正把天氣預測轉變成火警預報。

野火對于佛羅里達擴張中的郊區一直是個很大的威脅:曾被開墾用來種植農作物的郊區土地如今長滿了灌叢和樹木,在亞熱帶的氣候中欣欣向榮。佛羅里達每年12月到翌年5月是漫長的旱季,接下來的雷電季節又是美國本土中最劇烈的,更增添了火災的危險。刻意引燃的林火稱為“計劃焚燒”,可以降低這種風險,但得天氣恰當才行,因為熱風可能使火勢失控。
因此,氣象學家們試著把天氣預報與火警電腦模擬相結合,以推測計劃焚燒的火勢會如何發展。這并非易事,因為火會創造自己的天氣。例如,火的上升氣流會吸入空氣,產生風,助長火勢。但研究人員希望發明一種工具來告訴林務官員,該在何時何地放火,以及煙霧會如何擴散。
天氣預報前景尚好
那么,預報一般的天氣,例如大多數人生活中會遇到的寒流、毛毛雨和陽光,前景又如何?波爾德的大學大氣研究聯盟主席李察·安特斯說:正穩定進步中。
更精細的模式和更快的電腦將會加速這項進展。舉例來說,在美國一些主要城市進行的密集計算實驗計劃已經能夠預報24小時后的雷暴,且誤差不過幾公里。盡管這還不足以保證野餐或婚禮不碰上雷暴,但對機場來說已經很有用了。
新生代的衛星將有助于突破目前天氣預報的限制。如果計劃進行順利,從今年12月起,美國與中國臺灣合作的衛星,將借由接收全球定位衛星發送出來的無線電訊號來探索大氣層。這6顆微衛星將會收集穿過大氣后又進入太空的全球定位訊號,分析無線電波波速受到溫度和濕度的影響,創造出一幅包含這些大氣屬性的全球大氣圖。
另外有些衛星則會利用光對大氣層進行取樣。有一種稱為“激光雷達”的技術(LIDAR,全名“光線探測和測距系統”),運作方式就像一支光線雷達測速槍。它先發出激光脈沖,再偵測空氣分子和塵埃粒子反射回來的光線,借此測出風速。用衛星載送的激光雷達,可以在測量站稀少的大洋上空追蹤風跡,而大洋正是颶風和臺風的誕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