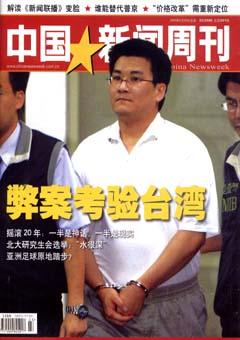陳永貴與“西水東調”
往 事
陳永貴由一個農民,而躋身中南海,的的確確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氣候需要。而其時的大寨已不是生產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典型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陽縣,原本是一個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小山村。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1963年夏天大寨遭遇洪災后,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不向國家伸手等待救濟,而是與天斗與地斗,三戰狼窩掌,展示了大寨人艱苦奮斗、改天換地的英雄主義氣概,使大寨一舉成名。1959年國慶10周年,陳永貴登上天安門城樓,見到了毛澤東;1960年,山西省委發出向模范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學習的號召;1961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大寨之路》的文章。中央最高機關報濃墨重彩的報道,感染了無數中國人。
1964年5月,毛澤東鄭重地提出農業要發揚大寨精神。他說:“農業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從此,大寨就作為中國農業的樣板樹立起來。而陳永貴也走入政壇:1967年2月,陳永貴當選為昔陽縣革委會主任。其后還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核心小組成員。1969年中共九大,陳永貴當選為中央委員。1973年中共十大,陳永貴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陳永貴當選為副總理。
陳永貴由一個農民,而躋身中南海,的的確確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氣候需要,而其時的大寨已是政治典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典型。
隨著陳永貴官位升高,在山西也產生了“兩個凡是”:“凡是陳永貴說的都一律照辦;凡是大寨、昔陽做的也都一切照搬。”陳永貴所主持的“西水東調”工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馬的。
“西水東調”工程的計劃,是從昔陽西邊,把向西流入黃河的蕭河水,東調到昔陽東邊的海河水系。廢棄西邊原有的三十多萬畝水澆地而保東邊的九萬畝水澆地,破壞了原有的水利設施,制造了新的水害。因此,工程計劃提出時,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術專家的反對。但是,山西省委的領導則以“寧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項目抹掉,也要保證昔陽這項西水東調項目”的態度,堅決上馬。結果,投資由原來的2000萬一直追加到9000萬,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計劃的三分之一。到“文革”結束后,這項“為大寨為昔陽爭光”的工程才停止。
“四人幫”垮臺以后,批評揭露這項工程的來信,紛紛送到山西省委和黨中央、國務院。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該報記者和通訊員合寫的通訊《昔陽“西水東調”工程緩建》,揭開了這個荒唐工程的蓋子。該報并配發了社論《再也不要干“西水東調”式的蠢事了》。社論尖銳地揭示了這樁“蠢事”產生的根源:
昔陽“西水東調”工程弊端叢生,工程技術人員意見很大,為什么能夠說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幾年,直到粉碎“四人幫”三年以后才停下來呢?這里,另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某些領導同志的封建家長式統治。我們有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又不聽取專家的意見,偏要號令一切,指揮一切,甚至用個人的喜惡來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樣一些同志捧著他,護著他。明明他的主張荒謬,卻要連聲稱贊,執行不誤。于是,設計改來改去,壩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謬誤取代,科學為獻媚遮蔽。你要堅持不同意見,那就是“立場問題”“態度問題”,甚至是“搞陰謀出難題”。不幸,這樣的事情,前些年在我們國家還是不少的。
陳永貴這時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所以《人民日報》還不敢直呼其名,只是在社論中提到這個錯誤工程的重要教訓是“某些領導同志的封建家長式統治”。報道發表后,《人民日報》收到了雪片似的來信。
稍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些記者成立聯合調查組深入山西,同山西新聞媒體合作,進行了四十多天的采訪,寫成了兩組內參稿。一組披露了十年來大寨的真實情況,一組則從陳永貴所奉行的“要念大寨經,還得昔陽人”和“學大寨,趕大寨,手中無權學不開”的觀念出發,披露其在干部任用上的家長作風及幫派路線。這兩組內參稿件,為中央總結“農業學大寨”的經驗教訓提供了資料。
對“西水東調”工程的揭露,為“農業學大寨”奏響了哀歌,也給多年來所提倡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行生產的“政治模式”敲響了喪鐘。
(作者為《炎黃春秋》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