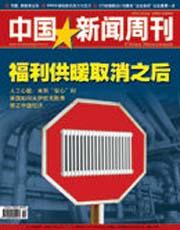北京不解波西米亞
顏 榴
一出中國百姓不熟悉的高水平的百老匯音樂劇在中國演出受冷遇是可想而知的。可《吉屋出租》在中國的尷尬并不是觀眾對百老匯或異域文化的陌生,而是在中國甚至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把一場真正專業的高雅演出介紹給觀眾
新年的第一天去看《吉屋出租(Rent)》,一進劇場就喜歡上了舞臺上的布景。鋼筋架構的高臺與漏出磚墻的后區,將人帶到街角的某一處舊廠房,至于這廠房是在紐約、倫敦抑或中國,倒不要緊,恐怕東西方的窮藝術家們看了都會覺得是回到自己的“窩”了。墻上的涂鴉暗示出紐約的背景,藍色調鋪墊了某種憂傷的氛圍。
這的確是個有點悲傷的故事:窮藝術家交不起房租,被房東驅逐,圣誕之夜饑寒交迫、黑暗沉沉。幾對戀人中,職業和性取向都不入主流,脫衣舞娘、同性戀,還有吸毒的經歷、罹患艾滋病的身體,分明是問題青年,怎么能在美國百老匯的舞臺上連演7年,贏得中產階級的贊賞呢?其實,《Rent》并不灰暗,相反倒昂揚,它所吟詠的人在逆境中尋求愛來作支撐也正是普世大眾的需要。
一出波西米亞人的音樂狂歡
“愛情買不到,但可以租得到,你是我的新租約。”這愛情宣言,含著鮮明的美國特色,從波希米亞的藝術家口中唱出,更是一點也不稀奇。所謂“波西米亞人”,原指波西米亞一地的吉普賽人,他們居無定所卻愛苦中作樂,后來泛指那些未成名的窮藝術家。他們一般都年輕愛玩,風流多情,常常揭不開鍋,偶有進項便盡情揮霍。在常人看來這可不是什么理想的生活,所以波希米亞人的境界就取決于他們是否真有藝術的追求。19世紀末時,世界藝術的中心在法國巴黎,20世紀中期時則移至美國紐約,巴黎左岸和紐約東村成為名聲赫赫的波西米亞人聚集地。普契尼有出歌劇《波西米亞人》正是描繪巴黎藝術家的生活,已成經典;100多年后,美國人拉森干脆在情節上直接效仿,音樂上大做文章,給紐約社會的邊緣人一個暢抒胸臆的表達,創造出音樂劇《Rent》。
《Rent》的音樂是成功的,它混合了搖滾、抒情民謠小品、節奏藍調、福音音樂以至探戈……豐富的音樂類型傳達出人物的多種情緒。如何把生活化的動作變成歌唱,一向是國內音樂劇的難題,除了做空洞的抒情似別無他法,《Rent》在這一點上顯得游刃有余。比如打電話,似吟似唱,處理得充滿諧趣。在說與唱之間,在一段段歌曲之間,《Rent》銜接得隨意自然,滿舞臺游走的是被音樂節奏所控制的人的精魂,卻感覺不到音樂的刻意。
當然不只是音樂好聽,在那樣一個看似雜亂的舞臺上,人物個個率性為之,卻統一在一個高低錯落的活動空間里,疏密有致。燈光打來,隨著人物的情感起伏變化多端,切換之迅速和到位,可能是國內更難做到的。說《Rent》是正宗百老匯音樂劇,名符其實,不單是技術上,而是因為在這樣一場貧病交加的波希米亞人聚會中,竟無多少頹唐色彩,溢出的多是快樂、自信,難道是美國人的天性就能如此地超脫困境?
在民族性上這雖然屬于健康的人格,藝術上卻有點問題。很難解讀出,以自身經歷寫完這部戲還沒來得及觀看就病死的拉森是因什么精神從外百老匯躍居百老匯并拿下諸多獎項的?這個35歲的作者僅以糖精取代苦澀,就能使中產階級流下感動的淚水?今歲蒞臨中國的《Rent》還是10年前的那個腳本的原意嗎?不得而知了。
至于莫文蔚,早已成為亞洲巡演的焦點,表現如何呢?賣力,卻不動人。主要體現在歌唱上,因為與美國歌手同臺,差距便很明顯,嗓音不是問題,調門卻不怎么準。早在宣傳早期,亞洲市場以莫作為票房號召,但報道只是一味宣揚莫“魔鬼身材,向老外賣弄風騷”之類,劇中也確實看到莫的此種狂放表現。
《點燃我的蠟燭》和《鋼管舞》一段,莫文蔚在舞蹈上下足了功夫。但事情往往是,在中國人眼中別有一番另類風采的莫文蔚,一俟掉到洋人堆里,掉到一群磕藥的藝術家堆里,她竭力接近的放浪還是不如人家的隨意來得自然。當然這也不是她努力就能做到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先期決定了。也正如此,莫的英文雖然已經很好,但要唱出劇中曲調的味道尚屬難事,要融合進劇中那一群美國人中就更需要時間。不過,也許人家就要這樣一個東方的骨感美人來裝飾他們的戲劇也未可知。
音樂劇和演唱會的區別有多大?
因為是一出百老匯的音樂劇,所以免不了有些要求,那是對演出質量的綜合考評。可是我遺憾地發現,在我被音樂吸引,手舞足蹈興起時,周圍的觀眾的反應大多是冷淡。那些在開演前買了望遠鏡和螢光棒,興沖沖走進去的人們,恐怕是失望了。我們的長腿莫文蔚除了一個勁跳舞和對老外“搔首弄姿”外,歌唱得實在是差強人意;況且劇中的曲調我們既不熟悉,節奏也很生疏,很難揮得起熒光棒來。
一出音樂劇和演唱會之間究竟有多大區別呢?許多人有這樣的疑惑。以莫來做招牌,引來的必然是喜歡抒情小調的流行音樂的聽眾,然而《Rent》的音樂強勢在搖滾和藍調,這其實是中國小資的趣味,但他們沒有被告知《Rent》里有他們想聽的這種音樂,于是便損失了最能有共鳴的觀眾。
而北京的北展劇場不是個理想的音樂劇劇場,劇場太大,必須要裝滿人才夠有氣派,可中國人看音樂劇的習慣根本還沒有建立起來,哪來那么多的觀眾呢?選擇了大的劇場,票房卻無法跟進,第二場(還是元旦夜)便有了許多空位,顯出冷場來。
這樣一出全英文的演出,曲目多、唱詞多、節奏快,加之又是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對英文程度低的中國百姓而言普遍難懂,可演出方偏偏將配有唱詞的節目單定出高價,薄薄的冊子賣到20元,大部分持100元票進場的觀眾不愿意再花戲票1/5的錢,這一來,大部分的人就都如墮霧里,對臺上發生的事情處之漠然了。
北展劇場是個老劇場,專業性卻打了折扣。開場鈴響3遍到開演之后場燈一直亮著,直至觀眾顧盼左右才滅掉。演出中不停地有人在前排走來走去,有的是要找位子,有的則可能想近睹明星風采,直直地立在前排不動,也沒有場務工來引導 這些讓坐在一旁的美國人監制看來非常費解。
這一切使我在享受了這場高水平的演出之后,在那么多人的大劇場里反而體會到一種孤單,一種未能與同胞一起分享他族藝術的失落,因為戲劇原本就是憑現場集體的狂歡而存在下去的。事實上,影響觀劇效果不僅僅是文化的差異,那些人為的干擾因素不是不可控制的,更絕非存在技術難度,但是這些年來,策劃或操作這些國外高水平演出的人又有誰在真正地在為觀眾考慮呢?
但愿百老匯的音樂劇屢次來華帶來的不只是演出市場和資本的滾動,而要啟動與之相對應配套的市場服務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