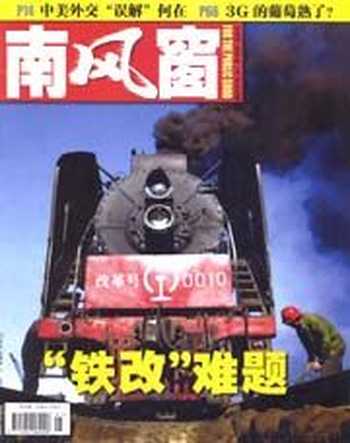“漸進”與“跨越”的路徑博弈
李紅昌
或許是被某些領域的成功經驗沖昏了頭腦,或許是把某些經濟理論視為圭臬,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尤其是一些不負責任的經濟學家開始宣傳這樣一種論調,即鐵路改革應該遵循國有資本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非競爭性領域的經濟學原則,從局部向整體,從邊緣向核心,從漸進到突變,在不影響鐵路建設與發展的前提下,有序地實現中國鐵路的改革與重組。
“國進民進”與“國退民退”
按照一般的經濟學理論,政府與市場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也是如此。由于民營資本在競爭性領域甚至非競爭性領域的效率都比國有資本效率高,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比計劃經濟體制更能激勵經濟主體努力工作,不斷提高經濟績效,因此,把競爭性領域甚至非競爭性領域開放給民營資本,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就鐵路產業而言,應該說,向民營資本開放市場不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根本性的問題反倒是,鐵路國有資本應該不應該退出,鐵路國有資本應該不應該進入?
單純對立地看待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將對立的觀點引入鐵路產業,就可能誤導改革。鐵路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的,更多的是一部“國進民進”或“國退民退”的歷史,而不是一個“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的進程。
林曉言博士認為,鐵路產業與其他產業不同的地方,或者說鐵路產業有趣的地方就是,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更多的是一種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如果考察一下歐盟鐵路、日本鐵路、韓國鐵路,甚至美國、加拿大、印度、阿根廷,我們都會發現民營資本進入鐵路產業的前提是國有資本的大量進入,國有資本大量進入的結果是民營資本在該領域的劇烈擴張。
正如我們以前所主張的那樣,無論是“網運分離”模式還是“網運一體”模式,無論是BOT模式還是特許經營模式,我們都需要合理地匹配國資與民資的關系,回避政府職責的中國鐵路改革肯定是不成功的改革,否定市場作用的中國鐵路改革肯定是成本高昂的改革。
整體改革或局部改革
整體改革或局部改革,反映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思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迄今,國內學術界或鐵路主管部門提出了若干種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鐵路整體改革方案,其中一些改革方案得到了實施或部分實施。
這些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方案、“網運分離”方案、組建區域公司方案、跨越式發展方案等4種方案。鐵路局部和漸進的改革適合于某些盡頭局如烏魯木齊局等,或許也適合于諸如京津城際、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但絕不適合于鐵路整體的改革與重組。
鐵路跨越式發展方案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思路,鐵路改革重組必須在生產力布局調整完成之后,或者說,鐵路改革重組不能超前于生產力布局的優化整合進程。2005年3月份,鐵道部撤銷了全部鐵路分局和大規模建設客專網等,雖然社會反響平平,但不能不說這是一次帶有整體色彩的革命性變革,因此值得贊許。
可惜的是,跨越式發展方案在整體性上仍有欠缺,特別是該方案不重視整體交易規則的建立,不重視市場資源的挖掘,過度依賴鐵道部的力量,缺乏統籌安排,使跨越式發展方案顯得十分粗糙、功利、隨意和局促。
鐵路是典型的網絡型基礎產業,忽視這一點就會形成錯誤的“以增量換存量,先局部后整體”的改革思路。鐵路的網絡經濟特性會使任何一家其他類型的鐵路企業都無法在鐵路產業中生存,它們的命運都會控制在鐵道部及其所屬鐵路局的手中。合資鐵路公司的經驗表明,如果不形成合理的調度指揮權生成機制,如果不形成合理的財務清算生成機制,處于鐵路網絡中的單個鐵路運輸企業就根本無法按照市場經濟機制進行運作。
實際上,有學者認為,如果鐵道部不進行整體的、存量的改革,即使客運專線公司擁有某一區段的調度指揮權,也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因此,各客運專線公司在目前格局下,調度指揮權只好集中統一在鐵道部運輸局手中。可見,鐵路進行增量改革的后果只會形成更大規模的存量,進一步增加而不是減弱了鐵路改革的難度。鐵路改革的順序不能與一般工商企業相同,整體的、一次性的、存量的改革是具有網絡特性的鐵路產業所必需的。
可以說,缺乏整體發展思路的鐵路改革肯定是失敗的改革,缺乏雷厲風行魄力的改革也肯定不是成功的改革。
缺失的公共治理
記得日本富士通綜合研究所上席主任研究員柯隆先生曾說過,中國現在似乎每個人都有怨氣,似乎每個人都是改革的受害者。反觀中國鐵路,似乎沒有人愿意為鐵路改革盡力,似乎沒有人愿意損失自己的哪怕一丁點兒的利益,大家都害怕成為改革的受害者。
中國鐵路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真實寫照: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產權配屬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已在所難免。問題是,我們現在最需要什么樣的機制來推進中國鐵路的改革與發展進程?答案卻很簡單:透明的、法制的公共治理!
社會利益主體越是多元化,矛盾沖突就越是顯著。公共治理平臺是一種決策商議機制,體現并平衡利益集團聲音和主張,集中矛盾與協調沖突,是一種民主治理與投票表決的機制。其他網絡型基礎產業或壟斷產業如民航、石化、電力、公路、電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缺少基本的公共治理元素,中國鐵路作為“最后的改革者”,不過表現得更明顯而已。如果缺少公共治理的營養,就像美好的愿望孵化出刺目扎手的怪胎、嚴肅的話題演化出下流的笑話一樣,結果讓人驚詫、懷疑、失望。
假如我國鐵路僅僅停留在對西方科技的吸收層面,而缺乏制度層面的激蕩與提升,沒有相應公共治理模式的保障,政府邊界和市場邊界沒有得到清晰界定,行政治理和市場治理沒有較好的耦合,那么,鐵路產業的前景實在不容樂觀。
韓國在建設漢城——釜山高速鐵路期間,通過引進整套的法國技術,開展消化、吸收和創新工作,韓國目前已經可以自己獨立生產并出口擁有自主品牌的高速動車組。這一過程中,國家的統籌規劃、政府的盡責、規則的鮮明嚴厲、公民的心平氣和,無不折射出公共治理的理性光芒。
鐵路改革與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了鐵路改革重組框架、鐵路生產運營、鐵路減員增效,甚至要精確到具體人頭和具體數字這樣枯燥而乏味的工作上,這也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鐵路改革都歷時很久,且有大量法律法規加以保障的重要原因。
中國鐵路存在的問題是多層次的,國退民進的盲目、交易規則的缺失、利益集團的強大,都使鐵路改革與發展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一層凝重的灰色。進入攻堅階段的鐵路改革,考驗的絕不僅僅是智慧。在其他產業的改革可以和風細雨的時候,鐵路必須站在風口浪尖上;在其他產業“國退民進”的大變革中,鐵路國有資本沒有退卻的借口;在其他產業可以增量改革的時候,鐵路改革沒有局部試點的余地;在其他產業可以放心大膽追逐利潤的時候,中國鐵路依然要承擔公益性責任。
客觀地說,中國鐵路改革與發展的環境十分嚴峻,鐵道部的處境是如履薄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鐵路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局性的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但鐵路產業的特殊性就在于,與電力、民航、公路、電信等網絡型基礎產業不同,它已經錯過了最佳的發展歷史時期。
幸運的是,我國所處的工業化發展階段、資源分布與工業布局東西錯位的空間格局、眾多的人口基數、高速鐵路的發展機遇等,為中國鐵路改革與發展提供了最后的一次機會,而如果錯過這次機遇,中國鐵路的未來孰難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