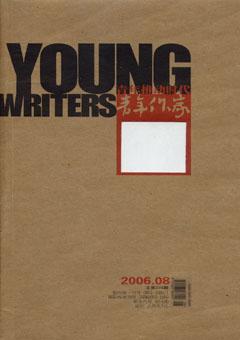城市欲望之書
倪 濤
《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個狩獵者的城市記憶》,如果這樣組合,它說的是上海的事情;而換一種組合方法:《七情六欲——上海1965—2005,一個狩獵者的城市記憶》,以這天翻地覆的40年為背景,所有的中國城市大都可以在書中找到影子。1965年是個什么樣的年份?作者為什么選擇這個年份作為回憶和記錄的起點?1965年我還沒有出生,對于我,那里是永久的黑暗和不可知,如果他人的記錄和講述可信的話,可以這樣描述: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日常生活開始有了些相對輕松的內容,而且在一些地方這種輕松似乎正在成為民間生活的主流;很少有人會想到,一場改變每個人命運和際遇的人造風暴即將來臨,花衣吹笛人正將魔笛舉到嘴邊,被魔法所惑的孩子們就將從城堡消失,沒有人能再把他們找回來。那年,本書作者王唯銘應該還是一個背著書包穿行于上海街道的少年,對即將到來的大事件一無所知,他注視著街角那個青年:“他的一身穿著是這樣的:格子襯衫包裹著上身;褲子將臀部繃得緊緊,褲子的褲管只有4寸,尋常的腳根本無法進入,因此,狹窄的褲管處裝了一根锃亮的拉鏈;腳上是一雙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頭皮鞋;發型是1965年最流行的兩種之一:大包頭,包頭上因為涂抹了許多凡士林而閃亮異常。”簡單的文字,細碎而富質感,還有一絲若有若無的揶揄和嘲諷;把這樣一個人物置于那個我所不知的年代,其中彌漫出的貌似真實的虛構氣息讓我迷惑而出神。從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早中期,960萬平方公里上發生了多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這些似乎不是本書作者所關心的,換種說法,這是一本關于小人物和小命運的書,在總體話語語境中被忽略的,正是作者所試圖還原的。
于是,這些詞語和事件成為敘述的線索:毛澤東逝世、《拉茲之歌》、麥克·哈里斯、鄧麗君、礦石收音機、手抄本、讓·雅克、FEC、阿里巴巴和彈吉他的張行、費翔、崔健、G30錄相機、出國潮、股票和楊百萬、重金屬、踏腳褲、中生代、新人類、SUV、波波族、拍攝暴民、文身和打洞、無情無性和有性無情……如果把這些視為關鍵詞的話,在這些關鍵詞的背后,激蕩著一個叫上海的中國最發達城市近40年的心緒,而這萬千思緒都由一張張備不相同的上海面孔來表達——那些閃爍在深宅大院里養尊處優不可一世的面孔:舊時代的寵兒、新中國一系列革命運動的被觸及者、轉型社會中世俗生活方式的領導者和萬念俱灰的感官動物;那些躲閃在狹窄里弄中渴望有朝一日出人頭地的黯淡的面孔:曾經的底層人群、新社會主流價值傳播者和革命運動的中堅、如今以精英價值觀為核心的科層社會中再次被邊緣化的階層;那些沐浴在新世紀光線中的長著絨毛的青春的上海面孔:熟諳英語或其他廣泛使用的外國語,年輕的實用主義者們——這些面孔上,都有著一雙充滿欲望的潮濕的眼睛。在這個中國的時尚之都,欲望如潮汐,起起落落,永無休止。
王唯銘稱自己為“狩獵者”,這個稱謂對這部厚達四百多頁、三十多萬字的書的作名而言十分準確——首先,他是冷靜的,他儔個真正的獵人,在黑暗中逡巡,孤獨而敏銳;其次,他是肉感的,狩獵者和獵物的關系是身體和身體的關系,他的身體、身體的氣息和獵物融為一體,曖昧的愛、恨和對抗彌漫在他們中間;他還是無情的,狩獵者瞄準自己的獵物,滿懷激動、惋惜、成功感和嗜殺欲,在黑暗中,叩動了扳機。
在我們這個時代來理解中國的城市是困難的,因為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其前提是“了解”和“提問”,而能夠提供給我們了解和提問的城市模型實在不多。看上去我們還有一些叫“古城”的地方和城市巨變下不知因何而得以幸存的“舊城”,但它們其實大都只具備標本的意義而失去了世俗生活的印記,所謂的新興城市則更像姓名不同的孿生兄弟:高大的建筑和寬闊的街道,行道樹和中心花園,酒店和噴泉,懸掛于人行天橋上建設某某、歡迎某某、祝賀某某的大紅布標——站在街頭,一陣阮惚,錯認他鄉是故鄉。對來自官方的文字,我一直持有懷疑,在那些光滑的、輝煌的、政治正確的詞語后面,哪些東西被忽視、被隱藏、被改造了呢?這時,個人化的體驗、記憶和書寫就顯得尤其重要,花瓶打碎之后,復原的工作就是揀拾碎片。足夠數量的相似文本在同一時空中勾連、糾纏、互文,張冠李戴,矛盾重重,錯漏百出,這不正是多數人的情感狀態和欲望指征嗎?
書中的照片也在為這樣的書寫提供注腳。比方這一張:留分頭、穿西裝打領帶的男青年背著女朋友的小坤包,穿喇叭褲燙了頭發的女朋友戴著俗稱“蛤蟆鏡”的模仿麥克?哈里斯的太陽鏡,走在上海70年代末的陽光里。這樣的場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國大地上隨處可見,濫觴之地應該就是這過去的十里洋場。還有這一張:熱戀的男女在公園池塘的游船上肆無忌憚地熱吻,船也悠悠,水也悠悠。這一幕,上映的時間是我不諳世事的少年時代。攝影是溫柔的暴力,它只留下自己能夠看見并愿意留下的東西,照片之外的事物永久隱形,但即便這樣,這些照片也足夠提供時尚和欲望的線索,幫助我踏上通向過去的道路。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一部分在云南一個離省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度過,關于所謂時尚,我比較早的記憶是鄧麗君的歌、“蛤蟆鏡”和拎在穿喇叭褲的人手里四個喇叭的日本“三洋”收錄機,而那時,省城已經開始流行喇叭褲,而那時,遙遠的上海已經在讓·雅克空氣般透明的音樂中醉過去。我們那里管男流氓叫“火槍”女流氓叫“皮蛋”,對穿大檔綠色軍褲和黑色剪口鞋的敬而遠之——據說他們都是愛尋釁滋事的暴徒,有人因為跳“熄燈舞”被抓,有人被揮舞的大刀砍掉手指,每次“嚴打”,都會有我認識或者聽說過的某某被送到比那里更偏遠的西部,并被吊銷當時視若性命的城鎮戶口;有人開始冒著巨大危險“投機倒把”,“海外關系”成為女青年的最愛和含金量最高的關鍵詞;有一對相愛的中學生在山洞里喝農藥殉情,幻想一夜暴富的人們一次次血本無歸;說是紅茶菌能夠防癌,家家就堆滿了巨大的吐著黏液的瓶子,說雞血延年,就有人往自己胳膊上扎針注射,后來又流行氣功,“大師”成為法力無邊的代名詞和救人出苦海的活菩薩,還有“甩手功”祀“吼叫功”,每天清晨許多人在操場上甩著手大聲地吼叫——都沒有錯過什么,雖說趕上來的時間有早晚,所有的中國城市,大江南北,在大致相同的七情六欲里躍躍欲試、欲罷不能、欲火焚身、靈魂出竅,在對一個個欲望泡泡的追逐中淺吟低唱、徘徊彷徨、漸行漸遠。
“欲望手紙一樣簡單,人生黑洞一般神秘。”這句話是本書最后一章的標題。欲望手紙一樣簡單——不能缺少卻不被尊重,不可重復卻一再重復,被褻瀆者褻瀆,被拋棄者拋棄,亨利·米勒式的丑惡而性感;人生黑洞一樣神秘——也許,但有時也許未必盡然。在同一章作者還這樣說:“一種欲望超越了所有欲望。”——這種欲望就是最原始的欲望,性的欲望,甚至有時連性的欲望都消失殆盡。我們的人生從理想開始,想著尋找到只屬于自己的情感和體驗,卻發現情感已經是昨日黃花,那就只滿足欲望得了,可誰連欲望也變得不再有體感,就像隔著安全套的性——下降的人生,還剩下了些啥?
責任編輯席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