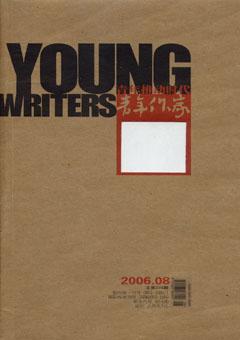要是鯨魚能飛(外一篇)
向祚鐵
黃昏時分,炊煙從各家的屋頂升了起來;村長從外邊趕集回來,帶了一些鯨魚苗給大家,讓大家發展鯨魚養殖業。養殖鯨魚的最大好處就在于等它們長大了,我們可以把它們的腦袋砍下來做剁椒鯨魚頭。鯨魚苗裝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瓶中,它們長著一層光滑黧黑的皮,大約有無名指頭大小,像蝌蚪一樣在瓶中游來游去。大家將這些鯨魚苗分了,各自帶到家中分別喂養。
鯨魚苗長得很快,但是麻煩也開始出現了。以我為例,我最初把鯨魚苗放在一個精致的眼藥瓶中,為了避免老鼠把它咬死,我把眼藥瓶掛在房間中央。第二天醒來,我就發現鯨魚苗已經把眼藥瓶撐滿了,它正在痛苦地想扭動一下身子。我趕緊把眼藥瓶敲碎,將它放到碗里;接下來的日子里,我開始搜尋家中的各種容器,以適應鯨魚不斷變大的身子:飯碗、菜碗、湯鍋、臉盆、腳盆……在搜尋容器的過程中,我有一個意外的收獲。我發現,以前我那些看似雜亂無章的各個器官需求其實都有一定的空間范疇,在生活中分別有序地對應著一系列的容器。
但是,鯨魚的成長速度不讓我有更多思考的時間。我每天都得為它尋找棲身之地而發愁,最后,我將它擱在了浴缸里。——但愿我沒有干這種傻事!第二天傍晚,當我收工回家的時候,就見我的小木屋往外繃得緊緊的,木板在嘰嘰嘎嘎地發響,終于一聲巨響,散架了。就見鯨魚腦袋擱在浴缸的這頭,尾巴搭拉在另一頭,正咧著寬大的嘴巴,樂呵呵地朝我喘氣。
這時候,我們大家都意識到,為了避免類似的禍患再次發生,我們得趕快想辦法把鯨魚送到河道里去,再讓它們沿著河道游回大海。
但是,怎樣將鯨魚送到河道中去,卻讓我們非常為難。鯨魚的皮只有頭發絲那么薄,皮下面就是肉。用繩子綁好抬它們走,這顯然會勒傷它們,甚至導致死亡,況且,鯨魚全身都是脂肪,軟綿綿的,油脂在繩套里滑來滑去的,用繩子也捆不住。最后,我們想到了一個辦法,就像船塢讓新船下水那樣,我們在通往河道的路上鋪設了長長的木板,木板上涂滿了油脂,然后讓鯨魚沿著木板滑往河道。
唉,想想我們村子里的情形吧,我們就像一群螞蟻搬運一條胖乎乎的蟲蛹,挨家挨戶地圍著那些鯨魚打轉;而我們的秧苗卻在田頭一天天地荒廢下去。好在我們最終把各家喂養的鯨魚都抬上了滑板,它們都滑到了河里,我們站在河兩岸,看著它們成群結隊地往前游去。
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快活時光。它們快活地追逐嬉鬧著,噴出一束束水柱,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沿途的村民都放下手中的鋤頭,站在岸邊饒有興趣地指指點點,同時,也向我們打探這些鯨魚當時的成長情況,每逢這種時候,我們就忘記了這些鯨魚當初帶給我們的麻煩,就好像看著兒子戴上博士帽的畢業照片,我們總忘記了當初把他拉扯大的辛勞,總是帶著一種幸福的辛勞之后的語調談起它們當初是怎么折騰我們的。
然而,令人揪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鯨魚還在繼續長大,河水已經擱不下它們的身子了。它們再也不能自由沉浮了,前些天,每當它們將穹隆的腦袋從水底緩緩浮出,岸上的人們總是屏住呼吸微張著嘴,看白花花的水沫沿著它們的腦袋往下流,然后發出一陣歡呼聲。但是,現在河水已經顯得太淺了,鯨魚的嘴巴老是露在外邊,噴出來的水柱也都撒在了自己身上,這讓我們怎么看都覺得別扭。為了讓鯨魚繼續自由沉浮,我們采取了緊急措施,先是把兩岸的水田挖開口子,把水全部放到河道里去,然后,在征得女人同意之后,我們男人都解開褲帶,一起朝著河道,將尿液全部射到河里去,為了保證足夠的射程,那些老年人都憋紅了臉;有人甚至還因此懺悔似地告訴大家,他悔不該今早去上廁所的。——盡管大家都努力了,但是,鯨魚的處境卻沒有得到有效改善。而最新傳來的消息是,聯合國救援小組的采冰船還剛從南極洲啟程,問題是,等這些冰塊運達我們這兒時,已經是冬季,這些冰塊未必能夠化成水,將鯨魚漂浮起來。
而這些鯨魚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厄運牢牢盯上,它們仿佛中了魔,在現有的困境中還是一味地長,它們仿佛就知道長大這一種生活方式似的。眼見它們一個個地困在河道里,肚皮無可奈何地耷拉在石頭尖端處,張著它們又寬又大的嘴巴,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我們持久的絕望情緒終于變得焦灼起來。不知道是誰最先傳遞了這種情緒,有人在下面小聲地嘀咕了一句話,這句話很快就在人群中傳開了,并且越來越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最終,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喊出了很多天以來一直就憋在心頭的愿望:“唉,要是鯨魚——能夠——飛——”
偏偏是第91天你捏疼了我的乳——姜濤語錄
最近,我有了一個男朋友。他是我們系里的,他比我高一屆,我們同上一門選修課。有一天,他來晚了,他見我旁邊有一個空位子,他就請求讓他坐那里,于是,我把我的書包移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坐下后,向我要了幾張紙做筆記,不久,又向我借鉛筆和橡皮,我也給他了。課間休息時,他又借我的筆記本看,于是他就知道我的宿舍和我的名字了。課后,我就走了。此后,上這門課的時候,他就挨著坐我旁邊。以前,我經常和我的一位女伴坐在一起。現在,她坐在我的另一側。他經常以餅干作早餐,課間休息時,他請我倆一起吃。因為他的神情有些張皇,所以我就吃一點,但我的女伴吃得比我多。他經常將系里老師的各種趣聞軼事講給我們聽,女伴聽了常“吃吃”地笑,將餅干屑噴到了桌面上,我低著頭吃餅干,有時也笑。開始時,我們三人坐在后面的一排座位。有一天,女伴坐到班里其他女同學那兒去了,從此,就我倆坐在一起了。
不久后的一個傍晚,宿舍管理員廣播說有人找我,我走下樓,看到他在樓門口不停徘徊。他手里捏了兩張票,他要請我去看電影。我說我明天要考試,去不了。他說電影非常好看,得了四項奧斯卡獎。他說:“去吧,去吧,還是去吧。”他說得很急切,我又擔心被班里的女同學看見,就快步隨他去看電影了。男主人公躺在床上,臨死時不斷地呼喚著情人的名字,情人緊緊地握著他的手。突然,他握住了我的左手,我把手往回拿,整個手掌恰好落在他的手掌里,他眼睛筆直地看著電影,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于是,我不動了;他就將我當作女朋友了。
他送給我一個心臟形筆記本,在扉頁上寫著:To my dear little Sparrow。有一天晚上,他將我的頭摟在胸膛里,低聲地叫道:“小麻雀。”我沒做聲。他又說:“你就叫小麻雀吧,好不好?”
我說:“好。”
從此,沒其他人的時候,他就叫我“小麻雀”。
他又告訴我,他家里人都叫他的小名“龍龍”,讓我也叫他“龍龍”,他是南方人,[n]和[l]分不清楚,我腦子里總是當成“膿膿”,有時,叫他“龍龍”的時候,我都忍不住感到好笑。他覺得他的小名很逗,他也笑了。
今天,他要我晚上去他宿舍。我說我不想去。他說,反正遲早要讓大家知道的,而且大家一直在一起上課,都是熟人,沒有什
么可怕的。晚上我上完實驗課后,時間有點晚了,我向男生宿舍區走去。他所在的宿舍樓藏在男生樓群的最里面。晚自習剛結束,男生們有的騎車回宿舍,有的拎著開水瓶去打水,在樓與樓之間的空地上有不少人在走動,我忽然覺得,周圍都是男生,就我一個是女生。
我找到了他的宿舍樓。他住在三樓。我們班上的男生住在二樓。我在二樓的樓道上碰到了我班的生活委員,他拿著漱口杯往水房走去。他會意地微笑著向我點了下頭:“你好。過來了?”
我也點了下頭:“你好。”
他急忙從我身邊走了過去。我也匆忙來到了三樓。
男朋友的房間在走廊的那一頭。走廊上掛滿了褲子、衣服,還有好幾條內褲,由于剛掛上,衣服不斷地往地面掉水滴。過道的燈本來昏暗,被衣服遮掩后,顯得更暗了,因此走廊看起來比較長。
為了不淋著水,我貼著右邊墻壁走。有時,濕淋淋的褲角碰到了我的額頭。我低著頭走。突然,我感到右邊仿佛抽空了。原來是一個男生打開了門。他手里端著臉盆,盆里裝著他洗完腳后的熱水,里面還漂著襪子,騰騰地冒著熱氣。他斜著腦袋看了我一眼,趿拉著拖鞋“劈哩叭啦”向水房跑去。到水房門口時,他突然大聲地唱了一句:“你總是心太軟,心太軟——。”男朋友房間的門是關著的。我在外面站了好一會。這時,那個男生又回來了,他又看了我一眼,走了。到他宿舍門口的時候,我以為他又會唱歌,但他不唱歌就進去了。我敲了門。門開了,是他們宿舍的老二。老二對我說:“老三一直在等你。剛才他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你等會兒吧。”
他們的房間地面上有很多廢紙和方便面的塑料袋,書桌上堆滿了書,還有一小堆桔子皮。老五坐在床沿上洗腳,腳掌在不停地打水,同時彎著頭在桌面上吃方便面,老五的耳朵塞著耳機,沒有注意我進來。男朋友此前向我要了張照片,說要我看著他晚上睡覺,老五右手拿著勺子吃方便面,左手拿著有我照片的像框,因為吃面,他脫下了眼鏡,所以他就瞇縫著眼睛,靠得很近地仔細看我的照片。照片是我暑假爬上南岳山頂拍的,我當時挺著胸,做了一個勝利的V字手勢,我擔心老五的眼睛會碰至到我的胸。
老二走了過去:“來,我喝口湯。”說著,老二就把碗拿了過去。老五的一口面還沒吃完,因此,余下的面條晃晃蕩蕩地從碗里抽了出來,就好像在他下巴長了一撮黃胡子;湯汁滴滴灑灑地往下掉,有些油滴滴到了像框的玻璃上,遮住了我的臉。這時老五看見了我,慌忙去床上的手紙筒扯下一塊手紙,擦我照片臉上的油。
老二喝完面湯,看到我在看著他們,他把碗還給老五,說:“你坐吧。”他拿了一張凳子過來,讓我坐。凳面上踩滿了腳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太臟了。”他從桌子腳下撿了一張報紙,在凳面上用力地擦了幾下:“你,坐吧。”
我坐了一下,又站起來了。老大和老四正在計算機上玩《街霸》格斗游戲,還有另外兩個其他宿舍的人在觀看。老大用和尚上陣,老四用安妮上陣。和尚的上半身裸著;安妮的身子很苗條,穿著泳裝,腳上穿著高跟鞋。和尚與安妮打得很激烈,他們的招法都很靈活。雙方拳來腳往,有時安妮踢出連續的掃蹬腿,觀眾們就叫道:“老四,別老攻下盤呀!”和尚退到了一邊,突然朝安妮的小腹處發出了一道沖擊波,安妮躲過了,她還落地未穩,和尚又發出了一道沖擊波,擊中了。旁邊的人都興奮地催促老大:“快點發,快點發!別讓她喘氣!”老大讓和尚不停地發出沖擊波。突然,安妮一個跟斗騰空而起,踢了一記漂亮的飛腿,用她的高跟鞋尖狠狠地踢在和尚的襠部。安妮又向和尚的襠部踢去,和尚避開了。和尚攻了上去,他扎了個弓步,右拳直統統地向安妮的小腹處打去,沒等安妮做出反應,左拳又直筒筒地向她的小腹處打去,大家都靜了下來,微張著嘴,嘴角帶著僵滯的笑意,聚精會神地看著和尚擊打安妮。安妮因為遭到連續擊打,行動遲緩了。所以和尚一拳接一拳地重復擊在她的小腹處。安妮把腰往前挺了一挺,往后僵躺下去,和尚耍了個漂亮的旋風腿,從高空重重地落了下來,單膝跪在安妮的小腹上。和尚贏了,咧著嘴笑。
剛才,他們忍著沒笑出來,看到和尚咧著大嘴,他們彼此看了一眼,忽然心領神會地爆出笑聲來。他們越笑,笑得越厲害。他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合不攏嘴。
老四用手捶了一下老大,喘著氣說:“老大,你的和尚也太陰了!”
忽然,從我背后的床上探出一個腦袋,原來是老六,剛才他一直躲在他的床簾里面,我沒有注意到。
老六沖著他們叫道:“老大,你是不是讓你的和尚在安妮前面,盡了男人應——盡——的任務?”
仿佛聽到了某句暗語,大家又暴笑起來。老六看到了我,吐了吐舌頭,腦袋“嗖”地縮進床簾,就仿佛一只烏龜,將腦袋伸出殼外,受到驚嚇,又馬上縮進烏龜殼。這時,男朋友回來了。他拿著一束玫瑰走了進來,他看到大家在笑,看了看手上的花束,又看著大家,于是也就羞澀地但又不無得意地笑了。
男朋友是學工程的,他也經常以“文人”、“騷客”作為自己談笑的資料。但在骨子里頭,他卻不認為自己方頭方腦,像一塊磚頭,相反,他甚至認為自己是頗有那么一點詩意的。他帶我來到樓外,去我們的那片草坪。他晃了晃手中的花束:“剛才我去校外買花,冷得瑟瑟發抖,就像玫瑰的花瓣一樣,在寒風中顫抖。”他說著,把花送給我。我接過花,并且“嗯”了一聲,表示對他的應答。我右手拿著花,他拉著我的左手,想快點走出男生宿舍區,到達那片草坪。他比我高很多,他的步伐比我的步伐大,他走得快,我跟不上,如果要跟上,我就得邁著小跑步。我小跑了幾步,很不適應。我把手掌在他手心里轉了幾下,抽了出來。他放慢腳步,看了我一眼,又拉我的手,我把手給他了。
我們來到草坪。由于天氣又干燥又寒冷,我倆又走得很快,胸腔與口腔都比較干澀。月亮很圓,他指著月亮說:“你看,今晚的月亮真圓,就好像是用圓規畫出來似的。”他抬著頭說話,鼻腔又澀,所以他的聲音在寒冷的空氣里聽起來仿佛很遠。我說道:“是嗎?——嗯,確實很圓。”我倆都沒說話,我低頭看著影子。花束的影子投在草地上,像一個洗耳球,我的右手則握著這個“洗耳球”的柄嘴。
男朋友背過身去,用手掌擋在嘴巴的前面,他輕輕地對著手掌哈了一口氣,聞了聞嘴里的氣味。他悄悄地從口袋里掏出口香糖。他在一旁嚼著口香糖。我繼續看著地上的影子。有時我的身子動了,影子也就動了。男朋友嚼口香糖的聲音,有時大一些,有時比較輕微。
突然,他摟住了我的腰,讓我的頭靠在他懷里。他摟住我,輕輕地搖。我也伸出雙手,去摟他的腰。因為天氣冷,我倆的衣服都穿得很厚,他又長得粗壯,所以我要努力才能合抱住他的腰,——就好像游客為了測出一株大樹的合圍,用勁地張開雙臂去箍樹身一樣。他俯下身子,來吻我。這時,我雙手就摟不住他了,雙手被撐開了。我把雙手垂了下來。他的嘴唇放在我的嘴
唇上面,兩人的腳挨著;他彎著身子,我站立不動。
他將右臉貼在我的左臉上,他的臉很冷。他的臉在我臉上輕輕地摩挲。然后,他吻我的左臉,有時,他用舌尖輕輕地舔我的臉,所以,當他的嘴唇離開之后,我的左臉又涼又粘。當他吻到我的耳朵旁時,他鼻息的聲音很響,可能是因為天氣太寒冷,所以鼻息的聲音顯得突出。他不吻我了,他把臉龐擱在我的嘴唇旁。于是我就吻他。我有時也用舌尖舔他,舔到了小沙粒,在牙齒間咬得發響,我把沙粒吐了出來。
他說:“怎么啦?”
我說:“沒什么,是沙子。”
他笑了一下說:“一定是剛才我去給你買花時,外面的風沙刮的。”
他雙手捧著我的頭,在月光下看了一會兒,突然用雙手摟住我的腰,頭下腳上地倒起來。這次,我因為右手拿著花,所以沒有像前兩次那樣,雙手繞著他的脖子——以便他橫著抱住我。我倒了過來,我的右手拿著花,所以手背打著干硬的草地,擦破了皮。他慌忙地扶我起來。
我連忙說:“沒關系,沒關系。”
他說:“沒事吧?”
我說:“沒事。”
他說:“我們走走吧。”他拉著我的手,我默默地跟著他走。我倆走了好一會,我停下了。他看著我:“小麻雀,你怎么了?今天怎么不高興,是不是偷谷子吃,被農民伯、伯打跑了?”
他在逗我笑。我說:“劉嘯龍。”
這些天來,我一直叫他“龍龍”,所以突然稱呼他的本名,話剛出口就覺得空蕩蕩的,讓我一下子不知道接著該說什么。他看著我,等我說下面的話。我于是鎮定了一下,想跟他說,我倆最好分手算了。于是,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們,——我們還是算了吧。”
他體貼地看了我一眼:“對,對,天氣這么冷,我們還是回去算了。”
他拿起我的左手,在手背上吻。手背上涼嗖嗖的,就好像在手背的那一塊小地方刮了風。他走在我前面,我把左手伸到背后,在衣服上將他的口水擦干。
快回到我的宿舍樓時,他突然像記起了什么似的:“快看看,快看看花里面還有什么。”我從花束里拿出一張便箋。突然,我覺得里面的話語會與我倆最近看的一部電影里男主人公的幽默相類似。我站在路燈下,打開一看:“今天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它是我倆相識第91天——因為既不是第90天,又不是第92天,偏偏是第91天,所以它值得紀念。”果然,和我所設想的一樣。也不知為什么,我就是忍不住笑了,他見他的語句讓我笑了,也滿意地笑了。宿舍樓的大門已經關閉了,在門外,聚著一對一對的遲歸者。情侶們都在各自絮絮私語,有時,氣息從嘴里出來后,在燈光下看得很分明,大家各自說著話,互相不注意,就好像北冰洋上漂浮著一座座冰山。突然,管理員把門打開了,大家“哄”地一聲走進去了,男朋友說:“快進去吧。”我們向門口涌去,仿佛人很多。但是,很快,大家走向不同的樓道,樓道又黑又長,我們仿佛一支支探險隊,無聲無息地消失在迷宮的各條通道。我住在最高一層樓上。上這層樓的就我一個人。樓道的燈壞了,走廊是黑的,我扶著墻面,一步一個臺階地往上走。我聽得見自己腳步落地的聲音。我忽然想,剛才那些女同學們,她們就在我下面的各個樓道行走著,但我為什么聽不到她們的聲音?她們到底已回到宿舍呢,還是正在回宿舍的路上?也許,在黑暗的深處,壓根兒就沒有宿舍在等著我們,我們只是以“回宿舍”作為一個借口,得以在通道里不斷地行走下去,然后就慢慢地消失掉?
宿舍到了。我走了進去,她們都睡了,女伴一人開著應急燈,正在背TOEFL單詞。屋里靜悄悄的。她抬頭看了我一眼,笑著說:“好漂亮的花。來,讓我插上它吧。”我吃了一驚,把右手抬了一下,才記起了手中的花束。
女伴把花插在玻璃瓶里,我從水房打回冷水,再往臉盆里倒了熱水,我在洗腳,我低著頭,坐在床沿上,我沒有動,女伴打趣道:“好幸福啊,——現在還沉浸在那里面。”我吃了一驚,抬起了頭,她手里捏著一張小卡片,嘴里微動著背誦單詞,我穿上拖鞋,去水房倒水。
臉盆放在水槽里,我打開水龍頭,水流“嘩啦啦”地沖洗著臉盆,水房的燈壞了,沒有燈光,月光透過窗戶,靜靜地鋪在地板上,月光很自,使水房的暗處黑得更分明。突然,我想哭,眼淚順著我的臉頰流了下來。我在心里說:“沒關系,沒關系,就會好起來的,——只要習慣就會好起來的。”
責任編輯席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