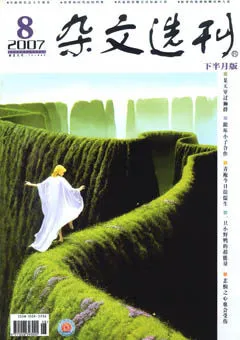給女兒十年后看的信·我們生而平等
小小:
我不確定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還能不能回憶起那天上午的經歷,所以,我要先給你記下這一段。
那天上午我們去了一家孤兒院,院里收了幾十個孩子,都是從正規福利院里接來的殘疾兒童。天恩和天豆高位截癱,只有胸以上的部分能動,每天要靠插導尿管來解決排泄問題;新新腦癱還有多動癥,平時需要用一根繩子拴在欄桿旁防止他自傷;小剛快六歲了,智力障礙,運動機能也有問題,走路會往地下倒,叫“姐姐”發出的聲音是“給給”;還有一個孩子每天要在矯正支架上待幾個小時,這樣經過許多年后,他也許可以正常行走;還有個天使一樣可愛的嬰兒,他和正常孩子的區別是生來只有一只胳膊……
我是來獻愛心的,所以在面對這么多長相可以用“丑怪”來形容,留著口水與鼻涕,號哭或傻笑的孩子們,我是用理智壓抑住了內心油然而生的反感與歧視,然后才能去接近他們的。
我的反感與歧視,來自于耳濡目染的社會觀念——對身體缺陷者、失敗者、地位低下者的輕視,這種觀念是在不知不覺當中接受的,所以成為我不由自主的選擇。我的理智來自于我的道德自省,這種后天的東西要壓住下意識的反應,需要花的力氣還真不小,而且多少令自己的行為有些變形。
你還好,你還沒有耳濡目染那些觀念,沒有讓它進入你的血液,因此你不需要內心掙扎。你很自然地正視他們的缺陷,坦然地表現出你最初的恐懼,又隨著熟悉很快地把它們丟到了一邊,和小剛玩到了一起,像和你的其他朋友一樣。你們一起逗弄一只螳螂,聚精會神。你們倆都興高采烈,幾個小時后,你們成了好朋友。他管小他一歲的你喊“給給”,臨走的時候,你執意要把你的玩具送給他做禮物。
你發自天然的善意與一視同仁,讓我欣慰又慚愧,這種貴如珍寶的品質,真希望你能保持始終。
人究竟是不是平等的——這個問題我曾思索多年。在這個世界,有的人出身富貴,襁褓之中人生就被鋪就了金光大道;有的人生自寒門,必須奮斗終生。有的人天生家庭殘缺,見不到父母;有的人卻被溺愛。有的人生在大城市,世面見得多機會也多;有的人長在小山村,畢生的理想可能只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人是平等的么?
但是,不管是窮人富人、正常人殘疾人,有一些東西,始終是一樣的。他們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上,是一樣的;他們對獲得美好未來的期待,是一樣的;他們作為人生就具有的尊嚴,是一樣的。
在昨天,你記得嗎?小剛和你玩的時候,那種由衷的快樂,那份對所玩的游戲、對獲得的友情的沉浸,與你有什么不同?他并沒有感覺到自己被打入另類,與你一樣,他不知道這個社會把他排到了最低的等級。他對這個世界的那份熱愛,你還記得嗎?
由于叢林社會法則,不少人對不幸者是嫌惡的。在我小的時候流行過一種哲學——殘缺不全者應該從小被消滅,而對這一哲學還有過符合邏輯的闡述。有些人覺得,與其讓他們成長之后因為自己的不勝任而遇到生存障礙,不如就不要長大,這樣對那些人更好。我想他們在做這一決定的時候,忽略了那些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忽略了他們同樣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探索和欣賞的興趣,忽略了他們即便遇到無數的生存障礙,都有活下去和活得更好的期待——就如同幸運者們自己一樣。這只與人如何看待生活有關,與自身的條件,其實無關。
你們都還小,很幸運地沒有被這個社會的所謂規則所扭曲。但我不確定在接受了許多人的行為暗示之后,在遇到冰冷現實的各種門檻之后,在他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歧視與拒絕之后,你們還能否記得這些最簡單的道理。如果看到這封信的時候,你已經不記得這個上午的感覺,那么你至少可以想像一下你自己是那個不幸者,去體會一下你對這個世界的感知與要求——其實太陽沒什么不同,樹木花草沒什么不同,這個世界的美沒什么不同。在所謂“社會”之外,這個世界天然給每一個生命的,沒什么不同。
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