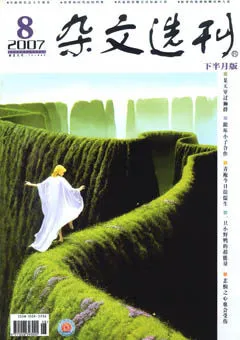短信平臺(八則)
一直以來,人們關注著長壽的話題,德國的短壽博物館用短壽來喚醒揮霍生命者,這是個好主意。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游戲人間的人、透支健康的人、糟踏青春的人,會不會有心靈的觸動?
這樣的博物館,在中國,也應該存在。
(讀2007年7月(下)《走進德國短壽博物館》)
——李樹青(廣東)
再大型號的x光機、再先進的數碼B超、再昂貴的進口CT、功能再齊備的核磁共振,也只能測看到人體的骨骼、血管、神經纖維和出現在它們中間的小小異變,卻無法看清人的品質、素養和善惡,要看清這些東西,只有聽其言觀其行了。
(讀2007年7月[下]《我的眼睛有了特異功能》)
——瀚瀛(河南)
我們長大了,我們成熟了,我們做事知道瞻前顧后生怕留下把柄,說話知道左思右想惟恐鬧出笑話。我們學來的知識越多,創新的勇氣越小;我們走過的路越長,越是不敢過獨木橋。都說“初生牛犢不怕虎”,長成了大牛,為什么反而怕貓了呢?
(讀2007年7月[下]《我們嚇壞了自己》)
——鄭俊甫(河南)
害怕死亡的人沒有真正懂得生活,對生活有過真實體味的人卻渴望死亡。這是永遠的邏輯謬誤但是一個滄桑的真理。
馬克·吐溫在文章中先后讓一個人選擇了歡樂、愛情、名望、財富。其實,這不就是現實中人們夢里追求的東西嗎?但是當以失去自我為代價而真正得到以后,卻想以一個渴望死亡的方式來解脫。誰之過?
(讀2007年7月[下]《生命的五種恩賜》)
——楚九(湖北)
對于公交車上的語音提示,我已經習以為常了,似乎應該理解為這是人家善意的提醒,卻從未想過不經意間所流露出的隱性的、潛在的貶低。“女”字當頭,初衷是彰顯女人的地位提升,“農民”做綴,想表達的是贊揚他們奮發圖強的精神,但是這樣的“好心”,反映的卻是“歧視”。
(讀2007年7月[下]《潛歧視》)
——劉昱非(遼寧)
兒童樂園有一種游戲:小朋友們拿著魚竿,坐在船上“太公釣魚”。只不過那些魚,不是長鰾的魚、有肉的魚,而是塑料魚、仿真魚。當然,這并非我們的“專利”,國外也有類似的“發明”,讓孩子們玩塑料蜻蜓、塑料蚱蜢……記得我們這代人,從小在河里摸魚蝦,在田間捉蟲子。而今,不過幾十年光景,童年記憶就開始裂變——人們無法親近那些活生生的花鳥蟲魚,只好親近花鳥蟲魚的“替身”。但愿那只是臨時的“替身”,不是永久的“標本”。
(讀2007年7月[下]《仲夏之夜。我們的星空哪兒去了》)
——潘德東(重慶)
老人以為敲門的警察是劫匪,警察以為老人遺落的鬧鐘是炸彈。生活中,你救了一個素昧平生的傷者,傷者的家人卻懷疑你是肇事者;你電話問候一下久未謀面的朋友,朋友會以為你心有所圖。“你是誰?你想干什么?”這個問題每天都要在我們腦子里回響,答案是:“我不是誰,我是社會公信力下降后誕生的一對雙胞胎,名字叫猜忌和冷漠。”
(讀2007年7月[下]《你是誰》)
——美麗羔羊(河南)
朱先生對死的達觀態度,強烈地沖擊著我們的“生死哲學”。在我們的現實中,往往是重死不重生,一個人可以渾渾噩噩地活,而一旦死了,就特別“認真”,特別“在意”,特別地要把活人“折騰一番”,活沒活出個樣子,死了卻要死得很“隆重”。這是一種可悲的生死哲學。我所希望的生死應該是:活應該好好活,認真地活,努力地活,活得精彩,活得無愧;死呢,不勞煩“母體”,還可以“化做春泥更護花”。
(讀2007年6月[下]《如果我死……》)
——劉誠龍(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