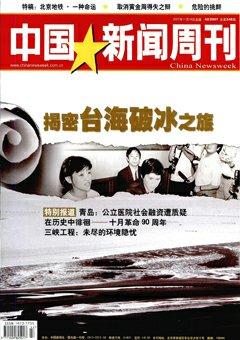日本:小澤沖擊
陳 言
小澤一郎辭職事件,彰顯日本在野黨的捉襟見肘。戲劇性變化讓人眼花繚亂,日本政治的多事之秋遠未完結

沉默寡言、能進敢退,被視為日本男人的美德。中國觀眾熟悉的電影演員高倉健在《追捕》《幸福的黃手帕》中扮演的男主角,表現的正是這種日本男子的特點。
日本的政治家并不一定沉默寡言,但不善言談的人不少。比如9月12日宣布辭去首相職位的安倍晉三,該退的時候毫不猶豫,沒有太多的言語。盡管當時有不少人說了不少風涼話,但和在野黨黨首小澤一郎的行動相比,安倍的武士氣質顯然高出了許多。
11月4日,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先是不滿意黨內高層對他要和執政黨“野合”(這是《產經新聞》11月4日報道中所用的語言),憤然提出辭呈。但兩天之后,在黨內高層的反復勸說下,小澤收回辭呈。在外界看來,對比安倍的干脆利落,小澤的舉動實在有些蹩腳。
日本《朝日新聞》 指出,民主黨人才匱乏,內部爭斗不斷。如果有17名參議員調轉船頭,投入自民黨懷抱,自民黨就能在參眾兩院取得多數。如果小澤真的辭職,很有可能造成民主黨的分裂,屆時自民黨在參議院也不戰自勝,民主黨奪取政權的希望將更加渺茫——這便是民主黨力勸小澤留任黨首的原因。
民主黨:亂了陣腳
日本執政的自民黨黨內有派系,這已經為中國讀者知曉。同樣,民主黨內也是派閥林立,爭斗激烈。
日本政治記者二木啟孝這樣分析民主黨黨內派閥:民主黨黨內主要有七個派閥,分別為小澤主宰的“一新會”、菅直人的“國家形狀研究會”、鳩山由紀夫的“實現政權交替之會”、前原誠司的“凌云會”、野田佳彥的“花齊會”、赤松廣隆的“圣殿”、舊民社黨的“友愛”。每個派系大致有30到50人。
二木同時指出,民主黨的派閥組織并不嚴密,但小澤派則抱團意識特別強。“不過,小澤派在黨內也有強敵,那就是前原誠司的凌云會。”
小澤11月4日提出辭職,民主黨上層頓時亂了陣腳。干事長、黨首代行、當過首相的重要議員,很快就去拜訪小澤,力勸其收回辭呈。高層們尤其擔心,小澤辭去黨首也就算了,但如果小澤旗下的“一新會”脫離民主黨,則勢必引發黨內地震。
在小澤的政治生涯中,稍不如意,他就會另起爐灶組建新黨。從自民黨分離出來以后,小澤組先后組建過新生黨、新進黨、自由黨,最后與民主黨合流,讓民主黨成為參議院中占有多數席位的大黨。如果小澤堅持與自民黨合謀,無疑能壯大執政黨的勢力,讓執政黨在參議院獲得多數席位。
不過,從小澤提出辭職的口氣來看,他本人似乎并沒有鬧分裂的意思。
小澤:選舉高人
民主黨真情地挽留小澤一郎,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小澤是選舉的老手。在小澤的引領下,民主黨取得了參議院選舉的勝利,民主黨進而希望小澤能帶領該黨在眾議院選舉再嘗勝果,奪取政權。
小澤的競選策略和許多日本政治家不一樣。在網絡已經十分發達,電視成為媒介主流的今天,小澤卻更強調直接去一線為競選造勢,通過召開小型對話會,把候選人的政治口號面對面地告訴選民。小澤似乎天生對媒體有戒備。對媒體的采訪,他盡可能躲避。能專訪到小澤的日本國內外媒體歷來就不多。
去年,因為民主黨議員用“偽造的電子信”攻擊自民黨,導致民主黨黨首前原誠司辭職,小澤接任。時值千葉縣選區議員補選開始,而民主黨在該地并不占優勢,能推出的候選人只有26歲的縣議會女議員。剛剛出任黨首的小澤,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不準開會,所有人一起下選區!”“把自己認識的千葉縣選區的人全部寫出來!”
小澤沒有坐民主黨的選舉宣傳車,而是跨上一輛自行車就騎去了選區,一個一個地接觸選民。小澤站在一只啤酒箱上向寥寥無幾的選民發表政治演說的照片登上報紙以后,反而吸引了日本國民的注意。那次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硬是拉到了比自民黨多955張的選票,成功當選。
千葉縣補選之后,小澤看清楚了日本選舉的路數,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了農村。他讓候選人走到鄉間去拉選票,“肯定會有一兩個人能聽到你的呼喊的。”小澤說。正是在這種策略主攻之下,民主黨取得了參議院選舉的絕對勝利。
眾議院選舉在即,民主黨顯然離不開小澤這樣經驗老到的政治家。小澤雖然不善演講,不太會和媒體溝通,但在眾議院選舉中,民主黨需要小澤的選舉智慧。
小澤時代:還沒開始,就已結束
小澤一郎在提交辭呈后,正式會見了日本媒體。記者會上,小澤談到了與首相福田康夫兩次單獨會談及執政在野聯合執政的可能,也說了他本人對自衛隊在印度洋為美國軍隊提供后勤補給問題的看法。但期間,他更多的是用非常嚴厲的言辭,批評一些媒體對他的誹謗。
最后,小澤話鋒一轉:“黨內拒絕了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提議,這等于對我不信任。政治已經混亂,我決意辭去黨首的職務。”
第二天,日本《讀賣新聞》以曝料的形式,公開回應小澤的批評。該報報道說,小澤與福田會談時,同意出任副首相,17名內閣大臣名額中,有6個將讓民主黨人士擔任。
言下之意便是:小澤已經接受執政黨的招安,但民主黨內部意見不統一,小澤才不得不辭職。
事實上,聯合執政的構想,并非出自福田和小澤。今年7月參院選舉結果出來以后,眼看著自民黨慘敗,安倍政權搖搖欲墜,《讀賣新聞》主筆渡邊恒雄決意親自出面,改變日本政治格局。他力主兩黨“聯立”,親自說服了小澤,又安排前首相森喜朗作為首相密使,與小澤進行了接觸,接著有了朝野兩大黨首領的兩次單獨會談。
11月6日,小澤接受了黨內對他的反復勸說,決定收回辭呈。7日,他又正式地見了一次記者。“我是個東北人,生性不善言談。以后要盡可能和媒體溝通。”小澤說。但接著,他再次批評了日本媒體對他的誹謗。同時,小澤也表明了他的決心:“帶領民主黨,竭盡全力應對今后的眾議院選舉。”
“以小澤先生的身體狀況和行事風格,就算是在選舉中民主黨獲勝了,他也不會擔任日本首相。”日本一家月刊雜志的主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小澤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體質較差。更重要的是,“小澤是一個‘破壞者,如若讓他成為內閣領班,他力所不及。”
1993年,小澤脫離自民黨后,扶植細川、羽田等人成為了首相,他本人并沒有直接拿下這個職務。執政黨總裁與內閣總理(首相) “總總分離”論,是小澤的一貫主張,但日本政治似乎還未能接受這個模式。
從安倍辭職開始,日本政治進入一個多事之秋。而秋天的麻煩,一直延續到了當今的冬季。小澤的進退,震憾了整個日本,政治的戲劇性變化讓國民很不適應。這也削弱了民主黨的信譽,人們開始懷疑民主黨的政治能力。
《產經新聞》政治部長乾正人不無遺憾地說:“我預感到,小澤時代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