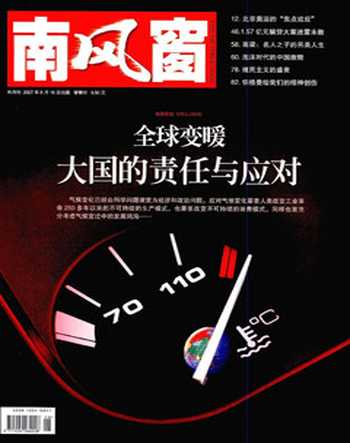當氣候成為政治
趙 義
當全球氣候變暖(核心是減排問題)成為國際社會核心議題之一后,各國的政治角力就不可避免。在“一超多極”的格局中,歐盟的態度最為積極,英國甚至試圖將全球變暖提升到危及國際安全的高度。
全球變暖涉及國際安全,實際上已經不是空談。西方國家普遍擔心,全球變暖帶來的干旱、歉收和熱帶疫病可能使亞洲、拉美、特別是非洲已經搖搖欲墜的政府更加不穩,成為窩藏“基地”和其他恐怖組織的“失敗國家”。海平面上升可能使孟加拉和越南等低地國家出現無數難民,給這些國家自身及其鄰國造成巨大壓力。只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接受將氣候變暖這一成因復雜、責任劃分爭論不休、但又日益突出的問題托付給安理會這樣一個可以作出制裁決議的機構。
中國在減排問題上的積極姿態并不遜于歐盟。中國“十一五”規劃制定了2010年前減排14億噸二氧化碳氣體的雄心勃勃的目標。盡管2006年的進展有些讓人難堪,但是即便最終只能完成規定目標的一半,中國所減排的溫室氣體數量也大大超過歐盟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的義務。
一則中國外交的理念傳統中“天下主義”的成分是很重的,中國外交無論怎樣為自己的獨特道路辯護,同時都會強調中國要對人類作出貢獻的精神訴求。即使是越來越講國家利益的今天,中國仍然堅持這一點。在減排問題上的積極姿態無疑可以為中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加分。
其次,中國并未主導國際政治的“決策議題安排”,但出招是加分的,并且給美國造成了壓力。對中國而言,通過發展解決問題是一貫堅持的具體主張。但中國外交越來越講“有所為”,因此中國選擇在這個議題上積極作為。至于美國,作為世界現有格局最大的“警察”,任何涉及自然資源的議題,戰略利益的考慮總是要放在第一位的。“中國、印度都不承擔義務,我們也不承擔”的說法,完全可以被視為一種說辭。
誠然,在氣候變暖問題上,有責任大者,有責任小者,但“各家自掃門前雪”根本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前人走過的發展道路,后來者可能還要再走一次。擺脫這個怪圈,改變發展模式,勢必要對國際現有政治經濟秩序進行改革,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利益重新劃分,自然涉及大國怎么理解和處理自己的戰略利益。
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可替代能源(從長遠看,這不是個問題,因為人類總能找到可以利用的能源),圍繞現有資源的國家沖突模式不消亡,任何減排的國際安排都可能變成雙刃劍,像氣候變暖帶來國際安全問題一樣,也可能成為國際沖突的誘因。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就是吸取了歐洲各國為了爭奪煤礦等自然資源而大打出手的歷史教訓而建立起來的,到最后甚至要往消除國家界限的方向發展。但這個道路走得又是何其漫長而曲折。誠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說,對日益減少的資源的競爭,已經削弱了各國解決沖突的能力。在減排問題上,最終考驗的是各國的合作精神。
因此,減排只是冰山之一角,底下的世界是什么,還不能說完全清楚。但這也正說明,圍繞氣候變暖問題的國際談判機制是必要的。政治家搞什么樣的“氣候秀”反而不重要。那些攻擊在氣候問題上最賣力人士之一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搞騙局的人,忽略了一條:在日益透明化的世界上,最高級的“騙子”是拿真問題來“騙”的。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深入人心的國際主流政治議題。
美國的立場也不會一成不變。其公共輿論已經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小布什任期結束后,美國外交政策可能會進行調整。影響很大的普林斯頓計劃就認為,在本世紀的未來歲月里,不會有哪一種威脅能夠居壓倒性優勢;相反,會出現的是形形色色、有時甚至是互動的多種挑戰所構成的“魔方”。這群美國智囊把全球變暖與核武器、印度和中國崛起、流行性疾病的威脅等并列在一起。
對于把中美關系看成是最重要的大國關系的中國而言,未雨綢繆是必要的。美國對中國改革議程的關注“熱情”之高,是眾所周知的。一旦美國這個“警察”加入進來,氣候變暖議題對中國的影響,也許會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