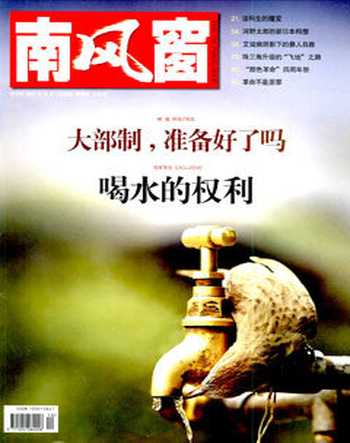珠三角升級的“飛地”之路
黎凌浩

近來,在距珠三角腹地100到300公里的環形輻射帶上,出現了這樣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聚集地”——它們雖地處粵北山區或東西兩翼,地理位置上與珠三角沒有任何關系,但這里的企業從珠三角搬遷來,園區的經營管理和招商一般由珠三角方面的人主持,產業園每年產生的工業產值和稅收,要與珠三角各地市平分……這里有人稱為工業園,有人稱為“產業轉移園區”,更多人稱它們是珠三角環形輻射帶上的“飛地”。
而企業在甲地,但產值、稅收仍然算到乙地、丙地的頭上,這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它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道理。
一方面,珠三角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高度聚集,空間、資源、人口、環境都難以為繼,亟須通過產業轉移騰出空間,以促進產業的升級改造;另一方面,中西部和欠發達地區有著令人羨慕的用地指標、電力負荷、環境容量和更加廉價的勞動力。
但是,當前的“產業轉移”要做到既符合經濟學原則、又適應實際國情,絕非一件易事。“飛地”,也許就是一種承載著各利益方諸多訴求的“中國式產業轉移模式”。
而更重要的是,它已經很現實地引領了一批勞動密集型企業由沿海向內地滲透,就像當年他們從香港、從臺灣、從東南亞,來到珠三角駐足。
“微不足道”的增幅回落
“企業呈規模外遷是在動搖深圳的根基!”近日,一篇關于深圳工業企業成規模外遷的媒體報道又挑起了各方敏感的神經。但事實上,這事并不新鮮。
據深圳貿工局牽頭展開的一項企業外遷調查表明,早在2006年6月,9家工業企業已經或計劃外遷。到今年6月,僅羅湖、南山、寶安和龍崗四區,已經計劃外遷的企業多達522家,其中已經外遷的499家。而企業外遷對深圳工業增速的影響在2%左右。
在引發外遷的各種原因中,工業用地短缺是最主要的。深圳土地面積只有1953平方公里,可供使用的建設用地只有900多平方公里,但現在已開發近700平方公里。按照傳統的發展模式,用不了幾年深圳將無地可用。企業外遷,成為部分用地量大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不得已的選擇。
無獨有偶,珠三角另一個工業大市中山市則同樣憂心忡忡。到今年連續5年,每年有1000多家有科技含量、有規模效益的企業落戶中山,但中山卻為找不到足夠的地塊和用地指標去安置這些企業而大傷腦筋。
作為地方經濟管理者,一方面中山經濟管理部門非常希望那些占地千畝、員工數萬但稅收貢獻一點點的制鞋廠、制衣廠能夠搬出去,騰出地方給這些有科技含量、有規模效益和豐厚利稅的企業;另一方面他們也在擔心,走一個企業少一塊產值,稍有松懈,中山在廣東“老五”的位置可能就會被發展勢頭更加迅猛的“老七”惠州攆上,現在算起來,也許這些企業還“一個都不能少”。
而499家企業在深圳又是一個怎樣的概念?2005年以來,深圳新登記注冊企業11萬余家(其中今年上半年就有2萬余家)。同期約4萬家企業吊銷營業執照和注銷工商登記;而今年1月到9月深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增加值2182.28億元,增長15.2%,增幅較去年回落了2%;而在一些中低產業外遷過程中,企業把總部、研發中心放在深圳,生產部門外遷,如此這般,這499家企業和2%的增加值增幅回落就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此外,近年來內地到珠三角“招商引資”的隊伍是一串接一串,開列的條件不可謂不優惠。可是讓他們納悶的是,讓一家沿海大型勞動力密集企業到內地怎么就這樣難?即使土地白送、稅收全免,這些企業還是寧愿窩在珠三角也不愿到內地發展。
對于深圳一年499家企業外遷,內地招商團們認為這太少了,499家企業當中有規模的企業不多,而且大部分在珠三角區域流轉,真正能夠走出珠三角、走出廣東到內地發展的企業少之又少。
“飛地”后的產業升級
在距珠三角腹地約250公里的陽西縣,臺商陳士傳的新廠房開始投入使用,與周邊數十家來自中山的企業一道,成為中山火炬產業園在陽西縣“飛地”的第一批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企業。
而過去,他們全部在中山市經營服裝、制鞋、玩具、電子等產品的出口加工業務。陳士傳的富利來公司一年服裝、服飾出口額超過1000萬美元;現在在陽西,他的生產能力是過去的3倍。
離開珠三角后,陳士傳最大的感受是,過去“招工難”和“用電難”等困擾,現在在新的地方都迎刃而解了,而且勞動力成本、水電成本都有較大幅度下降;而在中山市,則利用騰出來的廠房設備與一家日本企業合資,研發生產汽車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儀器,市場極為看好。
產業轉入地陽西縣縣委書記李孔流則說,按照現有規劃,與中山合作建設“飛地”占地1.1萬畝,按照雙方協議,中山方面負責園區建設投入與日常經營管理,陽西縣負責周邊配套設施的建設投入,產業園每年產生的工業產值和稅收,中山和陽西平分。
李孔流說,“飛地”模式對雙方的利益和訴求都有充分保障,這樣的合作對雙方來說是一件雙贏的大好事,中山獲得了工業發展所需的土地,還能收獲稅收和工業產值,陽西獲得了渴望已久的拳頭產業。他們預計該“飛地”8年內將為陽西帶來年工業產值300億,為當地提供直接就業崗位8萬個,陽西將一舉摘掉落后的帽子。
在“飛地”承接勞動力密集產業轉移的時候,有人也極力反思“珠三角模式”的得失,避免走珠三角曾經走過的彎路。
河源產業轉移園負責人賴澤華認為,以“飛地”的模式建設產業轉移園,本身就能促進進園企業走集約式發展模式,避免重復當年珠三角一些地區“家家點火、村村冒煙”的情形;而河源在承接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過程中對企業有明確取舍,目前他們從深圳和東莞等地引進了5家手機生產企業和6家手機零部件配套企業進入產業轉移園,并為此建設手機檢測中心等公共技術平臺。現在在河源山區,一個起點頗高的手機產業集群漸具雛形,到2010年,這里將實現年產值450億元、年稅收18億元,等于重新建了一個河源市。
對此,廣東省省長黃華華說,面對珠三角勞動密集型企業自發向外尋求發展空間的趨勢,廣東省出臺了《關于廣東省山區及東西兩翼與珠江三角洲聯手推進產業轉移的意見(試行)》,并在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建設18個省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園,總規劃面積15萬畝,年產值可達2600億元,年可實現利稅150億元。此外,各地市、縣(區)或鎮所建設的產業轉移園區上百個,他們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把民間自發的產業轉移,提升為由政府引導、適應市場規律的產業有序轉移。
更重要的是,這些政府主導的上百塊“飛地”,基本分布在距珠三角腹地100~300公里環形帶上,形成特征明顯的珠三角產業轉移帶,有意無意造就了珠三角第一層產業輻射波。
何時飛進泛珠三角?
今年6月,第四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在湖南長沙開幕,廣東經貿代表團因其帶來大批貨真價實的經貿合作項目受到各方矚目。其中,廣州市市長張廣寧在省會城市合作論壇上的發言擲地有聲。他說,在前三屆泛珠經貿洽談會上,廣州所簽訂的147項合作項目已全部履約,涉及基礎設施、產業與投資、服務貿易、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環保、勞務等領域,合作總金額達340.56億元;本次經貿洽談會又簽訂了150多億元的合作項目,也將一如既往。
但在會議間隙,有記者問張廣寧市長,泛珠三角其它省區都把眼睛盯在珠三角,盯在產業轉移上,幾乎每個省區都表示愿意當珠三角產業轉移承接地,為什么張市長對“產業轉移”一事只字未提?張廣寧笑著說,還沒到時間,還沒有這方面的機制,這需要九省區坐下來好好研究。
換句話來說,讓廣州市無償動員大批勞動力密集企業離開廣州,分赴泛珠三角各省區,廣州還未能接受。
毫無疑問,在近年珠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中,廣州是最成功的。短短數年時間,廣州從以輕工業為主的城市,實現了以汽車工業、裝備工業及臨港大工業為主骨架的發展升級,在工業化進程中實現了重化階段與信息化階段并舉,并成功地避免了“高科技”產業“勞動力密集型”化,切實為接下來的新一輪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儲備了人才,預留了空間。
但同時廣州也正為它的調整和轉型支付成本。正處在調整過程中的工業體系尚沒有完全發揮到最大值,而一些從前可以充“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勢頭不再,廣州的工業產值被深圳拉開距離,被蘇州趕超。在這樣的局面下,動員大批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離開廣州,就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總體上來說,中國式產業轉移依然需要政府推動,而政府推動的動力,則源自利益的平衡。
而如果泛珠三角九省區能夠面對現實,在制度上能夠切實創新,以“飛地”模式引導產業轉移,珠三角第二層產業輻射波將有可能提前覆蓋整個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屆時泛珠三角九省兩區將形成完整、開放且密不可分的區域經濟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