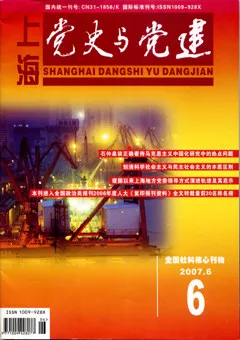是國家培養了我們,我們要好好報效國家
采訪:謝黎萍 黃 堅 杜 捷 張 勵
整理:黃 堅
時間:2006年9月7日
采訪前記
鄒世昌,材料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58年在前蘇聯莫斯科有色金屬學院獲副博士學位。時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所副研究員、輕合金室主任,第十研究室甲種分離膜研究室工藝組組長。
留學蘇聯,見到毛主席
我們所里的歸國留學人員中既有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也有從社會主義國家留學回來的。我是屬于由國家派出去,然后再回來的這一類歸國留學人員。1953年,國家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急需大批的各類建設人才,規定凡是四年制的大學生都要提前一年畢業,因此,我在念了3年大學后,就提前一年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了。畢業以后,我被分配到科學院工作。那時,全國各地分配到科學院的大學生都要參加集訓,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部長作報告,接受政治思想教育。集訓是在北京北海文津街院部進行的,集訓完了以后我就被分到上海冶金所工作,那時不叫上海冶金所,叫工學館(即中國科學院工學實驗館)。
1953年,所里派我出去參加留蘇考試。那時,國家為了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高級科學技術人才和教學人才,造就一支強大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隊伍,十分重視留學生工作。當時的留蘇考試是全國統考的,錄取后我就到北京念俄文去了。念俄文的留蘇預備生集中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上課,地址就在北京宣武門里面,我們那時其實是沒有什么宿舍的,住的地方原來都是教室,我們一間房間就住20多個人了,而且都是上下鋪,我那時是睡上鋪的。除了語法課是中國老師教的,教我們念俄文口語的都是蘇聯專家的夫人,她們都住在友誼賓館。北京的友誼賓館就是專門為蘇聯專家造的。每天早晨,大巴士把那些蘇聯專家夫人接過來,教我們俄文。所以,想想我們當時念俄文的條件還是很好的。
念了一年俄文以后,1954年,我就到蘇聯去了,在莫斯科有色金屬學院材料科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當時,國家為了培養一個留蘇學生,確實是花了很大的代價,大概相當于培養國內三十幾個大學生。像我們出去留學的時候,國家就專門為我們每人配備了兩個大皮箱,里面的衣服從襯褲到襪子、襯衫,夏天的西裝和冬天的西裝,還有外面的皮大衣和帽子,全部都配備齊了。像我們這些孩子,光靠家里面上大學都很困難,更甭提出去留學了。我的家境也不是很好的,中學以后都是靠助學金支持念上來的。所以,當時大家都覺得我們是國家和人民一手培養起來的,我們就是要報效國家。
對我們這批人,國家除了在生活上非常照顧以外,在政治上也不斷地教育我們。當時凡是有國內代表團來蘇聯,路過莫斯科的,都要給我們做政治報告。這些報告都是國家領導人作的,而且他們都脫了稿子講,一講就是3、4個小時。我舉一個例子,1957年那一次,毛主席率領一個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那次是陸定一同志給我們做報告,報告從早晨8點鐘開始,一直做到中午。在莫斯科大學聽報告的留蘇學生有近2000人,聽完報告以后,大家都遞條子,要求見毛主席。劉曉大使說,毛主席率代表團來莫斯科的消息傳開后,你們留學生就有好多人寫信給大使館,要求見毛主席。你們這種心情,我們完全理解。毛主席就住在克里姆林宮,因為昨天晚上開會開得很晚,現在還在睡覺。等毛主席起來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可能。現在,你們先去吃飯。于是,許多人就去吃飯了。我們一聽有希望見到毛主席了,也就不去吃飯了,紛紛涌到前面的座位去,我記得那個時候自己坐得挺前面的。下午2、3點鐘,我們就看到拍電視的設備都搬進來了,知道可以見到毛主席了。所以,毛主席接見留蘇學生時,我們當時就坐在下面。那天,代表團所有的成員都來了,劉曉大使激動得有點講不出話來了,是毛主席親自介紹了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這是宋慶齡、這是鄧小平、這是彭德懷……一個個介紹過來。毛主席在講話中說“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東風壓倒西風”,我們聽了以后,都覺得非常受鼓舞。國家把我們當成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就寄托在我們身上,那我們就得好好干,現在就得好好學習。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政黨在別的國家是不能活動的,但當時中蘇關系十分友好,中國共產黨可以在蘇聯開展活動,可以開會,可以過組織生活,可以發展黨員。我就是1956年那一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黨,我是留蘇學生中在莫斯科吸收的第一批黨員。另外,我們還可以參加蘇聯共產黨一些大的活動。譬如,當時學校黨組織播放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蘇共二十大內部報告錄音時,我們都去聽,也都聽懂了。斯大林那么一個偉大的人物,赫魯曉夫一下子把他講得一塌糊涂,這對我們的思想震動都很大。我所在的莫斯科有色金屬學院,是2個人1個房間,1個是中國學生,1個是蘇聯學生。蘇聯學生一般都是蘇共黨員,在政治上、思想上各方面都比較好的。校方作出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為了幫助我們學習俄文,因為你和蘇聯同學住在一起,他講俄文么,你就沒有時間講中文,你也就只好講俄文了。另一方面,他可以在各方面幫助你。我記得我宿舍的那個蘇聯同學聽了赫魯曉夫的報告后,至少一個月沒有一個晚上睡好覺。為什么?思想轉不過來么。所以,要說蘇聯共產黨為什么到后來出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那個時候就埋下根子了,它把蘇聯共產黨員多年來的一種堅定信仰毀掉了。當時,蘇聯發生的種種變化,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教育。
重返冶金所,加入輕合金研究行列
我在蘇聯莫斯科待了3年半,1958年初,拿了個副博士回國。回國以后,帶著組織關系,先到高教部報到,然后回到科學院。當科學院再分配的時候,確定我和另外1個同學2個人都到長沙去。我們2個原來都是冶金所出去的。后來因為老所長周仁發火了,他說我們這里送了幾個出去,你們1個都不送回來,以后我們不送了。科學院最后決定,2個人中送1個回去。姓周的同學學的是化學冶金,那個時候長沙礦冶研究所的重點是在化學冶金,所以,他就分到長沙去了。搞材料的重點那時還是在上海冶金所,所以,我回到了上海。
50年代初我剛到工學館的時候,工學館很小,只有幾十個人,很多都是解放前老的工作人員。那個時候,工學館還沒有研究室,只有3個組,一個是化學冶金組,一個是物理冶金組,一個是窯業組。化學冶金組就是從礦石里面把金屬提煉出來,物理冶金組就是做材料的,窯業組是做陶瓷的。3個組的領頭人是3個老院士:窯業組是嚴東生,現在是上海硅酸鹽所名譽所長;物理冶金組的領頭人是吳自良;化學冶金組的負責人是鄒元燨,現在他去世了。研究室是后來才成立的。1958年我回來后,那時研究所正好開辟一個新的方向,叫輕合金。就是搞鋁合金、鎂合金、鈦合金,因為在金屬里面,它們的份量都是屬于比較輕的。我回來后,職務是助理研究員,擔任輕合金研究室的副主任,后來任主任。我是所里留蘇回來的第一個人,到“文革”以前,所里從蘇聯留學回來的人員大概有二三十個人之多,我們都成為各個部門的骨干力量。
上海冶金所的歸國留學生中,從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老專家,在所里面大都是擔任室一級領導職務的,像鄒元燨是負責化學冶金部分,吳自良是管物理冶金的,嚴東生是管陶瓷的,陳炳兆是管精密合金的,許順生跟我在一起,他是室主任,我是副主任,是管輕合金的。石聲泰是腐蝕室的室主任,黃玉璞沒有當室主任,究竟在哪個室里,我記不清楚了。這些從歐美回來的專家是我們的前輩,年齡上也比我們大一點,在生活待遇各方面,他們基本上都是享受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譬如,他們的工資當時就都是二三百元了,是一般研究人員的二三倍。再譬如在住房方面,象吳自良原來就住在愚園路1055號一棟小洋房的上面,許順生當時就住在五原路,他們50年代居住的住房就相當于我們現在一套套的公寓房了,而當時上海一般居民的住房,人均才幾個平方米。我們從蘇聯留學回來的人是國家培養的,在生活福利方面的待遇和國內培養的科研人員是一樣的,回國后,我們還是繼續住宿舍。
接受新任務,參與研制甲種分離膜
1960年夏天,我在長春出差時,一份電報催我馬上到北京。我到北京后,所黨委書記萬鈞已經在北京了。有天晚上,科學院用車把我們接到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的辦公室。錢三強說:蘇聯專家撤退了,不能幫助我們造原子彈了。原子彈的一個關鍵就是鈾同位素的分離。因為天然鈾中238的含量是99.3%,235只有0.7%,現在要把0.7%的235濃縮到90%以上才能做原子彈。濃縮鈾的關鍵設備就是分離膜的元件。蘇聯專家說:分離膜的元件現在世界上只有美國和蘇聯會造,它是社會主義陣營安全的心臟,是絕對不會泄露出來的。你們中國弄不到分離膜元件,你們的設備就是一堆廢銅爛鐵,你們就造不出原子彈來。錢三強講,黨和國家決定把研制分離膜的任務交給你們去完成。聽了這些話,大家深感責任重大。
當時錢三強在落實這個任務的時候,除了我們上海冶金所這1家外,還有沈陽金屬所、復旦大學、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全國共有4家單位在做。4家單位大概做了1年,進展不快。1961年,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出差,黨委書記萬鈞說你開完會不要回上海,還有一個會你要去參加。中國科學院裴麗生副院長要召開會議,可能是討論甲種分離膜如何進一步集中力量,加快進度的事。會議開始后,4家單位各講各的優勢,我就專門講上海綜合性的工業基礎比較強的優勢。會后,二機部和科學院又組織人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因為搞分離膜這個事情,涉及的工業行當很多,包括化工行業、紡織工業以及裝備工業,實驗室研制完了以后,還要大批量生產。所以,從技術條件來說,上海相對比別的地方來說,要好一點。加上那時候,上海市委表態說,研制甲種分離膜如果放在上海做,上海就把它作為第一號任務來做。冶金所黨委也表態說,如果把它放在冶金所做,所里人員隨便挑選。1961年10月,二機部、公安部,還有國防科工委等在上海開會,決定將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沈陽金屬研究所、復旦大學的有關科研人員集中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組成專門研究室,進行“甲種分離膜制造技術”的協同攻關。為此,上海冶金所專門成立了1個研究室,按照當時的編號是第10研究室。
為了加強對研制甲種分離膜的領導,上海市成立了1個領導小組,派華東科委的副主任許言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專門負責這件事,領導小組成員還包括冶金所的黨委書記萬鈞、冶金局的一個局長,好像紡織局也有1個領導參加進去。在領導小組下面還成立1個辦公室,主任姓蔣,是從二機部調來,專門負責管理和協調工作。冶金所還為第10研究室專門配備了1正1副2個支部書記,加強10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實際上他們也參加10室的業務協調工作。
大概用了1個月的時間,全國有關人員全部集中到上海。當時,所里派出已經是副所長的吳自良擔任10室主任。金大康、李郁芬(復旦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和我,我們3個人擔任組長,分管3個組。我分管的這個組的任務是要把粉末做成分離元件。
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大家同心合力,不計任何報酬,白天做,晚上繼續做。包括吳自良,當時他領了3個組一起做。我們每3個月向二機部上報1次書面匯報材料,匯報整個進度情況。錢三強3個月1次,要聽匯報的。同時,他們也經常下來檢查情況。我記得1963年的春節,周恩來總理到上海來,要聽這方面的工作匯報,后來是冶金所的萬鈞書記去匯報的。就周恩來親自來聽取匯報工作這件事,我想當時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做事情能夠做到這樣的程度,真是不簡單啊!
1964年,我們研制出甲種分離膜,1965年做鑒定。其實在做鑒定時,我們實際上已經開始生產了。因為,當我們實驗室研制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時候,后面生產廠的人已經來我們這里參加工作了,上海冶金局也已在選址建生產廠了,廠里的設備和工藝完全是按照我們實驗室的設備和工藝參數做的,我們這里多少溫度,他那里就是多少溫度。等我們這里實驗室的工作做完后,生產廠就把工作接過去,我們實驗室的人員也跟過去,廠里的生產操作規程都是我們寫的。生產廠批量生產出分離元件以后,立刻就用于生產濃縮鈾了。原子彈的原料問題解決后,中國的原子彈很快也就爆炸了。甲種分離膜的成功研制,確實為我們國家的原子彈爆炸做了很重要的貢獻。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1983年,那時我已經擔任上海冶金所所長了。有一次在北京開會,見到錢三強,他跟我們講:你們的分離元件做得很好。現在我們國家的濃縮鈾生產就是靠它。它的壽命比原來蘇聯人說的還長,你們應該申報國家獎項。聽錢三強這么一講,我們才開了竅。從北京回來后,我們就整理材料,申報獎項。后來,甲種分離膜制造技術榮獲1984年國家發明一等獎,這也算是對我們工作的一種肯定吧。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王關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