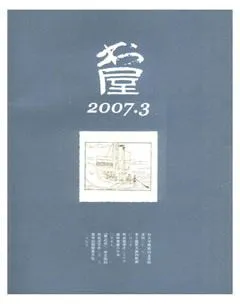治“大學”若烹小鮮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是說治理國家應(yīng)該像煎小魚那樣,不要翻來覆去地瞎折騰,而應(yīng)該小心翼翼地倍加呵護。這種“呵護”是守望和等待的姿態(tài),而絕非務(wù)激昂、喜更張,更非刻意地炒作。它所提倡的顯然是所謂的無為而治。治理一所大學固然不能同治理國家相比,但俗話說得好,“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它們的道理卻是相通的。因此,我們也可以套用老子的這句話說“治大學若烹小鮮”。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爭創(chuàng)一流大學”口號的呼聲中,我國大學興起的“圈地”運動、“合校”浪潮、“擴招”比拼,把大批高校帶入了一個集體“造勢”的漩渦之中。人們熱衷于盲目地制造規(guī)模,不切實際地追求外延擴張,其結(jié)果倒是形成了不少世界一流的大學建筑、大學校園(甚至包括大學校門)和在校人數(shù)的“巨無霸”,但卻唯獨距一流大學的目標依然遙遠。除了能夠靠這種虛假繁榮暫時滿足在各類排行榜上露臉的虛榮心之外,似乎不大有多少真實的價值,相反卻埋下了種種令人擔憂的隱患。錢穆先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美國訪學,給他的最直觀印象是美國大學的規(guī)模和設(shè)施之龐大。“某一人驟然走進大學,其首先注意者,厥為此大學之建筑。其次所看到者,乃其里面之設(shè)備。如擁有規(guī)模宏大之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實驗室、體育館等,凡此種種,皆極像樣”。如果一所大學的硬件設(shè)施是有人文內(nèi)涵的,有著與其悠久的歷史相稱的底蘊,而非徒具形式、虛張聲勢的軀殼,那倒也無可厚非。然而反觀今日我們大學的這一切,卻難以令人恭維。黑格爾曾經(jīng)說過:“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一所大學倘若缺乏文化內(nèi)涵,喪失了內(nèi)在精神,即使它擁有一流的硬件設(shè)施,不同樣是俗不可耐嗎?
大學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應(yīng)該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即使一所大學在物質(zhì)層面上差一些,只要它擁有自己的精神魅力,就不會妨礙它的尊嚴。那些新興的大學建筑盡管充滿霸氣,但絲毫不能讓人心生敬畏,因為它們?nèi)鄙偕铄涞膬?nèi)涵。只有軀殼而無靈魂,那絕不是真正的生命。清華老校長梅貽琦有一句幾乎被人們引用濫了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今天重溫這句名言或許會有別樣的體會。眼下辦大學,硬件設(shè)施不可謂不重要,但“大樓”與“大師”兩相比較,自然是后者更具有決定性和優(yōu)先性。現(xiàn)在不是“大師”過剩而“大樓”匱乏的問題,恰恰相反,是“大樓”林立、“大師”缺席的問題。“大師”不是刻意培養(yǎng)出來的,“大樓”卻是可以人為地建構(gòu)起來的。在一定意義上,大師乃是大學文化和大學精神的人格化。一所大學培養(yǎng)自己的學生,主要不在于教給他多少知識,而在于養(yǎng)成他的人格和能力。知識可以通過讀書獲得,它甚至不需要到大學來就可以達到。但大學的精神氛圍,以及它對人的熏陶、潛移默化的影響,則是沒有別的辦法代替的,非到大學親身感受、體味、領(lǐng)會不可。一踏進校園,應(yīng)該讓人能夠頓感一股書卷氣撲面而來,心生一種超凡脫俗的沖動,心地一片清涼。這才是大學的不可替代之處。大學精神氣象的形成也非一蹴而就的,不能操之過急,所謂“欲速則不達”,它有一個自然而然的生長過程。我們應(yīng)該學會“養(yǎng)成”,學會等待。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為大學文化和大學精神的養(yǎng)成提供條件,而不是直接地模仿或人為地移植。因為這樣得來的靠不住,也不會持久。文化是“泡”出來的,而不是“學”出來的。刻意的模仿總不免拙劣。草坪可以移植,樹木可以購買,大樓也可以拿金錢建造,但唯獨大學的文化和精神沒有辦法用移植和購買的方法來建設(shè)。
回顧一下當年西南聯(lián)大的情形,可以印證梅貽琦所言不虛。按照汪曾祺的描述:“有一座校門,極簡陋,兩扇大門是用木板釘成的,不施油漆,露著白茬。門楣橫書大字:‘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依今日眼光視之,不僅簡陋,簡直寒磣無比。學生宿舍又怎樣呢?“路以西,是學生宿舍。土墼墻,草頂。兩頭各有門。窗戶是在墻上留出方洞,直插著幾根帶皮的樹棍。”“桌椅是沒有的。很多人去買了一些肥皂箱……下面兩層放書,放衣物,這就書櫥、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來學士在這樣的肥皂箱桌面上寫出了洋洋灑灑的論文。”教室同樣簡陋得可以。“大圖書館的東面,是教室。土墻,鐵皮頂。鐵皮上涂了一層綠漆。有時下大雨,雨點敲得鐵皮丁丁當當?shù)仨憽!彪m然條件極差,但大學卻絲毫不因此失其尊嚴和高貴,因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何陋之有?更具挑戰(zhàn)性的是,那個時候的大學師生幾乎天天躲日本飛機警報,隨時有被炸死的危險,遑論找工作?大學教授和同學一樣,不僅衣食住行缺乏基本保障,就連自己的生命也隨時面臨意外。生存環(huán)境和條件之惡劣,由此可見一斑。據(jù)馮友蘭回憶,“在昆明受到的戰(zhàn)爭直接威脅是空襲”。“有座土山中間有道峽谷,我們稱之為‘一線天’,都認為那里是一個很安全是地方。空襲時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顆炸彈落在‘一線天’門口,掀起的土把華羅庚埋起來了,幸虧很快就解除警報了,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來。又有一次,一顆炸彈正落在西倉坡清華辦事處院子里,有一位工友不幸遇難”。金岳霖的幾十萬字的《知識論》書稿,就是在躲飛機警報中不慎丟失的。他后來又以頑強的毅力重新寫了出來。但是這些惡劣的生存條件似乎沒有妨礙這一代學人的學術(shù)理想。這不能不令今天的我輩肅然起敬。當年的學生畢業(yè)論文,論其水準足以令我輩無地自容。有人說,眼下博士論文不如以前的碩士論文,碩士論文不如以前的學士論文。這種說法也許有些言過其實,但論文的總體質(zhì)量下滑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究竟是為什么?這里并沒有“憶苦思甜”的意思。從內(nèi)在的方面去反省和檢討,也許具有更積極的意義。它將有助于增進我們的免疫力,使我們在種種誘惑面前保持足夠的抵御能力。顯然,這一切不是取決于“大樓”,而是取決于“大師”。
當年的西南聯(lián)大可謂大師云集,不乏文化昆侖式的人物。他們大都學貫中西、道接古今。這樣的師資群體,不免使后來的人們汗顏。令我們尷尬的是,大學教育在學術(shù)層面上出現(xiàn)了嚴重的青黃不接的局面。在相關(guān)領(lǐng)域或?qū)W科,昔日的輝煌恐怕早已是漸行漸遠,成為久違了的回響。學術(shù)命脈恢復(fù)起來,就不是一代人、兩代人的努力所能夠奏效的了。今天的人們必須追問,我們的優(yōu)秀學術(shù)傳統(tǒng)究竟是如何中斷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美學等甚至被宣布為資產(chǎn)階級偽學術(shù),以致在大學課堂和學術(shù)論壇上遭到封殺。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顧道:“實際上自解放以來,我的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問題是這種“否定”和“批判”并不是學術(shù)的而是政治的,因此它所帶來的不是學術(shù)上的創(chuàng)造和自我超越,而是極左路線的束縛、限制和干預(yù)。它不僅極大地妨礙了學術(shù)的原創(chuàng)力和應(yīng)有進展,更為嚴重的是阻礙了中華民族的思維能力的健全和成熟,甚至造成了一個新的文化斷層。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又面臨著全然不同的歷史情境和問題。現(xiàn)代化的取向作為我們這個民族世紀性的歷史選擇,才真正有機會被提上日程。與此相適應(yīng),大學治理也無可逃避地被納入現(xiàn)代性的軌道。但毋庸諱言,大學學術(shù)的人為干預(yù)不僅沒有終結(jié),而且在現(xiàn)代性的制度安排之下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就像人有人性,狗有狗性,現(xiàn)代化也有現(xiàn)代性。所謂現(xiàn)代性,籠統(tǒng)地說也就是使現(xiàn)代化成其為現(xiàn)代化的那個內(nèi)在的理由。它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被規(guī)定,但人為性無疑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現(xiàn)代社會就像一個被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千姿百態(tài)、光怪陸離的現(xiàn)象使人們喪失對其概括的能力。但若仔細考量,還是可以有所把捉,關(guān)鍵是要找準其中的紋路。作為啟蒙的歷史—文化后果,現(xiàn)代性的合法性內(nèi)在地蘊涵于啟蒙精神之中。按照康德的說法,所謂啟蒙就是人有勇氣來運用自己的理性。當理性被人們用來審判一切的時候,它自身卻逃避了一切可能的判決。康德雖然致力于揭示理性的局限性,但理性本身固有的缺陷未曾被他真正揭示出來。因為康德只是揭示理性的外部不足,而非發(fā)現(xiàn)理性本身固有的致命缺陷。“上帝”被理性之“劍”殺死之后,作為主體的理性自我——人有一種取而代之的沖動。它帶來的后果是僭越,即占據(jù)上帝的位置而為所欲為。這是為啟蒙思想家們所始料未及的。啟蒙時代的人們急于“建功立業(yè)”,有著強烈的成就欲和事業(yè)心,這也不能說是壞事,但其中所蘊藏的功利取向和對效率的無止境的追求,這一切過度的急于有所作為的姿態(tài),卻破壞了自然而然的境界和那種回到事物本身的質(zhì)樸。
昆德拉在小說中質(zhì)詢道:“慢的樂趣怎么失傳了呢?啊,古時候閑蕩的人到哪里去啦?……他們隨著鄉(xiāng)間小道、草原、林間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嗎?”在現(xiàn)代社會,“速度是出神的形式,這是技術(shù)革命送給人的禮物”。而在作者看來,所謂“出神”,就是自我的喪失狀態(tài)。他繼續(xù)寫道:“跑步的人跟摩托車手相反,身上總有自己存在,總是不得不想到腳上水泡和喘氣……當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給一臺機器時,一切都變了:從這時候起,身體已置之度外,交給了一種無形的、非物質(zhì)化的速度,純粹的速度,實實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更深度的危機在于,這種追求速度的沖動一旦變成制度安排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就勢必改變?nèi)藗冊械目创澜绲姆绞剑恢脫Q成一種游離事物本身的善于算計的功利態(tài)度。一位中國的長者曾經(jīng)對《東方哲學的故事》一書的作者貝克說:“在你們西方人眼中,用一小時而不是三天時間到達某個地方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我們東方人所關(guān)心的是你到那兒要干什么。”其實,這不僅是東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差別,隨著現(xiàn)代性的降臨,也成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鴻溝。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現(xiàn)代性也可以說就是人為性。回頭想想,在現(xiàn)代社會還有什么是不能夠“人造”的?在今天,“克隆”已不再僅僅是一項生物技術(shù),而是變成了廣義的文化性格。現(xiàn)代人從“生”到“死”,都難以擺脫人為的干擾。從剖腹產(chǎn)到安樂死無一不是非自然的狀態(tài)。所謂“搞笑”、“做愛”、“造勢”之類,都是為現(xiàn)代社會所偏好并鼓勵的樣態(tài)。“搞”、“做”、“造”皆為人們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而人為即是“偽”,它遠離了“誠”。所謂誠,即本真地生成。所以《中庸》說“不誠無物”。這不是說離開了“誠”,便什么都不復(fù)存在,而只是說離開了它,一切都將不能本然地呈現(xiàn)出來、成就起來。本真地生成亦即“無為而成”,所以“誠者,自成也”。“至誠無息”,誠使事物永無止息地存在,也可理解為沒有消息,“天何言哉”?上蒼不偏不倚,最為無私,所以是至誠,它還需要什么自我表白嗎?所以說“誠者,天之道”。在這里,我們又一次體認到了儒家智慧同老子智慧的相通之處。現(xiàn)代社會的人為性,其代價是把事物的本真性遮蔽起來了,人們由此陷入了一個虛假的世界之中。現(xiàn)代文化令人作嘔的矯揉造作和虛情假意,使我們難以回到事情本身。
關(guān)于大學的使命,當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曾多有論述,他說:“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guān),不可視為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顯然,蔡先生為民族的命運和未來計,強調(diào)的是大學的文化擔當和人格成就之使命。“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此一性質(zhì)不應(yīng)因為世俗化和市場化而被否定和拒絕。筆者在一篇小文中曾提出:“大學之為大學,其根本在于它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高度和厚度。”就像一個人一樣,一所大學也必須有自己的氣象和風骨。在種種擋不住的世俗誘惑面前,大學應(yīng)該有足夠的免疫力,保持自己的氣節(jié)和操守,保持自己的精神上的高貴,而不能隨波逐流,甚至媚俗或同流合污,哪怕是高雅的媚俗。然而,今天的大學恰恰是在迎合各式各樣的外在尺度中遺失了自己的自主性。可悲之處在于這種迎合是在主動的姿態(tài)中實現(xiàn)的。在蔡先生看來,大學的天職應(yīng)該是學術(shù)的成就和延續(xù),大學應(yīng)致力于養(yǎng)成思想之興趣和習慣,而非進行作為謀生手段的知識訓練。然而,大學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建制,又總是本然地與大學所追求的目標若即若離,有時甚至不免相互牴牾。這不能不說是學術(shù)和思想在大學制度內(nèi)所遭遇的悲劇性的命運。在大學內(nèi)部,我們甚至難以找到或發(fā)現(xiàn)可資借鑒的參照系,這除了因為大學治理被現(xiàn)代體制的法眼盡收眼底之外,還由于大學在其本性上面臨著一個悖結(jié),即學術(shù)和思想的自由在大學作為社會建制難以保持自治的條件下有走向異化的危險。
盡管羅素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未必都令人信服,但他的這一觀點卻是有意思的,他說:“事實上,受教育最多的人,他們的思想和精神生活變?yōu)槲s是極常見的事情,他們?nèi)狈_動,只擁有一定量的機械式的才能來代替生動的思想。”知識以及為此而設(shè)置的專門機構(gòu)——大學,在本性上就有一種偏離自然的傾向和性格。這是文明的吊詭,文化和文明的異化。文化或文明原本是人的自我肯定,但當它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面臨著淪為一種否定力量的危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文化乃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文化的發(fā)達程度取決于人對自然的疏離程度。從一定角度說,雙重意義上的自然(包括大自然和自然而然)乃是知識的解毒劑,也是現(xiàn)代性及其人為性的解毒劑。
民間思想的最大優(yōu)勢或唯一優(yōu)勢就在于它的真誠、率真,它的回到學術(shù)本身。它對于大學的啟示意義在于“無為而治”。一所大學,就好似一只準備做繭的蠶,讓它在那里靜靜地吐絲、默默地做繭好了。在民間,在社會的最底層,總是有那么一些對學問和思想有著特殊偏好和執(zhí)著追求的人,即使在今天這樣一個紅塵滾滾的時代,他們依然無怨無悔、孜孜以求。這些民間學者和民間思想家身上所透射出來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無疑給當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畫卷抹上了凝重的一筆。因為正是這種精神的存在,才真正凸顯出思想的尊嚴和崇高。帕斯卡爾意義上的那棵“蘆葦”,雖然孱弱,卻象征地表達了思想植根于大地的那種“草根性”。民間思想家恰恰就是那條聯(lián)結(jié)思想蒼穹與廣袤大地的堅韌紐帶。
民間思想家們往往沒有學歷,沒有學位,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以至不是學士,因此也就難以獲得優(yōu)裕的治學和思考的環(huán)境,缺乏可以分享的學術(shù)資源,甚至找不到“知音”交流,不得不忍受心靈孤旅。由于沒有合法的“名分”,他們被拒之于學術(shù)界的大門之外。這就是民間思想家必須面對的命運。民間思想家因為自己的獨特經(jīng)歷,總是難以得到現(xiàn)有學術(shù)體制的“準入”,從而被視為“另類”,既難以得到常人的理解,也難以得到學術(shù)界的承認和公正評價。這種情形在制度化無孔不入的今天尤其嚴重。民間思想家的“出身成分”就像永遠抹不掉的“原罪”一樣,成為縈繞他們心頭的“夢魘”。無論他們在學術(shù)上做出了怎樣的貢獻,都有一道難以跨越的“卡夫丁峽谷”橫在他們的面前。
民間思想家們雖然無“資格”進入主流學術(shù)語境,缺乏“發(fā)言”的機會,但從本質(zhì)上說,只有他們才真正有資格進行靈魂的叩問,因為他們擁有的是真誠,是對功利的超然態(tài)度。對于學術(shù)來說,這種純粹性是彌足珍貴的。同體制內(nèi)學者相比,民間思想家顯然處于極端的劣勢地位和邊緣化狀態(tài)。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苦難和困厄才能孕育并成就真正的智慧和思想。反觀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不乏其例。當年的馬克思身處社會的邊緣,遭遇種種排斥和迫害,貧病交加。他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自我解嘲道:“未必有人會在這樣缺貨幣的情況下來寫關(guān)于‘貨幣’的文章!”以致窘迫到連郵寄研究“貨幣”的手稿(即《資本論》)的郵費都沒有。馬克思的夫人燕妮·馬克思在一封信中寫道:“同這種擁有金錢和種種斗爭手段的官方勢力作斗爭,當然是極其有趣的;如果斗爭的結(jié)果是我們勝利了,那就更加光榮,因為斗爭的另一方擁有金錢、權(quán)力和一切,而我們卻常常不知道從哪里能弄到寫信的紙,如此等等。”黑格爾曾對歌德說過:辯證法“只不過是經(jīng)過整理和方法地訓練了的反抗精神罷了。”這也正是馬克思之所以選擇辯證法的根本原因所在。黑格爾由于成了普魯士王國的官方哲學家,即使擁有辯證法,也難以將其引入實踐。這一點只有在邊緣化的馬克思那里才成為可能,其中緣由耐人尋味。
當一個人處于業(yè)余狀態(tài)的時候,他的所思所想絕沒有學術(shù)之外的企圖。一旦進入“學術(shù)共同體”,成了所謂“圈子里的”人,做起學問來倒是考慮得很多,有這樣那樣的顧忌,有這樣那樣的權(quán)衡,也有這樣那樣的算計。這些東西說到底不僅與真正的學問或思想無關(guān),反而阻礙了學問或思想的造就。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他必須不停地“碼字”“作文”,以免被別人遺忘,以便出色地“完成”體制賦予自己的職責,從而滿足自己日益強烈的虛榮心。如此一來,就難免沉湎于學術(shù)之外的考量。一旦成了體制的俘獲物,人們就不可避免地淪為既得利益者。它銷蝕著人們對學問和思想的目的性追求。學術(shù)的體制化一方面使思想變成了“職業(yè)”,另一方面使學問變成了“制造”。“匠氣”、“機心”也就在所難免了。“職業(yè)”同“志業(yè)”之間的天壤之別,就在于前者因作為謀生手段而淪為工具性的規(guī)定,后者則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方式。這里的體用之別,判然可鑒。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民間思想家的民間性,使得他們保有了人文關(guān)懷和價值擔當?shù)募冋浴?br/>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民間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發(fā)現(xiàn)”。其實,說“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隱含著主流學術(shù)話語的偏見了。因為既然是“發(fā)現(xiàn)”,就必有發(fā)現(xiàn)者和被發(fā)現(xiàn)者,而民間思想家只能處于“被發(fā)現(xiàn)”的受動的客體地位。他們只能等待著發(fā)現(xiàn)者的拯救。這實際上暴露了現(xiàn)行學術(shù)體制的致命缺陷。重要的不是民間思想家有沒有碩士、博士頭銜,有沒有名分上的資格,而是他們是否做得像碩士和博士一樣出色。
沖破學術(shù)體制繁文縟節(jié)的層層束縛,最大限度地釋放來自民間的思想,這理當成為一個健全而成熟的社會的應(yīng)有作為。在一個日益“科層化”的現(xiàn)代性體制之下,如何捍衛(wèi)民間思想家的思考權(quán)和發(fā)言權(quán),更是值得格外關(guān)注的事情。他們所需要的不是恩賜和同情,而僅僅是尊重。民間思想家的存在,其更深刻的意義也許并不在于他們具體“說”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們的存在本身。正是由于他們的存在,包括大學在內(nèi)的整個學術(shù)界才擁有了一種判準、一把尺度,從而才有了自我反省的可能。這不僅是民間思想家的魅力,更是民間思想本身的力量。努力維系學術(shù)體制內(nèi)外力量之間的建設(shè)性的互動,乃是一個民族在思想上永葆生機和活力的絕對前提。關(guān)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盡快找到這樣一種互動的恰當機制。這已經(jīng)成為擺在今天的人們面前的一個難以回避的課題。
羅素說:“一個教師應(yīng)該在大多數(shù)的日子里,能教多少就教多少,真能在工作中得到愉快。”這種說法,今天聽來真是恍如隔世。他認為:“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用更多的錢,使教師能有更多的空閑,而且有一種自然的對于教學工作的愛好。”這里最吃緊的是“自然的……愛好”。陶潛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悠然”乃不期然而至,它是不經(jīng)意間的來臨。在人為性的體制下,“悠然”早已成為遙遠的絕響和現(xiàn)代人的奢侈。久違了的從容心態(tài),應(yīng)當是做學術(shù)并把學術(shù)做得中規(guī)中矩的絕對必要的主觀條件。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學須靜也”,“靜以修身”,因為“非寧靜無以致遠”。涵養(yǎng)的工夫就需要這種靜的氛圍和境界。然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真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倘若整天被搞得心旌搖蕩,惶惶不可終日,大概也做不出什么一流的學問。學術(shù)不端現(xiàn)象的泛濫就是一個明顯的癥候,它印證著學術(shù)的浮躁。清季章學誠在家書中曾說:“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逼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為,往往不如初志。”古希臘也有“閑暇出智慧”的說法。今日學術(shù)的浮躁透射出來的實際上是學者心態(tài)的浮躁。這里不能不提及制度安排的因素。制度決定論者喜歡把制度視做萬能之物加以推崇和膜拜。其實,當制度安排游離了事物本真性的時候,其消極作用也會被制度放大到無以復(fù)加的地步。真正重要的不是制度的有無,而是制度的優(yōu)劣。制度的設(shè)計歸根到底不可能離開心態(tài)這一變量的干擾。心態(tài)往往是以集體的偏好和無意識狀態(tài)約束著制度的形成。我們今天的心態(tài)是被現(xiàn)代修飾過了的心態(tài)。與羅素所說的相反,現(xiàn)在我們是“用更多的錢”來吊教師的胃口,喚起功利之心,為了完成更多的課時量而奔波,為了超額完成各式各樣苛刻的指標而“制造”知識和學術(shù),而非“用更多的錢”來保障他們的閑暇,培養(yǎng)思考的興趣和教學的興趣。馬克思所說的作為謀生手段的勞動只能成為一種奴役,而不可能使人們從中感到愉悅和享受。他把這種性質(zhì)的勞動叫做異化勞動。它只能是人們生活的不堪忍受的重負,而絕不能夠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這樣的勞動又何以能夠期望它使人獲得創(chuàng)造的樂趣呢?
我們的運動員之所以在很多時候出不了一流成績,恐怕與體育比賽被賦予了太多的外在含義所致。體育本來是游戲而已,游戲的最大特點乃是無功利性。倘若被附加上許多原本不該屬于它的規(guī)定,那么它也就不可避免地異己化了。一個運動員在比賽時如果身后有十三億雙眼睛盯著他,成敗在此一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他能不高度緊張嗎?這樣的狀態(tài)又怎么能夠不妨礙他的成績呢?如果獲勝我們就興高采烈,以至于喜極而泣,甚至大有揚眉吐氣之感,好像體育成績能夠一掃晚清以來積淀下來的民族屈辱;如果失敗,則沮喪不已、痛苦欲絕,甚至摔暖瓶、扔鞋子。諸如此類,說到底不過是弱國心態(tài)和民族自卑的表現(xiàn)。把體育同愛國直接掛鉤,反而遮蔽了體育的本真意涵。大學的治理也是一樣。今日大學受到的牽制過多,許多事情乃是身不由己。自由的代價就是“無用”。然而啟蒙精神的實質(zhì)就是追求有用性。有用性使我們離開了事情的本然狀態(tài),而陷入一種以占有為取向的對象性關(guān)系的鉗制之中而難以自拔。這種有為的姿態(tài)恰恰妨礙了大學的自律,與大學的使命背道而馳。
公允地說,人為性并不單純是由于現(xiàn)代性作祟而出現(xiàn)的,它實際上是多種因素在一個極特殊的歷史境遇中湊合在一起共同導(dǎo)致的后果。因此,這種人為性還帶有中國的特色,例如傳統(tǒng)社會的官本位所表現(xiàn)出來的政治全能主義,鼓勵了人們的唯意志論偏執(zhí)。似乎擁有權(quán)力,就可以無所不能、無所不通,官員教授、官員博導(dǎo)、官員出書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大景觀,看上去他們似乎是最早一批實現(xiàn)了馬克思所孜孜以求的目標即所謂“全面發(fā)展的人”。社會角色的紊亂,意味著缺乏對人的自我局限性的清醒認知。這不啻是另一版本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再者就是傳統(tǒng)的計劃經(jīng)濟的管理模式所具有的慣性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續(xù)了人為性。由于制度安排中的路徑依賴,傳統(tǒng)體制的弊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某種復(fù)制,盡管已不再是原生態(tài)意義上的表達。然而,無論原因是什么,最大限度地克服大學治理方面的人為性,無疑是中國大學未來的真正希望和出路所在。在這方面,我們還是應(yīng)該學學古人的智慧:“治大學若烹小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