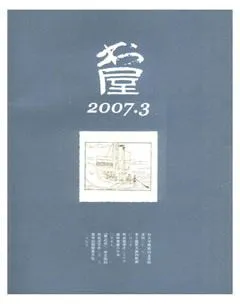也談稅收
李煒光教授的《寫給中國的納稅人》一文誠如《書屋》的編輯絮語所言,系發憤之所為作,情緒激昂,見解獨到。筆者淺陋,有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稅收的“三性”
讀了李瑋光教授的文章后,筆者翻了翻書,查著幾條外國對稅收的定義,不嫌繁瑣,羅列如下:
1. 英國《新大英百科全書》定義:“在現代經濟中,稅收是國家公共收入最重要的來源。稅收是強制的和固定的征收;它通常被認為是政府公共收入的捐獻,用以滿足政府開支的需要,而并不表明是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稅收是無償的,它不是通過交換來取得。這一點與政府的其他收入大不相同,如出售公共財產或發行公債等等。稅收總是為了全體納稅人的福利而征收,每一納稅人在不受任何利益支配的情況下承擔了納稅義務。”
2. 美國的《現代經濟學詞典》定義:“稅收的作用在于為了應付政府開支的需要而籌集穩定的財政資金。稅收具有強制性,它可以直接向居民或公司征收。”《美國經濟學詞典》則認為,“稅收是居民個人、公共機構和團體向政府強制轉讓的貨幣(偶爾也采取實物或勞務的形式)。它的征收對象是財產、收入或資本收益,也可以來自附加價格或大宗的暢銷貨”。
3. 日本的《現代經濟學辭典》定義:“稅收是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為籌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資金,而按照法律的規定,以貨幣的形式對私人的一種強制性課征。因此,稅收與其他公共收入形式相比,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稅收是依據課稅權進行的,它具有強制的、權力課征的性質;(2)稅收是一種不存在直接返還性的特殊課征;(3)稅收以取得公共收入為主要目的,調節經濟為次要目的;(4)稅收的負擔應與國民的承受能力相適應;(5)稅收一般以貨幣形式課征。”
這些定義與李教授所言的我國教科書上對稅收的定義基本相同。定義里也清楚地認定了稅收的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且這些國家應該都是市場經濟國家。所以認為“稅收三性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那時候的體制,是大政府,小社會……三性的提出,符合當時的制度需要和要求,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這個說法恐難以站住腳。
另一方面,李文對“三性”的論述也有偏頗之處,如認為強制性是任何法律共有的因素,不只稅法有強制性,其他法律也有。我們講法的特征是強制性,是從法理上講的,并不意味著各門法的特征都是強制性,像民法的特征,我就沒見過哪個教材上講它的特征是強制性。關于無償性,李文講到“不給納稅人以應得的報償,那你征稅干什么?”《大日本百科事典》中對這一問題是這樣解釋的:“盡管稅收是公共收入的一種形式,但它并不像手續費那樣具有直接的交換關系,它是無償的。盡管當稅收收入為公共支出以后又返還給國民,但是每一個納稅人受益的大小與其納稅額并不成比例。”最后,李文講固定性,是用法律與政策相比,具有固定性。而稅法的固定性是指課稅對象、課稅額度和課額方法的固定性。而現實生活中存在亂收費、亂罰款及亂攤派并不能說稅法的特征不是固定性,而恰恰是違反了稅法的固定性這一特征。所以固定性不僅是稅法的一個特征,而且是當前更應該著力解決的問題。李教授講的服務性,確實很有道理,它與稅收宣傳中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相契的。
而且,即便是引入“債務關系說”,納稅人與國家的關系仍然不同于民法的合同關系,如納稅人不納稅,國家仍然是以強制力征收,對納稅數額有異議,仍然要通過稅務復議等形式來解決等等。
法律與權利意識,沉重的話題
如李教授所言,我國現行稅制中有二十四個稅種,確實只有《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稅收征收管理法》是稅收法律,其余的都是依照授權立法進行的。1984年9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和發布有關稅收條例。1985年,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根據兩次的授權立法,國務院從1994年1月1日起實施工商稅制改革,制定實施了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六個暫行條例。授權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工作亟須法律保障的當務之急。但也應該看到,從1994年的工商稅制改革到現在,已有十二年的歷程,《立法法》的施行也有六年半了。這些稅收暫行條例還沒有按照《立法法》的要求,盡快制定成法律加以固定,而且立法的呼聲也不高,確實說明了立法者與納稅人對這一問題的漠視,我想這也是李教授寫這篇文章的良苦用心。
我十分贊同李教授的觀念,針對目前存在的諸多稅收方面的問題,如果不在提高公民權利上下功夫,不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即便是立法完善、制度落實,在稅收方面仍然會存在很大的問題。其實不光是在稅收方面,我們的憲政理念和觀念存在太多的問題,現在大家的關注點大多在刑事法律方面,而在行政法律方面,可能比起刑事法律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德國法學家耶林寫過一本名著,名字叫《為權利而斗爭》。這是一個公民對法治世界的呼喚,而中國的廣大納稅人,我想他們更關心的是稅負的高低,而不是稅收的公平;他們更津津樂道于自己的依法納稅,而很少考慮政府是怎樣使用稅款的,有沒有揮霍浪費;他們即使對稅收有這種那樣的想法,也很少表達,因為在一個傳統上國家大于個人的社會,對自己所交稅款說三道四是不明智的。
所以,在當下,更好地解決稅收問題的責任仍然在政府,李教授的文章與其說是寫給納稅人的,不如說是寫給政府的。公民(納稅人)要通過對權利的訴求引發政府的互動,促使政府職能向服務性的進一步轉變。讓我們再回味一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稅收四原則吧。“一切公民,都須在可能的范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以維持政府”;“各公民應當完納的賦稅,必須是確定的,不得隨意。完納的日期、完納的方法、完納的數額,都應當讓一切納稅人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各種賦稅完納的日期以及完納的方法,須予納稅人以最大的便利”;“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盡可能等于國家所得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