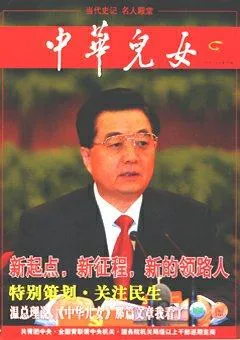李贛騮:亦醫亦政皆為民
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原副主席李贛騮,有著魁偉的身材、洪亮的嗓音、奕奕的神態和謙和的舉止,聆聽他那親切的話語與感人的往事,似在品味一首韻意豐富的詩。
作為醫師出身的李贛騮,近年來一直在為海峽兩岸統一鼓與呼,苦尋“良方”。2001年9月,李贛騮率團訪問了臺灣,與臺灣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把工作做到“家門口”,根據兩岸形勢的變化,加強了祖國統一聯誼工作,促進了與臺灣同胞和海外人士的了解,增進了友誼。同時,他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擴大與海外華僑、華人的交流與交往,多次率團到國外與當地華僑、華人社團進行了接觸和交流,在共同反對“臺獨”、推動祖國統一等問題上達成共識。
為人:秉承名門報國志
曾任廣州大元帥府參謀總長的“民國元老”李烈鈞,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在江西督軍任上又參加討袁的“二次革命”。 1933年,53歲的李烈鈞喜得么子贛騮,此前已有6子3女。李贛騮一出生,即由揚州來的奶媽喂養,其姆媽(上海稱親生母)華世琦為無錫名門望族,后隨其祖父到福建,畢業于福州女子學校,既善講福州話,又熟稔拉丁文,是一位有修養的知識女性。李贛騮父親成年征戰南北,家業及部屬的家眷均由夫人照顧、資助、代處有關后勤事務。
“辛亥革命爆發時,我還沒來到人間,關于父親當年上馬打仗、卸鞍吟詩的傳奇經歷,是從父輩那里聽來的。”據長輩們講,小時候的李烈鈞非常聰慧,能誦讀經書,貫通經學,曾以武寧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江西武備學堂學習。1915年12月,李烈鈞與蔡鍔、唐繼堯共商討袁事宜,決定以反對袁世凱復辟、捍衛共和國體為宗旨,組織“護國軍”。12月25日,李烈鈞與蔡鍔、唐繼堯一起,揭起護國討袁的旗幟,通電云南全省,宣布云南獨立,從此爆發了反袁護國運動。“多年以后,父親談起護國運動時根本不提自己,他說在這次護國運動中,要說貢獻最大,當屬唐繼堯。”其實,在這次運動中,李烈鈞起了關鍵作用,可謂舉足輕重;他這種為革命不計功名的無私奉獻精神,給李贛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小時候,李烈鈞一家到重慶,蔣介石安排住處被謝絕,全家寄宿歌樂山上的馮玉祥宅。“我自7歲上學起才開始記事。父親與馮玉祥都很反感蔣介石的獨裁,不滿他無團結抗日的誠意。歌樂山附近風景不錯,還有溫泉哩。記得父親講,馮雖與蔣是拜把兄弟,但一次白天馮到蔣處,打個燈籠,說太黑暗了,看不見世道。”
“父親雖自己已中風而半身不遂,但抗日情緒高昂,先后送5個兒子上前線,只有在香港當醫生的大哥與尚年幼的我沒有進部隊。”因病情加重,李烈鈞于1946年病逝。今天,李贛騮還對中共代表吊唁父親的情景記憶猶新:“當時,受毛澤東的委托,周恩來、董必武、葉挺等前來吊唁,我們兄弟姐妹正身著孝服跪在靈堂行禮。只見董必武手撫棺材說——李老先生,您的‘寧為烈士魂,不做亡國奴’的遺言我們銘記在心,將付諸行動。”李贛騮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父輩同仁們身處羈境時所表現出凜然正氣的愛國義舉和心系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勵我們為早日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加快民族復興偉業盡心盡力。
為醫:德技雙馨見柔腸

“家里軍人多,在這種氛圍里,我受到感染,小時候常常頭戴軍帽,肩佩徽章,腰別手槍。我從小就想當兵,追隨炮兵出身的父親。”當陸軍、海軍的5位兄長,如愿保家衛國,文韜武略,英姿颯爽。1950年,對于“七駿”之七的李贛騮受到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的激發,踴躍報名參軍。
十分理解兒子的母親,便義無反顧地同意他參軍。李贛騮選擇的兵種依次是炮兵、坦克兵、海軍。可是,經體檢,他的視力是100度近視。雖沒戴眼鏡,大小不一的“E”符號視力表卻模糊不清。于是,夢寐以求上前線卻泡了湯。
“好在從小在上海、嶺南中小學打下了些文化底子,被分配到哈爾濱醫科大學新設的俄文醫學系學習,開始人體解剖學、藥理學、病理學和微生物學等專業學習。”人生有許多十字路口,往往在某一關鍵路口的走向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好在是部隊委托培訓軍醫,也算后方軍, 李贛騮并不懊悔。誠然,事與愿違是常事,幸好學一行,愛一行,他也傾全力研學醫術。
1955年1月,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聽診器坐診的李贛騮,分配到北京中蘇友好醫院(現友好醫院)給內科專家做翻譯,不到一年專家返回莫斯科,李贛騮接通知將轉到中直第三醫院(現鼓樓醫院)當婦產科專家譯員。將進入隔科的特殊領域,他無奈地接受了。“誰叫我是醫生,沒有挑選的余地,不心甘情愿又怎么樣?不過,婦產科的蘇聯專家由于某種原因而沒到,我就沒當譯員,分到了內科當醫生。” 在李贛騮的心靈行為上只有“服務”二字,他說這是軍人與醫生的“紀律”。
1955年發生“康巴人叛亂”,中央組織工作團到川甘康青4省邊境的藏區做工作。當時不少人擔心出現不測之事而畏縮,李贛騮再次響應號召,主動報名參加其中的醫療隊隨中央工作組去藏區服務,活動在寒冷的康藏高原上的阿壩、甘孜、果洛等地,為缺醫少藥多病的藏胞就診除病。這里一望天地相接,雪域石峰,氣候獨特,空氣稀薄,常年活動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域,往往行走十余公里杳無人煙。“不到一個月,我們就不用翻譯,可以用藏話看病了。“當地稱我是‘門巴’,也就是漢語中的‘醫生’。我與藏區群眾關系很融洽,那時自己還取了個藏名‘才郎多吉’,就是‘長命富貴’的意思。”講到這里,豁達開朗的李贛騮情不自禁哼起《康定情歌》來,記者也不知不覺和唱起來。
兩年藏區實地體驗,對李贛騮年輕奔放的激情是一次升華。“叛亂平息后,我回來后到哈爾濱醫科大學進修了兩年。重新分配時,我本可以自己選擇,當問我愿意到哪去,我說服從組織分配——邊疆都去了,還有什么地方不能去。當時,說河北缺人,就把我分到河北;后來,河北衛生廳說邯鄲缺人,我又分到了邯鄲第一人民醫院。”的確,當時他可分到首都北京,也可分到上海,自己畢竟從小是在上海長大的,自己的母親那時還在上海生活。李贛騮擁有一千零一個理由,可找一個“好地方”安家落戶,但他又自愿到急需醫務人員的新興城市河北邯鄲做了一個默默無名的內科醫生。
在邯鄲第一人民醫院他是一個骨干醫生,論職稱早該是主任醫師了,但當時“左”傾的氣候,只能負著責任,不能有名,可他不計較這些,“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就行了。1964年國慶那天,邯鄲河沙鎮的一個工廠發生全國首例大規模的氯化鋇中毒。當時無搶救好辦法,中毒人數多、面積大,面對患者,作為事故搶救組組長的李贛騮成功地利用最新的人工呼吸心臟按摩辦法搶救。他常常伏下身,扯下捂嘴的紗布,嘴對嘴地為患者作呼吸,一次、二次、三次……,有時吸出的是一口粘糊糊的痰液。每當患者死里復活,大汗淋淋的他欣慰地笑了。他用這種措施搶救了多名危重患者,當各報、刊記者蜂擁圍住他,追問:“當時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臟不臟?”“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否展現在腦海中?”“毛主席語錄中的哪一條你想到了?”一向率直的李贛騮直言不諱:“實在是沒時間去想那么多,我覺得一個救死扶傷的醫務工作者面對生死關頭的病人,必須這樣去做!”
為政:“做官”為民是責任
“1980年,開放政策下,國家允許去海外探親,我申請到香港探親,海外的姐姐們都趕到那里一塊相會。”李贛騮所始料不及的是,在報申請時醫院方面不敢批復,擔心他一去不復返,因為他曾在“文革”中遭過孽、受過罪,在牛棚里“改造”過。于是,這份申請被擱置下來。眼看兄弟姐妹在港聚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這邊赴約的時間還遙遙“無期”,這下可急壞了李贛騮。無論與院方如何反復理論,他們也不敢同意,最后這申請竟轉到了市委辦公會上專題討論。好在李贛騮在當地有點小名氣,加之時任市委書記的岳岐峰開明而果敢,明確表態“讓他去,他不會不回來,我了解他”。為此,李贛騮獲準半年的探親假。
回來后,李贛騮作為“海歸”典型應邀到河北數個城市巡回報告,并回母校哈爾濱醫科大學作演講。他的樸實話語、真實感受深深打動了聽眾:“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雖然和愛人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那好比人生四季的冬天,哪能沒一點風寒。冬天過去了,不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嘛!我們的祖國,改革開放不已經迎來了萬紫千紅的春天嗎?當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又怎能舍她而去?!”在母校原定4場報告,最后不得不再應師生要求增補了兩場。
很快,李贛騮的名字傳開了,從邯鄲、從河北傳到了中央。一天,地方通知第二天中午12點中央電臺有重要新聞,要求收聽。次日,各個單位都在組織收聽中央電臺新聞。“文革”時這樣的活動多,好長時間沒組織類似的活動了,大家積極性很高,聚在一塊認真收聽廣播。一收聽才知是葉劍英發表對臺“十條”,聽完以后,大家余味未盡,接著收聽下去。沒想到廣播里傳出播音:“下面一個節目是河北醫生李贛騮訪問香港的感想,歡迎大家收聽。”這下,大家可更有精神了:“李贛騮不就是我們邯鄲的那個大夫嗎?”在收聽中,大家的問號被打開。本是組織收聽“葉十條”的,沒想到地方的人也上了中央臺重要新聞板塊。從此,一傳十,十傳q37wLM5LSf9YSpRS0i7qyh7IiubQuuNI5178XcmRZlQ=百,“李贛騮”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當初批準我赴港的岳岐峰書記,現在已是全國政協常委,我們還時有來往。”如今,李贛騮還在感念當年的批復人。
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清除了極左思潮。當時開始吸收黨外人士參加政府工作,但有條件:一要是知識分子,有文化;二要社會關系復雜的,以體現不注重階級成分;三要歷史復雜的,以體現既往不咎;四要挨了整還不埋怨共產黨的。“我恰好符合這些條件,我是50年代的大學生,有海外關系,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是‘文革’中的‘反動學術權威’與‘漏網右派’,而且我受了整而自己沒多少埋怨。”李贛騮在采訪時戲言自己因戴了好幾頂“帽子”而無意間當上了地方政府的官員,并笑言自己因個人的地方知名度而無形中助了自己的“官運”。
1981年,李贛騮走馬上任邯鄲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他一下子由一個恢復職稱的副主任醫師走上了主管全市文化、教育、衛生、廣播新聞、體育的副市長。當選“父母官”后,沒有一點高高在上的飄飄然,他還是“赤腳醫生”那副裝束:摘不掉的可笑的寬邊近視鏡,夏天一件汗衫,一條長短褲,一頂太陽帽,平平常常的裝束。
“早在念大學時,我就向組織遞交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可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實現個人志愿。到了‘文革’更是無法企求,80年代我又是舊話重提。這時,有人動員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產黨。對方講,參加民革也能發揮作用,只要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誠懇工作。”恰逢民革發展成員,李贛騮聯想到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與社會關系,認定自己在民革中能發揮作用,于是1981年正式成了民革的一員。當了兩年副市長后,李贛騮憑個人的優勢又同時出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不多時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贛騮雖身居廟堂之高,但他對醫務工作依然眷戀。“后來政務日益繁忙,身不由已喲!”說到這,他不無遺憾。
為家:風雨相依情更真
“我夫人也是哈醫大畢業的,小我兩歲。沒想到,在邯鄲工作期間,有緣份的兩人又走到了一塊。”李贛騮有一個嫻淑溫存的好夫人傅維儉,1999年在農工黨中央醫委會辦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
傅維儉是遼寧鐵嶺人,父親是留學日本的洋醫,回國后開了一家不小的醫院。1955年秋,她帶著金色的夢想跨入了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門檻。
“我在哈醫大進修時,正‘反右’,記得一回大字報上有她的名字,盡管當時我并不認識她,但印象很深,不知怎么的。或許這就是所謂冥冥中的緣份吧。”那時,傅維儉臨床醫學成績優秀,班級、學校的各項活動帶頭踴躍參加,只因她如實地跟同學講“我不是享受助學金讀書的、農民生活還較苦”的話,在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湊數當了個“右派”。憑她品學兼優的學業和表現,她可留校,也可進大醫院,或入機關走從政路,可偏偏因“右”別親離鄉到了河北邯鄲,當一名醫科專科學校的教師。
男婚女嫁,這是天經地義的常情。由于都是哈醫大的校友,李贛騮認識了邯鄲醫專的教師傅維儉。加之,傅維儉常常帶學生到李贛騮所在的醫院實習,兩人更有機會走得更近。“校友們經常聚在一塊,聊天、會餐、郊游。在交往中,我由同情她,進而產生了感情,由感情滋生了愛情,以后我倆就結婚了。”性情之人李贛騮尤為的直率、開朗,從不口諱個人的“絕對隱私”。“犯傻”的李贛騮當時不乏追求者,可他偏偏“傻冒”地看上個子說不上高、又戴著一頂沉重“右派”帽子的傅維儉。有人迷惑不解:“你為什么看上一個‘右派’?”他如是說:“‘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可以改造,我相信她是能改造好的。婚姻是講緣份、講感情的。”
一把鐵皮砸成的水舀子,滴上幾滴油,打兩個雞蛋,點著舊報紙,就成了荷包蛋,從食堂打回的飯,吃著蠻香,小日子也很滋潤甜蜜。李贛騮與傅維儉沒有任何說道,也沒有什么裝飾,簡而又簡,結合成一對相敬齊眉的夫妻。
后來,李贛騮雖如日中天,職位變了,地位變了,但對傅維儉的真愛沒有變。每逢休息的日子,他總是設法抽出時間陪夫人到公園走走,或燒幾個拿手好菜“犒勞”家人。對于李贛騮的性格最了解的是風雨相依的傅維儉,自從他當上領導,傅維儉更主動更多地搶干家里家外的活計。如今,李贛騮從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了,終于有時間同夫人一起到四處走動。
李贛騮興趣廣泛,喜歡看小品,對趙本山的表演尤為喜愛。雖年輕時“舞功”不凡,但后來因公務繁多而不得不“割愛”。4個子女,沒一個端“鐵飯碗”或坐“鐵交椅”,或在民營公司做自己的活,或在幼教崗位當“娃娃頭”,沒一個是靠父親的特殊地位而得取優待的。“靠他們自己去闖,沒能耐也不能埋怨哪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