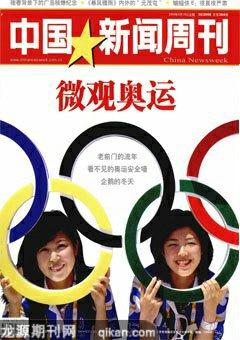關于中國的樂觀與悲觀
劉婉媛
“樂觀的一面告訴我,中國總能摸著石頭順利過河:而悲觀的一面也在擔憂,中國的改革開放接著要面臨比過去更刁鉆、更復雜的問題,中國能像以前那樣有驚無險地克服每一個困難嗎?”
關于改革開放,關于中國30年以來的變化,這個題目對于許多外國人而言猶如霧里看花。而當這位外表內斂的英國人抬起這個話題,言語頓時滔滔不絕,眉目間難掩興奮。
托尼·賽奇,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哈佛大學中國高級官員培訓班的主要負責人。事實上,這個項目是他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福特基金會駐華首席代表期間一手促成的,如今,這個項目已經培訓了6期中國司局級以上的高級官員。
與中國的淵源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倫敦大學碩士生賽奇從香港步行過羅湖橋來到了深圳。在北京,他迎頭趕上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幫”……那個與世隔絕而又驚心動魄的中國,讓這位年輕人百感交集。30年過去,中國已經今非昔比,而賽奇依然感慨:“這個國家永遠讓我感到驚奇。”
“那時,緊張的氣氛遠遠超乎我的想象。”
中國新聞周刊:當年,為什么選擇來中國呢?
賽奇:我來中國時是1976年。當時,我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政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對中國感興趣是有原因的:那個時候,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左翼學生運動風起云涌,我也是其中一個積極分子。對我們這些學生而言,毛澤東就是左翼運動的一個標志符,我們在游行中以他為利器,批評自己政府。可當時我總有個感覺,我們對中國肯定有很多誤讀。我們這些西方人,沒見到過中國是什么樣子,只能看到中國的一些宣傳冊說中國是如何的偉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妙不可言。而我自己,也讀過毛澤東選集。那么,真正的中國是什么樣子,我很想去了解,所以就選了中國作為研究的方向。
不過,我從沒想過自己真的有機會去中國,直至中英政府之間有了交換學生計劃,我很幸運地獲得了這個獎學金。
中國新聞周刊:那個時候的中國,給你上的第一課是什么?
賽奇:其實,第一印象挺美好的。我和同行的15名英國學生先飛到香港,從香港步行穿越羅湖橋來到深圳。當時的內地與香港邊界,沒有一點喧囂,沿途還有好多水牛,一切都那么悠游自在,那么自然閑靜。
直至在北京語言學院落腳,幾天后我才發現,緊張的氣氛遠遠超乎我原有的想象。當時,我幾乎不懂中文,也就在來華前臨時抱佛腳學了幾句“你好”“廁所在哪里”之類的話,不過,我發現即使中文再好也無法和中國人溝通。當地人對我們非常好奇,盯著我們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話,他們就會退避三合——他們認為和外國人說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有時候我們搭乘公共汽車。你知道,公共汽車一到站,所有中國人就一哄而上。但只要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也在等車,他們就會馬上讓出一條路來,讓我們先上車、坐下,接著,他們又嗖地一哄而上。在車上,中國人會和我們保持距離,公車永遠都那么擁擠,但我們身邊總有大約5米的空位。
在語言大學呆了三個月后,我就去了南京大學,成為那里自1939年以來的第一批“資產階級”學生。在南京大學,他們破天荒地讓我在校足球隊踢球。不過,因為我是外國人,他們都不愿意和我有任何觸碰,更別說是鏟球、踢人之類的動作。所以,我們隊當時的策略就是都把球傳給我,對手看到我控球,就全跑開了。
我在南京大學主修中國歷史,剛開始是學習中國當代歷史,但那純粹是浪費時間,因為課本上講的都是什么“兩條路線斗爭”“修正主義路線”。后來我改修中國近代史,研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什么的,還算有點意思。
盡管如此,當時在學校、在課本上學的東西并沒有太多新意。真正讓我學習到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貧窮的、封閉的中國。那里的人們對外界一無所知,而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是不需要也不應該了解外面的世界。人們沒有選擇,當局對政治的控制嚴密得超乎外界所有人的想象。三天兩頭就有一次政治學習。當看著人們坐在政治學習會上,百無聊賴直至打盹,我就覺得難過。
“一夜之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與外界接觸的渴望”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什么時候第一次聽說鄧小平的名字?
賽奇:我在來中國之前就聽說過鄧小平了——那個時候,只要對中國有點興趣,都會知道他的名字。不過,我在中國上大學的時候,雖然學校老師知道我們這些西方人對鄧小平很有好感,但從來不和我們談及這個話題。直到有一天,我記得是粉碎“四人幫”以后不久,我的一個老師興沖沖地跑進我的宿舍,說:“托尼,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肯定讓你很高興……”
“我知道,鄧小平恢復職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聽了BBC。”
那個時候,我聽到身邊的中國人都在興奮地談論:鄧小平回來了!大家會漲工資,下鄉的知青會很快返城與家人團聚,政治斗爭會結束。
我剛到中國的時候,我們這些外國人是不允許有中國人同屋的。但粉碎“四人幫”、鄧小平恢復職位以后,學校馬上就安排一些中國人和我們一起住。他們大多數是曾經在蘇聯學習物理、化學等學科的人,安排和我們同屋是為了學習英語,因為他們馬上就要被派去英國和澳大利亞深造。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我感覺到了中國人渴望與外界接觸、向世界學習的前所未有的熱切心情。
中國新聞周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你對中國今后的發展有什么預期?
賽奇:我想,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意識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折點。直至今天,我在哈佛給學生講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講解內容。
即便如此,我萬萬沒想到中國從此會發生那樣天翻地覆的變化。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在你看來,什么是中國改革面臨的最大問題?
賽奇:事實上,當年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當今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改革,這個問題比農業改革或者發展特區經濟都要艱深復雜得多,其次是逐步建立現代的政府結構,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在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趨勢下,逐步建立一個負責任的、透明的政府。這兩方面無疑是最困難的。
我想,中國新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很重視民生問題,也將農村地區的發展列入首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上述問題不是幾年間就可以妥善解決的,需要至少一代人付出努力。
“中國會繼續不斷地讓我感到驚奇。”
中國新聞周刊:大家都說中國是無法預測的,但我還是想為難你一下,預測30年以后中國會是什么樣子?
賽奇:(大笑)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只能告訴你一點:中國會繼續不斷地讓我感到驚奇。30年前,如果你告訴我中國30年后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肯定會嗤之以鼻:“你瘋了!怎么可能!”
每每中國的發展出現困難阻礙,當我們認為中國可能沒有辦法的時候,它最終總能找到解決的途徑。中國人摸著石頭過河,還總能找到過河的石頭。所以,我內心樂觀的一面告訴自己說:中國一定會繼續發展,繼續進步。
但是,我也有悲觀的一面,這一面的內心會提出質疑: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會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當前,國企改革就要進入最困難的階段,而政府執政也面臨許多挑戰。與此同時,一些新的挑戰也擺在了面前,比如環境問題、能源問題、社會公平問題等等。這些因素,都讓中國的未來難以預測。
但無論如何,中國一直在變化。這30年的改變不僅僅是經濟上,今天中國人的自由也是前所未有的。試想30年前,我們這樣的采訪和對話怎么可能出現?15年前,甚至10年前都不可能出現。我相信,變革一直會延續。中國人的極度靈活性,中國人對新思想、新事物的接納,都在過去30年里得到了證明。
中國新聞周刊:在過去的50年里、中國有哪些東西是你懷念的嗎?
賽奇:我懷念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車輛寥寥的大馬路上亂竄的日子。(笑)
確實,這30年來中國失去了一些東西。在我看來,現在的中國人似乎比以前自私了。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然而,30年來,中國的一些傳統社會關系結構漸漸解體了。
當物質豐富的時候,人們就會更多地去考慮人生的價值和信仰。中國的年輕一代在逐漸成長,他們沒有經歷過動蕩和貧困,他們會對這個社會有著和父輩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他們會給中國帶來什么變化,這也是一個大家非常關注、非常有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