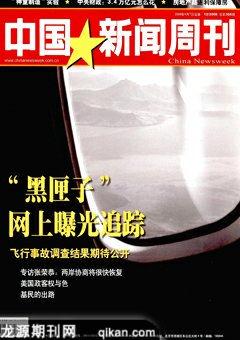《黃石的孩子》:直面戰爭的別樣風景
張江南
它是近年外國班底制作的中國背景影片里最沒有文化隔閡的一部

在當今“營銷似乎決定票房”的國內電影市場浮躁的環境下,電影《黃石的孩子》的發行商也絞盡腦汁地拋出了種種噱頭。可事實上,觀眾對于這部影片關于“好萊塢”“戰爭大片”等關鍵詞的所有期待未必成真。
首先該片不是一部抗戰背景的戰爭大片:雖然背景設置是抗戰時期,但在開場短暫的關于南京浩劫中慘烈屠殺的描繪之后,戰爭元素即被導演牢牢固定僅作為故事發展和人物心理形成的背景。
電影講述的是主人公英國記者何克如何帶領60多名中國孤兒,逃離戰爭的故事。所以影片整個故事幾乎都是在后方展開,回避了對戰爭的正面描繪,除了偶爾飛機蜻蜓點水似的轟炸,最火爆的所謂戰爭場面也只是火車站的小規模交火了。
曾指導過《明日帝國》的導演羅杰?斯波蒂伍德并未有更多演練好萊塢式宏大動作場面的機會,如果硬把電影與《拯救大兵瑞恩》扯上關系,基本是混淆視聽。而拿何克的拯救行為與辛德勒對比,也難以對位。
在故事進展中,何克并沒有如后者那樣艱難復雜的人格轉變、升華,影片只是通過何克目睹機槍攢射和縱火焚尸,完成了其從記者到具犧牲精神的英雄的成長。之后的大段的篇幅里,英雄何克只是如白求恩大夫似的,表現其國際主義義舉。若不是導演一再以“十字架”符號強調其宗教上的精神根源,何克幾乎等同于主旋律電影的典型人物。
反倒周潤發扮演的新四軍在西方視角的詮釋下,意外地煥然一新擺脫刻板銀幕形象,表示出知性、幽默、人性化的氣質。雖然這可能令多數中國觀眾不能接受,但周潤發作為何克精神導師的表演還是交足功課,無可厚非。
兩人與外國女醫生麗的三角戀情,最終既未挑起國際矛盾,又符合民族大義,浪漫抵死之后,可謂和諧。
《黃石的孩子》是其欣然公司出品的第三部電影。前兩部分別為許鞍華《姨媽的后現代生活》和程耳《第三個人》,皆非直瞄市場和票房之作。而這次投資接近3億人民幣跨國精良班底制作的《黃石的孩子》,票房前景依然不容樂觀。
《黃石的孩子》屬于標準的獨立電影,帶著濃重的歐陸文藝片氣質。而這并非導演意志所致,顯然是受本片的制片人阿瑟?柯恩的影響。這個瑞士人曾經7次獲得奧斯卡獎,他的作品包括大家熟知的《放牛班的春天》《中央車站》等。而《黃》一片從劇作上看,最核心的部分恰好都是來源于上面提到的這兩部片:影片故事的大結構建構于何克在攜60多名中國孤兒逃避戰火的旅程之上,他本人也在這個旅程中蛻變成孩子們替代性父親的角色;而這在《中央車站》里,反映為婦女攜男孩踏上尋母旅程并終成為替代性母親。
不同的是《黃》中孤兒數量更為龐大,旅程也因戰爭和惡劣環境(高原、沙漠、龍卷風)更加危險——這令影片獲得巨大的戲劇空間同時,導演的視覺呈現上也有令人稱贊的發揮。
相較而言,《黃》一片聚焦何克與孤兒們情感關系的細膩描繪,基本脫胎于《放牛班的春天》:何克與一群被戰爭陰影籠罩、有嚴重心靈創傷的孩子們相處時,擔當起老師的角色——教授英文、種糧種菜、打籃球,卻不斷遭遇“壞孩子”的敵對舉動。開始時他被孩子們騙去棒打了一頓,最為反叛的石凱稱呼他是豬先生,趁著夜雨破壞何克好不容易弄好的發電機,下令讓其他孩子捅壞何克貼好的為孩子們擋風的窗戶紙……這些都很容易在同樣講述二戰背景下法國后方清靜學校里,老師教育頑劣學生的《放牛班的春天》片里找到對應之處。
不同的是頑劣的孩子好教,被戰爭傷害的心靈卻難以康復:親歷父親被日本人殺害,母親和姐姐被奸殺的壞孩子石凱為復仇而死;而當何克準備帶著孩子們轉移時,一直表現最為乖巧內向的青,卻為逃避戰爭陰影選擇了懸梁自殺。性格截然相反的兩個孩子,最終都殞命于戰爭陰影中,影片由此發出全篇中最催人淚下的反戰呼喊。
《黃石的孩子》,戰爭搭臺,情感唱戲,可謂近年外國班底制作的中國背景影片里最沒有文化隔閡的一部。它雖未必能滿足主流觀眾的“戰爭大片”標準,卻打開了一扇直面戰爭和人性的窗,讓我們得見別樣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