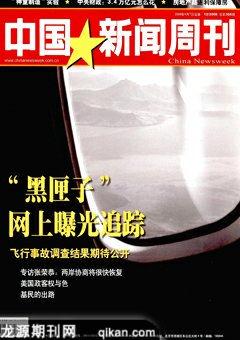中國為什么要負起國際責任
周 琪
“和平發展”和“做負責任的國家”,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一個和平發展的國家將不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相反,它將在現存的國際體制內基本按照國際規則行事,承擔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
當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在國際場合上強調,中國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在成為強國的過程中不會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時,實際是在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將努力成為一個在國際上負責任的國家。
“和平發展”和“做負責任的國家”可以看作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一個和平發展的國家將不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相反,它將在現存的國際體制內基本按照國際規則行事,承擔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這樣,中國和平發展成為強國的過程將可能成為歷史上的例外——根據對國際關系的研究,所有歷史經驗都表明,新的大國的崛起會顛覆現行的國際秩序,引發新的爭奪勢力范圍的戰爭。
承擔國際責任,是一個可以把“和平發展”進行量化的衡量標準。“和平發展”是一個總體過程,在這個過程沒有完成之前,它在其他國家的眼中可能只是一個承諾: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承諾不挑戰現行國際秩序和規則、不對世界上的主導國家構成威脅,特別是戰爭威脅。
“負責任的國家”或“承擔國際責任”,是中國想為自己樹立的國際形象,這一點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例如,根據前美國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蘇珊?舍克(謝淑麗)在《脆弱的超級大國》中的敘述,克林頓政府在其正式的政策演講中就已提到,中國政府開始把中國說成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她還留意到,在中國學者中,有人在1999年就建議,中國應采取更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姿態,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進入21世紀。
然而,在中國國內,關于中國國際責任的看法并非沒有分歧,其中有三個論點特別值得加以討論:
一、“所有的國家都只關注其自身國家利益,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觀的‘國際責任”。
持這種觀點的人可能僅僅是少數,但它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這個觀點忘掉了一個已經被國際上大多數人認識到的基本事實:冷戰結束以來,隨著東西方兩個陣營的消失,國際上非傳統安全威脅極大地加大了,包括恐怖主義、毒品走私、環境污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人道主義危機和傳染病等。應付這些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需要各國政府的合作和共同努力,因此就產生了各國共同的國際責任。換言之,現在所說的國際責任嚴格說是在冷戰后的條件下才得到普遍承認的。
二、“中國從來都是負責任的國家,新中國建立以來,毛澤東關注世界革命,之后各時期的國家領導人都有對國際事務的關懷。”
這個說法的問題在于概念混淆。恰好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際,中國放棄了世界革命的觀念和對其他國家內推翻現政權的武裝斗爭的支持。如前所述,在冷戰結束之前,并無當今意義上的國際責任可言。也就是說,毛澤東在推行世界革命中所負的“國際責任”,是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與今天中國在發展成為強國的道路上所要負起的國際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簡單地認為兩個階段都是“負國際責任”,將會削弱中國努力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在新的國際環境下的特殊重要意義——走和平發展道路。
三、“國際責任論可能被美國利用來限制中國的發展,具體地說,美國可能把同中國國力不相稱的國際責任強加給中國,來減緩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或把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選擇統統放到中國國際責任的籃子里,把中國在世界上尋求能源資源、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都看作是中國不負國際責任的表現,要求中國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做出犧牲或讓步。”
這些問題是切實存在的問題,的確需要中國認真一一應對。實際上,這里所謂的中國的“國際責任”問題,不過是對處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在許多方面利益不同的兩個國家之間矛盾和沖突的曲解。
然而,無論如何,美國等國家的壓力不應成為中國放棄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努力的理由,正如人不能因噎廢食一樣。實際上,中國的努力在國際上已得到了回報。根據英國BBC在2004年11月到2005年1月的調查,在20個國家中,17個國家的大多數被詢問者認為,中國的國際作用是積極的,這一比例大于關于蘇聯和美國的全球影響調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