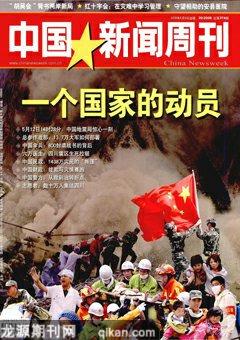守望相助的安縣醫院
嚴冬雪
地方搜救和救治是國家救援體系的神經末梢,也是國家救援過程的開端。在外部救援體系發揮作用之前,地方系統往往已經開始運作,有時甚至是以孤島的形式展開著
與北川比鄰的是安縣,北川很多人是安縣的親戚。
5月12日14點28分過后,安縣人民醫院接到的第一批傷員來自北川。
這是安縣的首個救治點,從地震發生到建立不過30分鐘

剛穿好一只鞋子就被震倒在地的醫院副院長胡建中,從宿舍地上爬起,奔到50米外的住院部。醫生和護士們正忙著將病人從樓上轉移下來。安縣人民醫院這棟七層樓的住院樓有五層是病房,每一層醫護人員都在轉移病人。
不到半小時,在余震不時的搖晃中,一百多號病人安然無恙地轉移到醫院的籃球場上。凳子來不及搬出來,很多人坐在地上,家屬們舉著輸液瓶子。
這時,一大批傷員從外面進來,大部分是抬著來的,軋斷的地方血肉模糊,像被絞肉機絞過。他們來自緊鄰安縣的北川。
北川人、護士王培菊跟幾個醫生開始搶救傷員。胡建中跟另幾位副院長一起,沖回住院樓,把被子、床墊從窗口里往下扔。下面的醫生把墊子鋪好,讓病人躺下,將被子蓋在因失血過多而渾身發冷的病人身上。身為副院長的胡建中又開始挨個房間搜索有無遺漏病人,最后一個離開大樓。
車和人運著傷員不斷涌進來。不管是三輪車、拖拉機、汽車,能用的都用上了,護士、醫生、院長都在抬病人,清潔工也幫著抬病人,沒有一雙多余的手。
胡建中突然想起還有兩位護士困在電梯里,忙帶著幾個人去把電梯門撬開。兩位護士前腳邁出電梯,后腳就直奔籃球場救護。
這是安縣的首個救治點,從地震發生到建立不過30分鐘。
有的傷員抬過來時已經休克。有的剛剛送來就死掉了。“得把死人弄到角落里。場地太小,我們就放在乒乓臺的角落里。”胡建中說。送過來的絕大部分傷員是北川和永安的。
一對母子,同一副擔架抬過來,孩子只有8個月,送來沒幾分鐘,母子就都沒了。“手術臺”是從門診部抬出的3張檢查床,露天下各相隔一米。一些必須截肢、縫合的病人,都在“手術臺”上進行。偶爾空閑出來的幾雙手,飛速奔上樓去抬病床。病床、藥品、器械,能搬的都搬了,住院樓已經搬空了。
籃球場還是太小,不到一個小時,傷員就放不下了。安縣人民醫院的辦公室主任羅鳴跑到安縣中學考察地形,因為整個安昌鎮開闊點兒的、大一點兒的只有安中的操場。羅鳴回來對胡建中說:不行,安中人滿為患,靠我們的力量是疏散不了的。
下午4點,安縣政府派人來醫院,說安縣中學挪出了一塊地方,可以搬過去。
20公里外的北川醫院已經完全坍塌,醫護人員都被埋在下面。這里也是北川傷員的首個救治點。
大地震當晚,行政人員的本子上,登記了1009名傷員,死亡20多個
內科主任趙鳴歧跳上一輛救護車,帶著王培菊和另幾名醫護人員,趕到安縣中學操場。6張課桌一張“床”,搭了4張“床”,沒有墊子,傷員直接躺“床板”上。
早已不分科室,清創、縫合、輸液,能做事的都用上。
操場擠滿了人,學生很多。“幾個學生在對我喊:‘阿姨,救救我吧,我不想死。我卻沒有辦法。”趙鳴歧哭紅了雙眼。“我接到的第一個傷員就是學生,下肢完全砸爛,救了十幾分鐘,沒了。”
入夜,毛毛雨飄下來,落在一身塵土、兩眼淚水的人們身上。到處都是惶恐無助的人。不間斷的余震給了傷者無法預知的恐懼,在災難過程中被無限放大,讓人看不見希望。唯一能看見的,似乎只有死亡。
到處都是北川人。王培菊碰到弟弟在北川中學的同學,得知地震發生時,弟弟所在班沒有在平時的新教學樓里,而是在另一棟稍舊的樓里上傳媒課——一棟五層坍塌成一層廢墟的樓里。“當時聽到十分難受。十分想回家看家人,但我穿著這身工作服,就有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我還是沒有回去。”王培菊開始哽咽,“我跟北川的老師打聽挖掘情況。他說高二·8班基本還沒開挖,基本沒有存活率。”講到這里,未滿21歲的她無法克制,大哭起來。
12日當晚,唯一一位負責記錄的行政后勤人員的本子上,登記了1009名傷員,死亡20多個。安中的傷員已經超過安縣人民醫院。這里成了主戰場。
安縣疾控中心、保健院的救護人員都趕到安中來了。休假的、退休的醫護人員,沒等誰的通知也紛紛趕來了。縣內救護力量開始增大。
縣外的援助還沒有消息,所有車輛呼嘯著從安縣經過,奔往北川。醫院一位后勤部長跑到門外馬路中央,硬攔下一輛車頭被砸扁的工程搶險車。車上有柴油發電機,加上蠟燭和醫院的手提應急燈,安縣的醫生們在微光中度過了一個最忙亂的夜晚。他們來不及戴手術帽,穿著工作服四處跑動,感覺不到腳下不斷傳來的震動。也沒有醫生來得及抬頭望天。當晚是有月亮的,紅色,像是被血浸過。
13日下午,不知道幾點,醫生們稍微閑暇一點。不知道誰遞給胡建中一包方便面,他就掰成幾塊,問“誰吃,誰吃?”大家都不吃,說吃不下。他就一人把它吃了,沒有水喝,干啃掉了。
截至13日下午4點,從記錄員本子上有證可查的傷員是4000多名。13日晚上,兩個救治點已經完全飽和,安縣必須成為一個中轉站,重傷員開始往綿陽轉運。
“我們兩臺救護車的轱轆就沒停過。”胡建中說。車輛根本就不夠。來了兩輛大卡車,醫生們冒雨抬著傷員往大車廂里塞。藥品和干糧也開始送進來,有了5頂帳篷,一頂作治療室、一頂作藥品庫,其余的都用來安置傷員。
外面的空地上,醫生們坐著、站著、蹲著,什么姿勢都有。下著大雨,有的醫生撐傘站著就睡著了。
趙鳴歧負責看守醫藥庫。傷員多她就參與救治,少就跟兩位護士在藥品庫外值守,“這可是救命的東西。”8天后,胡建中說起手下的員工,沒忍住眼淚:“一天半里,我們的醫護人員沒有吃喝一點東西。院部也始終沒有開過會。”
14日早晨,水和餅干運到,情況緩解了很多。王培菊和另一位同事合喝了一盒牛奶。通訊仍然中斷,沒人知道她在北川的家怎樣了,父母和弟弟都在哪里。
把空紙箱鋪在地上,同事終于可以輪班休息了
“藥品不是很缺,是奇缺。”胡建中說。
4000多傷員的重擔,壓在這家只有200張床位的醫院身上。安縣也是災區,樓房不能住,物資運不進。傷員需要止血、包扎,平常的無菌操作是不可能的。鋼針、刀片,很多的器械只用消毒液浸泡一下就接著用。
胡建中說,安縣是個小地方,縣醫院的設備在同級二甲醫院里本來就比較落后,跟江油、三臺等地醫院的財力、物力相差甚遠。
信息傳不出去,大家全是聾子、啞巴。人們搭車、步行到救治點來尋親。大部分人是北川的,也有安縣高川鄉、茶坪鄉的。“但多數找不到。”胡建中說。
14日深夜,手機終于能打通了。跟很多北川人一樣,王培菊依然沒有接到家人的電話。
王培菊的生父早已過世,現在的組合家庭里,繼父對她和弟弟十分好。沒有血緣關系的爺爺是目前唯一有音訊的人,老人說在安置點生活不習慣,硬是回到已成平地的北川。他說,孫女兒。現在只有你一個人有音信,我把家給你看著,你回來還覺得有一個家的感覺。“但是那個家已經……沒有了,我沒有家了,我只剩一個人。”王培菊大哭起來。
15日,又有幾頂帳篷運來,胡建中就分了兩頂給職工家屬。老人們自己搭建五花八門的帳篷。他們的兒女都在搶救傷員,沒有時間幫忙。
到了晚上,看管藥品庫的趙鳴歧把空紙箱鋪在地上,墊出一尺寬的空間。她讓同事在上面靠著藥箱躺一會兒,終于開始輪班休息了。
已成危房的宿舍就在50米外,胡建中3天都沒回去,進去刷個牙,又出來了。“直到17日,4天半的時間里,算上打盹的時間,我們好多人的睡眠加起來也不到8小時。”胡建中說。
直到20日,仍然沒有米飯可吃,只有餅干。僅剩的一點方便面都留給了值班醫生。
情況在好轉之中。醫院在花悄的分院來了第四軍醫大學的一個野戰醫院,為儀器全毀的縣醫院帶來一臺便攜式X光機。整個安縣要拍X光的都去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