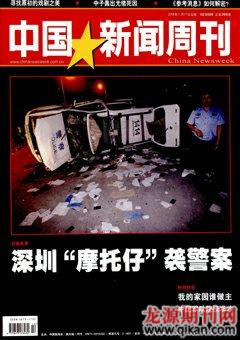徐志摩的別樣見解
邵 建
為何徐志摩對迷倒眾多中國知識人的蘇聯有一種特別的洞穿力?這還要看他的留學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社會對當時蘇聯的看法,其實是一種考量,它考量著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知識人的觀念與眼光。那個年代,彌布著一種激越的“向左轉”的氛圍,因而知識人包括青年對蘇聯的認肯在當時不僅是多數,也是主流。某種意義上,它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僅僅視為詩人的徐志摩,就是一個較為清醒的例外。
那時,有過這樣一幅英國漫畫,是諷刺蘇聯的。畫幅上“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此畫的諷刺意味很明顯,這一切都是表面的、假的、做給外人看的。但看過此畫的魯迅不這樣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認為該畫是“無恥的欺騙”。過后,魯迅專門作文“我們不再受騙了”,批評英語世界對蘇聯的攻擊和造謠,不但為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辯護,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價值立場和眼光。
但如果把這幅畫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態度會如何?事實已無可能,魯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經魂歸天府。然而,這個問題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難索解。可以肯定,徐志摩不會認為這幅畫是欺騙;如果欺騙,也是畫所畫的那個內容。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國,結識了英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韋爾斯。是年韋爾斯曾往蘇俄游歷,歸來后用游記記寫見聞。徐志摩讀后,特意為之評論。這便是徐文中韋爾斯親身歷俄的小故事。當他去參觀一所小學校時,問學生平時學不學英文,學生一齊回答:學。又問,你們最喜歡的英國文學家是誰,大家一起回答:韋爾斯。進而問,你們喜歡他的什么書,學生立即背誦韋氏著作,竟達十多種。韋爾斯很不高興,他相信這些學生是“受治”。后來,他特意不知會蘇俄接待方,獨自來到一所條件比前面更好的學校,又把那些問題一一提出,結果該校學生一概曰否。接著,韋爾斯又來到該校的藏書室,書架上沒有一本自己的書。韋爾斯什么都明白了。于是,徐志摩也什么都明白了,他寫道:“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類如此也。”
為何徐志摩對迷倒眾多中國知識人的蘇俄有一種特別的洞穿力,這還要看他的留學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留學美英時的徐志摩不是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而且他也曾用肖伯納的前半句話描述過自己:一個30歲以下的人不信社會主義是良知有問題(后半句為30歲以上的人如果還信是理智有問題)。但,在徐志摩短暫的一生中,他最想追隨、同時對他思想影響最大的人,是英國哲學家羅素。1920年,徐志摩寧可不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也要橫渡大西洋,到英國跟羅素去念書。徐志摩把羅素比為20世紀的伏爾泰,可見其“高山景行,私所仰慕”。
羅素在英國時是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出于對蘇俄價值理念的認同,1920年,他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去蘇聯考察。這一去不打緊,所謂乘興去,失望回,不但沒有接受其洗禮,反而把對蘇聯的看法寫成了批評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徐志摩不但讀過此書,同樣,也為它寫過評論。其中,羅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筆下得到了呈現,徐介紹羅素所以拒絕蘇聯,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達到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一蹴而就,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后者言,布爾什維克的理想乃是一個烏托邦。但,為了實現它,需要采用慘烈的暴力,這為羅素所懼怕。羅素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無法不反對蘇俄那種流血的激進。在他看來,人類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產生暴烈。
盡管徐志摩評論羅素和韋爾斯時對蘇聯尚未那么反感,其議論甚至有所持平;但這兩位有人道主義底色的英國佬潛在地影響了他,說到底,他自己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有趣的是,1921年徐志摩發表這兩篇事涉蘇俄的評論時,年輕得才24歲。魯迅是遠在30歲后轉信社會主義的,1932年他在受騙中寫《我們不再受騙了》時,已年邁五十,是晚景了。這樣一個年齡差和年齡比,讓筆者不免為之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