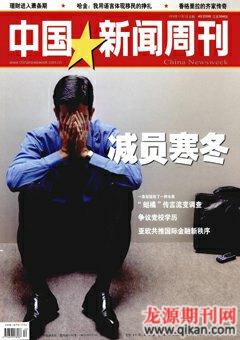審慎對待凱恩斯主義在就業問題上的作用
劉 彥
肇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在各國政府層面,正蔓延為一場凱恩斯主義回潮風暴。以美國政府7000億救市方案為首的貨幣拯救方案,被視為破除危機的法寶。雖然資本市場并不領情,但正如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二戰后美國和歐洲各國經濟復蘇中扮演的角色一樣,如今,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又當仁不讓地成為各國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問題的良策。
但是,無論新舊凱恩斯主義,必須考察其約束條件。凱恩斯主義面對的問題,是一國自由經濟市場本身的“失靈”,即承認自由市場經濟體除了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外,還存在著“非自愿失業”,原因乃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自由市場經濟經常出現小于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均衡。
從這個理論出發,凱恩斯為各國政府開出了解決本國就業問題的良方——以膨脹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拉動國內投資需求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均衡,從而最終實現充分就業目標。
然而,有關貨幣當局在出臺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同時,必須謹慎考察兩點:一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之核心,是否屬于一國自由市場經濟出現的“失靈”?二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是否可以繼續用增加政府投資來解決?如果不針對具體的經濟環境而繼續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很可能開錯了藥方,并無助于解決實際矛盾。
中國既有的經濟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于出口增長與投資增長。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升以及訂單減少的壓力之下,出口增長面臨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言的從“汗水經濟”到“智慧經濟”的轉型困難。這不是一國自由市場經濟內部所引發的供需矛盾,而是建立在價格干預和政府行政調控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模式,遇到了全球市場需求變化所致。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過去的出口經濟發展模式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通過維護城鄉之間的二元結構,為中國出口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另一方面,又通過產業政策和財稅政策(比如出口退稅政策、環境損失代價、匯率價格管制、資源型產品價格管制以及金融服務優惠等),為出口企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廉成本保護。由此可見,中國的出口經濟,并非僅僅由于自由市場選擇的資源配置結果,而且高度依賴于政府的調控之手。
在過去的30經濟增長中,出口拉動之外,政府投資扮演了不輸于出口的重要作用。這些大量投向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項目和重大投資項目(如鋼鐵、電解鋁等特大項目)的資金,在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條件的同時,也導致了房地產業節節升高、地方重復投資和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前一輪宏觀調控所要解決的問題。
可以說,既有的出口拉動與投資拉動模式,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又是造成今日經濟一系列內部結構性失衡的原因。在外部需求出現變化的前提下,如果繼續沿用凱恩斯主義式的調控方法,除了必然再次向出口企業回歸政策傾斜之外,在內需拉動不能快速見效的前提下,固定資產投資比例也必將進一步加大。
從就業目標上考察,出口拉動對于解決就業雖然表面上有利,但因其建立在低工資之上,對于每一勞動力的實際福利增加并無真正助益,這同時也是造成珠三角低廉勞動力缺乏的原因;而考察既有的固定資產投資效率和對就業率的貢獻,則不僅資金回報率極為低下(低下到只能是政府投資而不是私人投資為止),其對就業率的貢獻也反而較小。原因在于,政府投資的方向是GDP的增加而不是就業崗位的增加,鋼鐵等大型項目所需要的勞動力就業數目本質上是減少勞動力需求的。
因此,謀求經濟轉型的重點,不在加大凱恩斯主義式的調控,而在政府須從深刻干預經濟的宏觀調控定位中抽身,回歸服務型政府的本色。中國經濟急需一次從投資、出口拉動向高附加值的創新型出口和內需拉動的深刻轉型。
此種轉型,首先需要的是千千萬萬個微觀企業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和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此環境的根本,體現在政府能夠提供平等保護各私有產權主體的法律服務、公平透明的交易規則保護、無歧視性的金融產品服務和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等一系列內容上。
其次,轉型需要將現有擴張性財政的投資方向,從固定資產投資轉向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產品服務。只有增加每一社會成員的福利,才能最終增加其消費的能力與總體需求,從而培育內需拉動的動力。
如果不起步政府職能轉換而止步于揚湯止沸的凱恩斯主義財政貨幣政策,則不但克魯格曼的從“汗水經濟”到“智慧經濟”轉變難以完成,經濟也將面臨持續的“調控陷阱”:調控所要求的干預會越來越多并程度越來越深、范圍越來越廣,直至市場本身再也毫無彈性,最終回歸全能性政府與計劃經濟。這將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個后果。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經驗一再證明,無數微觀經濟主體對于束縛產權和交易的各項制度的突破功不可沒。政府從經濟微觀領域退出,不但會紓解既有的增長方式難題,而且當政府提供完善的服務、給予各創新主體以平等的經濟權利和主體地位之后,中國經濟會釋放出無限的潛能。到那時,中國制造們才會將創新智慧融入汗水,從而為中國制造在內外市場上重新贏得競爭能力;中國的每一內需主體,也將啟動更大更廣的需求,從而塑造真正良性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