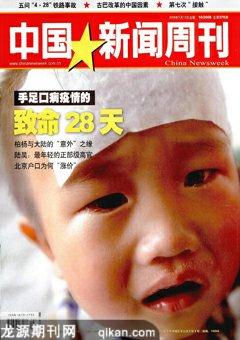古巴改革的中國因素
陳 君

雖然古巴一些改革措施與中國改革初期的思路近似,但兩國在國情、經濟狀況、所處國際環境等方面差別很大,這都決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國模式
2008年的春天,從兄長菲德爾·卡斯特羅手中接過“權杖”后,77歲的勞爾·卡斯特羅在古巴掀起一場變革——并非轟轟烈烈的革命,但卻改變著人們的生活。
開啟改革之路
2008年2月24日,勞爾·卡斯特羅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和部長會議的主席,正式接替因健康原因而移交權力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新政府將取消一些限制,著手改善人民生活,改變貨幣雙軌制,改變憑本定量供應生活用品的辦法……這一進程是逐步進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勞爾的就職演說點燃了古巴人的希望。
“勞爾很了解古巴老百姓關心的實際問題。”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徐世澄說。
上世紀60年代,徐世澄留學古巴,他印象中的盛產蔗糖的古巴曾是名副其實的“糖罐”。
然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美國趁機加大貿易禁運、經濟封鎖力度,古巴這盞“加勒比海上的社會主義明燈”黯然失色:國際市場蔗糖價格低迷,再加上遭遇旱災和颶風,古巴的支柱產業——制糖業產量不斷萎縮;俄羅斯停止援助,不再以優惠價供應石油,古巴不得不大幅削減石油進口,能源、交通受到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力低下,大量基礎食品需要從國外進口,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那幾年,古巴經濟被拋至谷底,物資匱乏,國民經濟呈負增長。
然而,“古巴沒有跟著拉美其他國家跑,也沒采取什么休克療法,而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足見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篤定。”徐世澄表示。
1991年,菲德爾開始推行“先對外、后對內”的改革措施:對外開放,優先發展創匯行業,如旅游業、醫生和教師勞務輸出等;有限度、有步驟地發展私營經濟,培植小規模市場……國家經濟慢慢走出衰退陰影,如今旅游業已成為古巴支柱產業,而與委內瑞拉共同實施的“石油換醫生和教師”計劃,則為哈瓦那廣開“油路”。
隨著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古巴國內要求改革提速的呼聲日益高漲。去年7月,“經濟改革實驗家”勞爾倡導全民大討論,政府最終收到120多萬條關于發展經濟的建議。勞爾決定順應民意,啟動經濟改革。
2008年2月19日,菲德爾發表《告古巴人民書》,正式宣布將“不尋求也不接受”再次擔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和革命武裝部隊總司令兩個職務。10天后,古巴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兩份菲德爾曾激烈反對的公約,“勞爾借此向國際社會釋放改革信號”,CNN如此評說。
古巴改革“師從”中國?
隨著眾多改革措施的展開,有西方媒體評論,古巴改革有很多地方具有“中國因素”,其中之一體現在交通上。
多西是一名百貨公司的職員,每天上班都要坐公交車。在他看來,改革的最大好處是告別了“駱駝巴士”。上世紀90年代初,為節約能源,古巴改裝了一些公交車,將鐵皮車廂焊接在一起做車身,用貨車車頭牽引,兩邊高、中間低,人稱“駱駝巴士”。“駱駝”能搭很多乘客,車費也很低。但車子破舊,行駛顛簸,噪音很大。
勞爾上臺后著力改善交通硬件。4月開始,“駱駝巴士”被嶄新的中國產公交車代替。未來5年中,古巴政府還將投入200萬美元用于改善公共交通。
“速度快,空間大,坐著舒服,公交車上還放著音樂,一路上多享受呀。”多西語氣輕快,“我們感謝中國的幫助,我們用的很多家電都是中國產的,中國和古巴從來都是一家人。”
“自家人”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深深地觸動了勞爾。1997年,他首次訪華,游歷多處,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和經驗;回國后還邀請訪華時陪同的中國官員到古巴訪問,為黨政軍干部作報告。2005年,他再次訪華,更加詳細考察中國的改革措施,在古巴設立專門部門,研究中國經驗。古巴一些經濟專家甚至建議“改革完全效法中國”。
不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世澄并不認為古巴在“照搬照抄中國經驗”。雖然古巴一些改革措施與中國改革初期的思路近似,但兩國在國情、經濟狀況、所處國際環境等方面差別很大,這都決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國模式。“古巴改革是在學習世界其他國家改革經驗后,從國情出發,走自我發展道路的大膽嘗試。改革順應民意,并沒有引發社會動蕩,體現了領導者的政治智慧,也符合國際社會的期望。”
徐世澄指出,勞爾新政,先易后難,是“循序漸進的、緩慢的”改革。古巴領導人認為可以利用“市場因素”發展經濟,而非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在醫療、教育等方面強調公平和平均、全民“共同富裕”,并沒有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
古巴改革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在于農業,其每年用于糧食進口的支出約為16億美元,“去年就花了13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全國有25萬個家庭農場,但50%的耕地閑置或荒廢。
為發展農業,早前在1993年,古巴就嘗試允許農戶自由經營,而這一次,政府走得更遠——有關土地用途和資源分配的決定,無需再請示國家農業部,地方和基層官員就可以決定,“大豆和大炮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勞爾對農業進行結構性調整,得到了哥哥的認同。
“地還是國家的,但允許農民和農業合作社承包、租種,農民能自由購買農具,家庭農場還能合法雇傭勞工,農產品也可以自由出售;種什么、什么時候種,自己說了算;為鼓勵生產,糧食、牛奶收購價也提高了一兩倍。”徐世澄介紹說,“種種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吸引跑到城里打工、不再務農的年輕人回來。”
受益于新政策的不僅是個體農民和私人小農場,大型農業合作社也陸續實現薪酬和產量掛鉤,按勞分配,調動起工人的勞動積極性。
“解放了人,解放了土地,一切都活躍了起來。大規模分配土地也是時候了。”古巴媒體為勞爾政府擂鼓助威。

在哈瓦那大學經濟學家圖安·堤亞納看來,農業是古巴經濟改革的試金石,“政府要在各個行業領域提高效率,如果農改成功,政府將在小型企業、個體戶和合作社領域推動新的改革。”
改革引發大變化
農業改革事關國脈。然而,熱鬧的都市似乎更能吸引西方媒體的目光。他們津津樂道于這個“神秘”“革命”“敵對”的國家哪怕一絲一毫的變化。
古巴《起義青年報》報道,4月22日起,美劇《黑道家族》《實習醫生格蕾》分別在古巴國營電視臺播出。西方媒體爭相轉載這一“大消息”。
“媒體太大驚小怪了,美劇、好萊塢電影、音樂,我們甚至比你們中國人看得還早、還多呢。”天津醫科大學一位古巴留學生說,“比如《越獄》,古巴的電視臺早就播了。”據說,今年上半年古巴將開播一個新頻道,24小時播放10多個國家的電視節目。
勞爾不會像年輕人一樣守在電視前看美國大片,他沒有時間。自2006年走到臺前,特別是兩個多月前正式掌權以來,他領導的新政府每隔數日就出臺一項新政,讓外界眼花繚亂——一夜之間,古巴人突然開始擁有更多選擇。
手機帶來的轟動效應最大。4月14日一早,在哈瓦那一家通訊業務營業廳前,來辦理開通手機業務的人排成長隊。“在古巴其他城市,興奮的搶購長龍也隨處可見。”古巴拉丁美洲通訊社記者費爾南德斯介紹道。這天,政府首次允許普通古巴人簽約登記手機服務。
“古巴從1991年起就開始提供手機服務了,但僅限于外國人、外企雇員和政府高官等人使用,不少人通過‘關系才弄到手機,手續很煩瑣。”費爾南德斯說,“如今,手機等電子產品對普通古巴人而言,仍是奢侈品。”
僅簽開通手機服務合同就要111可兌換比索(古巴外匯券,約合120美元),這只是激活手機業務的第一步。一款只有通話和短信功能的諾基亞手機售價75美元,帶攝像功能的售價280美元,這是美國地區同類商品售價的兩倍;而古巴本地通話費用則為每分鐘0.3美元。“還好,1/3的古巴人在美國等國家有親戚,僑匯收入占到古巴收入很大一部分,所以,人們對于如此昂貴的手機還是趨之若鶩。”費爾南德斯表示。
不僅手機,隨著經濟發展,電力供應的緊張狀況得到緩解,電子產品市場也逐步放開。
同時放開的還有酒店等服務行業。但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西方媒體卻在普遍質疑:“酒店開放了,但哈瓦那又有多少人能住得起呢?”
美聯社也不厭其煩地算了一筆賬:盡管人們的收入增加了,但古巴普通工人月薪也只有20美元,住一晚高級酒店需要一年工資,買一臺DVD需要5到6個月的工資,一臺電腦則要花兩三年的錢。
《時代》評論道,現實和理想的巨大反差讓勞爾改革蒙上陰影,西方輿論甚至奚落,改革是古巴的“面子工程”,DVD機和互聯網根本就不屬于“低水平下的平均主義”的古巴。但無可否認,古巴正在改變,而且引起全球矚目。
漸進式改革得到菲德爾·卡斯特羅認可和支持。“國父對古巴的影響會長期存在。這對古巴而言非常關鍵。”多西有感而發。
美國《時代》周刊曾這樣評價卡斯特羅兄弟:“哥哥是革命的靈魂,弟弟是革命的拳頭。”
更多的人同意哈瓦那外交學院教授多明戈·阿穆查斯特奇和斯坦福大學威廉·拉特利夫院士的預見,他們認為,古巴短期內的宏觀經濟發展將會得到中國和委內瑞拉的支持,而中期內的發展則將依仗其新興的石油工業的潛力。
接下來的問題是“勞爾能走多遠”,《紐約時報》問道。
分析人士認為,古巴改革正處在十字路口,能否深入進行取決于多種內外因素。就外因而言,古巴要進一步突破美國封鎖,進而與美國實現對話,改善外部環境;就內因而言,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打破平均主義……
在菲德爾注視下,勞爾要干的事太多了。古巴,這個以菲德爾大胡子和雪茄為標志的“革命加浪漫”的國度里,西方媒體眼中的“改革小步舞”注定將跳出更多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