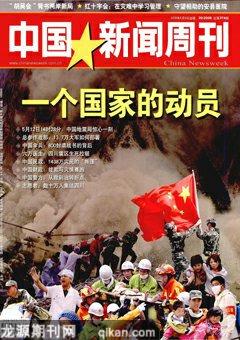雜種城市的魅力與意義
雷 頤
《城市九章》是本小書,不到十二萬字,卻異彩紛呈,令人頗有“目不暇接”之感。作者陳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就讀于香港大學和美國的波士頓大學,修社會學、政治學和傳播學,在香港創辦過《號外》雜志,還當過電影制片、編劇;曾在臺北呆過六年,現在長居北京,與京城“文化圈”“混得爛熟”。或許,只有如此“精彩”經歷者,才能把香港、臺北、北京、上海的本質、靈魂“參透”,才能在實不算多的文字中,對這幾座城市作如此精彩生動的比較、品評。
在兩岸三地的城市中,出人預料,他最喜歡的城市是“外表”實在寒酸的臺北。臺北的好處就在于它的“不建設”,才會讓人有自家寒舍“居家”的方便隨意,而無那在豪宅做客拘束。它最平易近人。它不是為政府、投資者和旅游者“興建”的,而是為在此地工作、生活的普通人“興建”的,他們才真正是城市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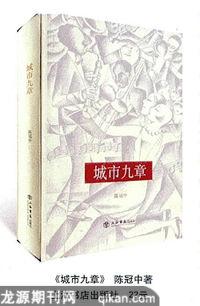
陳冠中筆下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英國紳士淑女的下午紅茶,在這里演化成香港本土符號的大排檔中的奶茶、茶餐廳和豉油西餐,港式電影從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萊塢,但香港電影最終還是自成風格,不是好萊塢。因為“你說我是半唐番,我承認,但是你別忘了我的汗和血”。
“汗和血”,是他的理論的重點。即“勞動價值和再生產,只有汗血論才能破各學說中的原教旨論和中心論”。在文化的傳播甚至“殖民文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勞作、創造的“汗和血”,本土與外來文化融合后的“變體”已不再是原來的幾種文化的機械結合,而成為一種渾然一體的“創造物”,通俗地說,就是“雜種”。雜種已不可能分出原來給予這個生命的每個個體。“還原就是毀滅,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論”就是要從那種自命為“偉大”的文化觀中解放出來,如各類文化原教旨主義、源頭優越主義、血統純粹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
在這種文化觀下,他不能不承認雖然“有一百個理由不該在北京生活”,但他還是想生活在北京。因為當代北京,提供了“混”的空間與可能。現在,來自全國各地世界各地的“文化混混”也越來越多,北京的文化元素自然更加全國化、國際化,更加色彩斑斕。“混”的人越來越多,北京已成為中國的波希米亞首都。有些人混得滋潤了,又時不時想過一過布爾喬亞生活方式。既要波希米亞又要布爾喬亞,于是“波布”(BOBO)在北京流行起來。兼收并蓄的北京文化,越來越“雜種化”,開始有些闊大恢宏的文化盛唐氣息了。
如果深入探求、思考城市的文化比較,必然會談到一個更基本、更重要、更廣闊、更嚴肅的問題:“世界主義成分稀薄的民族主義(或文明主義、本地主義)是危險的,上世紀的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本世紀主戰原教旨主義,都是例證。”“沒有世界主義成分的民族主義,將是戰爭與死亡的民族主義。這就是為什么,在到處都是民族主義論述的時候,我們也要多談世界主義。”這,便是本書最重要的目的與意義之所在。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