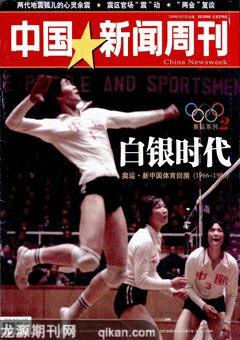兩代地震孤兒的心靈余震
孫 冉

從1976年至今,黨育新的成長經歷,正是一代唐山地震孤兒難以完成的苦痛修復。30多年后,她面對新一代地震孤兒——這一代孩子未來的路會怎么樣呢?
5月19日,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7天。
綿陽市中心醫院,太多的傷者,太多的哀痛者。生者不平靜,傷者不平靜,平靜只屬于角落里的一個孩子。
孩子瘦弱得像顆黃豆芽,四肢纖細,腦袋由于過大而耷拉在肩膀上。醫生說,是腦部積水造成的。
“黃豆芽”只有兩個月大,不哭不鬧,平靜得異常。她對7天前的那場災難是否有記憶,誰也不知道。她的目光透露著驚恐和對新環境的不安。
7天前,她被母親抱在懷里。房梁壓在母親身上,致命傷來自于頭部一道拇指長短的傷口。母親蜷縮著,為孩子留下足夠的空間——在母親蜷縮著的身體下,“黃豆芽”像種子一般奇跡地活了下來。
鄰居們在廢墟中聽見哭聲,把她從母親的懷里抱出來。孩子收住哭聲,自此平靜得異常。人們也許覺得她哭得太累了。
那一天,孩子的名字“母牽琦”有了新的含義——母親用生命牽出來的奇跡。護士們都說是個好名字,不過都不愿去面對奇跡的背后——母子生死兩端的現實。
沒人懂得“黃豆芽”那份異常的平靜,都認為是腦部積水的結果。
19日,從外面來了一個中年婦女。她抱著“黃豆芽”說,我知道孩子沒事,孩子什么都懂,孩子知道自己失去了母親。
這個中年婦女叫黨育新,唐山大地震中的一個遺孤。32年前,她只有6個月大。
32年的噩夢
32年前,唐山大地震,黨育新全家一共5口人遇難,惟有她,活了下來。
把她從廢墟中抱出來的解放軍說,在廢墟中,她不停地哭。父親最后一個動作,就是伸著胳膊,把她遞到廢墟的外面。
解放軍從她父親手里接過孩子,孩子不哭了。父親早已死去多時。
那一刻,人們給她起名叫黨育新——黨孕育的新生命。沒人說,她是父親用手送出來的奇跡。
5月19日,黨育新抱著“黃豆芽”,感覺抱著的正是32年前的自己。那時她是否也是這么一副黃豆芽的樣子,什么時候開始像個正常孩子哭鬧的,這些黨育新都不記得。唯一的記憶是她兩歲后的一張照片。那上面,黨育新胖乎乎的,和兩個姐妹站在一起。她們三個都姓黨,人們都稱“黨氏三姐妹”。
搜救到她的解放軍,后來給黨育新說,當時她很健康,胖乎乎的,一點傷都沒有。她父親也很好,致命的傷口很小,看上去走得很安詳。
這些話,黨育新從來都不相信。5月17日,她在電視上看到“黃豆芽”被解救的鏡頭,就覺得電視里那個孩子就是她自己。
32年前,黨育新和500個唐山孤兒被送到石家莊一所福利院(育紅學校)。她是那些孩子里最小的一個。那一次大地震,造成4000多個遺孤,其中1000多個和黨育新一樣生活在福利院里。
在福利院里,孩子們過著半軍事化的生活——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定時睡覺、起床,一起玩耍,形影不離。有時這是一種快樂,有時這也是一種集體化的孤獨。

黨育新記得,那時福利院的孩子特希望過年,因為只有過年才有人去慰問他們。
32年來,黨育新時刻都在幻想著有個父母,但這僅停留在幻想。“我從小就沒有父母的概念,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我們孤兒就是這樣。有人說我們孤兒沒有教養就是這樣。”黨育新現在有時覺得自己很自私,覺得自己以前被虧欠的太多了,“工作后,我想買什么,不論多貴我都買給自己,變相地回報自己”。
黨育新的夢想后來差點成為現實。有一對奧地利的夫婦來收養唐山遺孤,“黨氏三姐妹”同時入選。福利院的阿姨說,誰乖,誰就有家。黨育新覺得自己最乖,肯定討人喜歡。最終,老大黨育紅被選去,因為她沒有任何親戚。
黨育新不能去,是因為她終于找到了親人,她還有個姥姥活著。
她至今對當時的姐姐黨育紅有種奇怪的感覺,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嫉妒。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育紅去了奧地利,如今連中文都不會說,也忘了她們,不想回來。
她還說,福利院里,阿姨和藹得永遠像別人家的阿姨,從來沒人對她們這些孤兒嘮叨過。后來長大了,她很羨慕人家有父母的嘮叨。自己沒這個嘮叨,心里總是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何處會碰壁。
9歲那年,她被送到姥姥家。她說,她和姥姥有親情,生活卻沒保障。姥姥沒有工作,生活很苦,需要舅母給生活費,每月20,還要“看人臉色”,有寄人籬下的感覺。孤兒院雖然苦,但畢竟不用為生計發愁。黨育新很想回福利院。
她給福利院的阿姨寫信,希望他們來接她。她不知道石家莊的孤兒院(育紅學校)1984年已經解散。等了許久,也沒有阿姨來接,她第一次真實地感覺到被那個集體“遺棄”了。
從小沒人告訴她長大會怎么樣。來例假了,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也不喜歡和姥姥說話,姥姥從來沒有告訴她爸爸媽媽的事,連一張照片都沒有。
2004年姥姥去世,黨育新開始覺得姥姥不容易——因為死了女兒,自己再苦也要把外孫女拉扯大。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黨育新就跟著唐山心理干預援助團來到綿陽。她知道自己心理也有點問題,但內心里想到汶川來看一看32年前廢墟中的唐山和她自己。
她在醫院抱起“黃豆芽”那一刻,終于明白做一個母親的不容易。
兩代遺孤的歸處
到了綿陽,黨育新和她的唐山心理干預援助團,最想去福利院看一看。
5月21日,聽說梓潼兒童福利院安置了一些地震孤兒,黨育新和她的唐山心理干預援助團,馬上包車來到這個離綿陽有近一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這是一個7人的隊伍——只有兩人不是專業心理咨詢師,一個是擔任領隊的中國共青團唐山市委書記,另一個就是地震孤兒黨育新。
經過反復協商,黨育新和同事們終于獲準進入戒備森嚴的梓潼兒童福利院。院大門上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此處只有安縣孩子,無北川孩子,意欲領養者請三個月以后再來”。可見此處并不乏來訪者。
這是一棟兩層小樓,樓上是孩子們的宿舍。孩子們都聚集在一樓的院子里,好奇地看著這些來客。
黨育新一眼掃過去,心里不禁悲涼。近30個孩子里,一眼就能看出好幾個孩子是殘疾兒:白化病、智障、毀容。一個5歲的小男孩靠近打量黨育新。黨和他說話,他不應。老師走過來說,“他有嚴重的癲癇”。
只有幾個小男孩比較活躍,他們對來客手中的相機發生興趣。當來客舉起相機準備拍他們時,他們立刻擺出姿勢,露出微笑。
這幾個小男孩就是此次大地震的臨時孤兒,他們是安縣小壩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自地震后,這個學校的一部分學生來到了這里。
如今剩下5個孩子,無人認領。老師說,他們成為孤兒的可能性很大。
黨育新搬了個小板凳,坐在一個叫張顯林的小男孩身邊。他今年9歲,大地震時正在學校睡午覺。他還有個弟弟叫李鋼,是雙胞胎,兩人一個班。當時,弟弟在教室里玩,他叫弟弟趕快跑。所幸兩人都平安跑出。
“你和你弟弟怎么是兩個姓?”黨育新不解。
張顯林不語。他低頭玩著手中的鋼絲,一根牙簽粗的鋼絲被他硬生生折彎。他的手心被磨得通紅。
“你在班上學習好不好?”黨育新問。
“我期中考了95分。”張顯林笑了笑。
“我兒子和你一樣大,他可沒你學習好。”黨育新笑著說。
這時,一個與張顯林長得很像的小男孩也搬凳子坐了過來。他解答了黨育新的疑問。“我哥被我爸‘賣給張家了,不過哥哥經常回家玩。”小男孩叫李鋼,張顯林是他親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