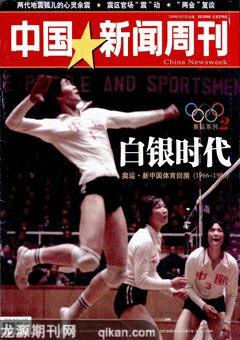卸下“新媒體”藝術的外衣
楊時旸

這個正在中國美術館進行的展覽,有別于以往在中國的美術館中的任何一次
6月9日開始,中國美術館一改以往的凝重色彩,在眾多帶著“高科技”味道藝術作品的包圍下,一個名為“合成時代”的新媒體藝術展正在把這里變成一個充滿趣味的游樂場。
美術館的正門口,一個拱型的跨梁上安插著無數發聲器,人們穿過的時候,劈啪的電流聲在頭頂炸響。從這里開始,這些被稱為“新媒體藝術”的作品正在把你引向藝術與科技糾纏的迷宮。
這次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中,根植于網絡虛擬空間的作品成為主體之一。來自奧地利一個命名為《因緣》的作品用三維成像的方式制造了一個藍色的虛擬空間,這是一個模擬的生命環境,三維的人形漂浮其中模仿著真實的動作,附加的聲音軟件制造出各種動態的聲音,表達感情的變化。
這是當下西方新媒體藝術典型的呈現方式——用科技手段制造出一個載體,并植入藝術家的觀念。
每個時代有自己的“新媒體”
“新媒體”藝術,這個概念有著引人入勝的名字和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內容。和其他藝術概念一樣,“新媒體”藝術也是一個被評論家事后總結出的說法。
早在上世紀20年代,無線電的大規模使用讓一些敏銳的德國藝術家意識到,這種可以向群體發送信息的媒介似乎可以成為自己創作的工具,這原本帶有實用主義色彩的介質成為了早期的“新媒體”。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媒體藝術是一個歷史時間概念,在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新媒體藝術,這個概念(定義的藝術產品)不是固定的。這次新媒體藝術展的策展人張尕總結說——利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新媒介創作出的藝術作品都可被稱為“新媒體藝術”。
科技上不斷的創新相繼被藝術家挪用采納,逐漸成為各自表達藝術觀念的手段。從早期的并不成熟的電子藝術,到70年代電視媒體藝術大師白南準,再到90年代的網絡藝術運動,“新媒體”藝術伴隨科技的發展擴延自己的表現形式。利用衛星同步傳輸不同地點藝術家本人的行為,利用網絡的虛擬空間表達對于人類自身困境的思考,再到與生物技術結合探究生命極限……“新媒體”藝術一直游走在藝術與科技之間。
當時的“新媒體”藝術家在某種程度上,有向主流藝術挑戰的心態。他們希望利用新的語言和手段建立一套與博物館藝術平行的體系。在這樣的心態下,90年代中后期,“新媒體”終于以“藝術運動”的形式大規模亮相,也無意中成就了20世紀最后一場大規模的藝術運動。當時在紐約讀書的張尕也參與其中。
“那時候在紐約有一個點,俄國有一個,德國、瑞士也分別有一些藝術家在做新媒體藝術。”張尕說。這個“新媒體”藝術運動自發產生,同一時間段,在西方四五個國家的城市,一些藝術家各自利用當時新興的媒介表達其藝術觀念。這場藝術運動統一地以利用新技術作為媒介,產生了一條獨立于藝術/美術館之外的表達系統。
那時候,這些自封為“新媒體”藝術家的人們,每周末在一起聚會喝酒,互相了解各自的新作品。那時的作品與現在多樣的新媒體藝術相比,顯得并不成熟,有人利用錄像制作實驗性的影像片段,有人利用剛剛興起的互聯網制作可以互動的頁面……更多的是利用電腦技術制作的一些可以互動的flash,或者根植于緩慢的互聯網速度做一些體驗性作品。“當時網速很慢,我們以藝術家的角度體驗和解讀那種慢,就是緩沖的感覺。”張尕說。
當時的“新媒體”藝術家為了實現其藝術觀念,自己學習編程、flash等電腦技術,常身兼藝術家、評論家、策展人數個身份。
1996年,包括張尕在內的一些“新媒體”藝術家成立一個叫做Net.time的網站,作為一個圈內交互信息的平臺,在互聯網尚不發達的時代,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網站也成為了一個作品。
2001年,舊金山MOMA藝術館策劃了一場名為010101的新媒體藝術展,徹底將新媒體藝術拉進了高雅藝術的殿堂。
在這之前,主流藝術圈對所謂的“新媒體”藝術家已有所注意,態度卻不以為然。但MOMA藝術館作為權威的當代藝術機構,在這里舉行的這次“新媒體”藝術展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形式從在野到主流的標志。
這次展覽之后,眾多藝術館和研究機構開始重新審視“新媒體”藝術。大批機構紛紛向“新媒體”藝術開放。最著名的包括奧地利的AEC藝術館,德國的ZKM藝術館如今都成為“新媒體”藝術的重要基地。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也看到了藝術家們創造力背后的商業可能性,許多高科技公司還設立了文化基金,為這些藝術家提供更多與科技前沿跨界對話的方便。
高科技成就“新媒體”藝術
而被“招安”之后的“新媒體”藝術也喪失了挑戰權威色彩,同時卻開始了更為成熟的創作。
“新媒體藝術當中所用到科技手段和科學不一樣,科技開發的目的是為了實用性,而藝術家采用這些科技手段是為了傳達個人的觀點,是無用性的。”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說。
從上世紀20年代的無線電藝術到如今的網絡藝術和生物藝術,這些藝術家并不只是以搞怪的方式去打破藝術傳統,更多的是對于已存在多年的藝術語言的質疑。“有的藝術家天生信賴使用的藝術形式,有人就會質疑,所以他們會不斷尋找新的載體。”張培力說。
“新媒體”藝術是一種對于原有的藝術邊界的一種拓展,這種拓展其實在杜尚多年前那個著名的小便池(1917年,法國藝術家杜尚將一個從商店買來的男用小便池起名為《泉》,簽上自己的名字送到美國“獨立藝術家展覽”上。“小便池”卻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的藝術品之一)就宣告了藝術邊界的模糊,如今的“新媒體”藝術家把原本屬于科學領域的生物技術、衛星、網絡轉化為創作的載體,再一次把藝術的邊界徹底摧毀。而藝術家所選擇的外在載體又進一步為觀念注入新的活力。
例如在這次展覽中,來自波蘭的作品《生命維持》,藝術家將幾株蘭花放置于美術館,并用計算機將蘭花的生長方式轉化為數碼輸入電腦,在虛擬空間中,蘭花可以自由生長,變成了一個虛擬的有機體,蘭花的虛擬形態以數碼狀態永遠存活生長下去。藝術家用最新的神經網絡人工智能技術探討了“永恒”的可能性。
這樣的生物藝術已經屬于當下新媒體藝術的前沿,但對于藝術家來說,這并非終止之地。伴隨科技的發展,藝術家會再發現更多可以被挪用的載體,并用于自己藝術的更新。
中國的“新媒體”藝術
早在1988年,藝術家張培力就創作出了國內第一個新媒體作品《30×30》。他在長達3個小時的錄像中,把一面鏡子摔碎,粘合,再次摔碎,不斷重復。機位沒有任何變化,沒有布光,沒有剪輯。那個年代,電視剛在中國普及,張培力看到人們在這種新媒介中忘記時間,就想用同樣的媒介讓人們想起時間的存在。他確實達到了目的,當這個作品在圈內被播放的時候,所有人都表現得極不耐煩。而10年之后,更多的國內藝術家才開始進行錄像藝術的新媒體創作,張培力因此被批評家稱為“中國錄像藝術之父”。
如今,西方的新媒體藝術已經囊括了從互聯網到生物技術等頗為交雜的范疇,中國雖然也有藝術家在嘗試,但到現在,中國藝術家更為廣泛的形式仍是錄像藝術。“我覺得沒有必要為了新媒體而新媒體,媒介不是目的,我們做這些是為了能用新的媒介拓展自己的語言,目的是為了表達背后的觀念。”張培力說。
但包括張培力,汪建偉等在內的中國新媒體藝術家們雖然逐漸積累著各自的國際聲譽,與傳統架上繪畫藝術家相比仍然缺乏普遍的關注。
現在,張培力主持著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系,他的很多學生都在進行著新媒體創作。在他看來,雖然因為資金和技術原因有些學生的作品不像西方同時代作品那樣具有成品感,但是“意識上已經沒有太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