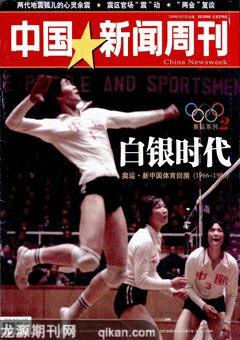改革要勇于面對“敏感問題”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三十年,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按照民主、法治、市場等改革的既定目標來衡量,改革進程依然沒有完成,仍有很多重要領域需要進行改革。推進這些改革,需要正確地處理所謂的“敏感問題”。每一次在制定某些方面改革方案的時候,總會有些人士會以涉及“敏感問題”而形成阻力。中共中央黨校李英田先生近日發表文章提出一個命題:敢不敢觸及“敏感問題”檢驗思想解放的真假。
確實,回顧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就可以發現,每一場有助于建立市場制度、推動社會向民主、法治方向演進的改革,最初都曾被列為“敏感問題”,而成為改革的禁區,甚至成為理論界和公眾公開討論的禁區。
這種情形與中國改革的環境有關。所謂“敏感問題”,通常是指某一問題在政治上、尤其是意識形態上比較敏感。在中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具體規則、制度,通常都具有意識形態上的依據。因而,隨便一項具體改革措施,都會與意識形態產生直接間接的關系。比如,是否允許城市個體工商戶存在,涉及經濟的公有還是私有問題;是否允許農民土地承包,涉及農村集體經營制度的存廢問題。
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在中國,大規模的改革通常以思想解放為先導,至少同時伴隨著思想解放。所謂思想解放,就是對固有的意識形態進行修正,容納那些即將的改革措施所隱含的價值。通過這一程序,敏感問題會被“脫敏”,變得不那么敏感,人們于是可以在這一領域進行改革。
應當說,過去三十年來發生的多輪思想解放及相應的改革,已經使大量“敏感問題”脫敏:首先,私人生活領域的眾多問題,基本上不再作為敏感問題進入政府視野了。至于公共問題,到80年代中后期,私人企業就不再是敏感問題了;經過鄧小平的南巡,市場經濟不再是敏感問題了;經過2004年修憲,私人財產權不再是敏感問題了;同時,執政黨確認了建立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目標,這兩者也不再是敏感問題了;據此,擴大公民的自由權利、其中包括參政議政的權利,就不再是敏感問題了。當然,村民自治制度、與社區業主自治制度的建立,也意味著此一范圍自治不再是敏感問題了。
不過,在所有這些公共領域的問題,最多只是抽象地不敏感了,它們作為目標已經不敏感了;但是,涉及到具體的制度的改革與行政過程,在一些部門那里,仍然有一定的敏感性。
今天,有些人之所以仍然熱衷于把有些問題列為“敏感問題”,拒絕向民眾提供相關信息,或者拒絕推進相關改革,當然仍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從這個角度看,深化改革確實需要進行新一輪思想解放,完整地確立市場、民主、法治、民生等價值的政治與觀念地位,進一步在意識形態上為人們為解決現實問題所進行的創新脫敏,為這些領域的進一步改革開辟更大空間。應當說,當下進行思想解放,具有前所未有的優勢,因為,市場已經基本上成為現實,民主、法治的理念已經成為常識,也不會有多少人質疑民生政策的必要性。
不過,今天之所以仍有若干“敏感問題”,主要是由于某些政府部門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人為劃定。將其劃為敏感問題,就可以維持對自己有利的現狀,躲避民眾的監督,甚至可以擴張自己的權力與尋租空間。因此,深化改革,光靠解放思想是不夠的,還需要打破已經形成的某些特殊利益格局,使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無法挾持公共利益。
中國改革的過程就是縮小“敏感問題”范圍的過程。改革的目標之一,則是要把“敏感問題”這個詞從公共領域中清除出去。面對公共利益、公眾利益,沒有什么東西是“敏感”的。因為,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公眾利益,本來就是制訂各項法律、政策、制度的唯一目的。即便是有些所謂“機密”,公眾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申請信息公開。只要是公共問題,就是公眾、媒體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依照公眾的意見,為了公共利益,按照法定程序,任何具體的規則、制度也都可以成為變革的對象。
可見,在公共領域中縮小乃至清除“敏感問題”的前提是,切實地確保權力的公共性。即,從法律上、從理念上,執政黨、立法機構、行政部門等等掌握權力的機構都把公共利益、公眾利益當作最高的、最敏感的目標對待。由此,法律、政策就可以根據“以人為本”的理念調整,而不會以敏感為借口成為特權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