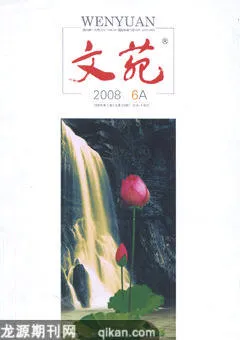紅袖添香,綠袖添飯
涼月滿天
草的世界花為貴,花的世界草值錢。女人花配男人草,世界很美好。
數不清多少根草從我的世界里穿梭而過,他們個個都曾是我的“男色”。最早時候有成龍、周潤發,和演《花樣年華》和《重慶森林》的梁朝偉,然后又迷上在《黑冰》里扮演大毒梟的王志文。人到中年,生存艱難,娛個樂都沒時間,如是不追星約有兩年。這可真是“葉落梧桐秋氣深,西風瀟灑到園林,吹落男色片片金”。
今天才又迷上在《士兵突擊》里扮演史今班長的張譯。我老人家又把他變成我的又一個“男色”,通紅嶄新!十分市儈地講,他未出名之前,就算是真的找到我頭上,我還真不希待搭理他,現在他出了名了,我想搭理也搭理不上——所謂的孤獨就是人人看得見,人人進不去,否則還叫什么孤獨哉。這就是追星的結果:星星都是孤獨的,你老看它在眼前晃,卻永遠不可能把自己空投到它上面。
其實種種男色,每個女人的心里都裝著一車,還帶不定時換崗的。古時有潘安出游,被色女們擲果盈車,近代有汪精衛,在廣州演講被女學生擲花如雨,估計此時張譯若是出來,也會給流著哈喇子的女粉絲們用花活埋。
《荊棘鳥》里有個萬惡的老女人,莊園主,仗著自己有倆臭錢,就死不要臉地愛上英俊的拉爾夫神父,拼命和自己的親侄女搶愛人,還伸過臉來強迫人家親,拉爾夫一躲,她想死的心都有了。她一定沒讀過佛。佛理說戒色,可沒說男色女色。偶像時代的男人一旦淪為偶像,也就成了男色,那是一定要戒的,不然就像某女狂追劉德華,死定了。
問題是,怎么個戒法?
最有智慧的人,可以仿效《閱微草堂筆記》里的狠招:一書生眷戀已死孌童,惘惘成心疾,兩僧人解其心結,讓他一想此童歿后,臭穢腐潰,血肉狼藉,惡心;再想此童如仍活著,越長越大,不再婉孌美好如少女,卻漸壯漸偉,修髯如戟,可厭;三想我若先此童而死,這家伙必定歸了別人,拿侍奉我的一套去侍奉別人,可氣;四想此小童若是還活著,我沒錢養不起他的時候,他必定生出異心,見我如同陌路,可恨。既然如此,饒他芙蓉如面,仍須入土為安。
可是,拿這個來對付我的后宮三千,是不是太狠了點?
生為“色女”,非僧非尼,生活不易,為什么就不能拿“色男”來犒勞一下自己?再色也不過看看照片,讀讀文章,了解了解彼人的生活經歷,如此而已。張某人早已聲明他只是一個演員,且大聲疾呼:“千萬不要被演員扮演的角色迷惑,演員只是演員,絕不是生活。大家都喜歡茜茜公主的扮演者羅密·施耐德,而現實中,她官司纏身,生活被弄得一塌糊涂,毫無生活處理能力,最后自殺了。
好在煙花爆開,只是瞬時亮眼,一個個男色被我請進來,送出去,拖進來,踢出去,估計這個更維持不了很長時間。在“色”的上面,女人和男人一個德性,薄涼、懶惰、花心,鐵打的營盤流水的色男。
這個世界上總有些如我之類的小人,一邊在心里養色男,一邊還裝得道貌岸然,更有一些披著披風的女蟑螂,拿錢硬砸帥哥上床,所以我不替自己擔心,倒替他們擔心。我把他們當男色不要緊,他們不要把自己當男色就行。男而不色,是他們自己做人的底線,要不然亂紅飛過秋千去,一地雞毛卻算誰的?
不過所有一切,與我無干。生在天地間,心有俗念,兜無余錢,也擋不住自己做夢玩,男人能夢紅袖添香,憑什么不讓我夢綠袖添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