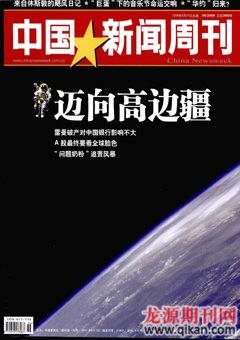中國太空“第一步”
蔡如鵬
相對于之前的“神六”,“神七”將實現太空行走,最大的挑戰是提供可靠的艙外航天服和氣閘艙

9月20日,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神舟七號飛船端坐在70米高的長征二號F運載火箭上,沿著一條1500米長的無縫鐵軌,經過1小時零5分的垂直移動,順利轉運至發射架下,等待最后的發射。
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早前宣布,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將于9月25日至30日擇機實施,屆時,將有3名航天員組成飛行乘組。其中一人將走出飛船,成為中國太空行走第一人。
一位知情的航天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要進行出艙活動,神舟七號的技術難度和風險性要比此前的飛行大很多,無論是技術攻關、產品研制、航天員訓練,還是任務組織指揮,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統顧問組組長黃春平透露,發射首選時間定于9月25日晚9點10分。太空行走預計在26日或27日的下午或晚上進行,隨后飛船將于28日返回地面。
沒有路的行走
航天員將在神舟七號附近進行40分鐘的太空行走,“一手拉著艙外的扶手,一手進行操作”
《國際太空》雜志副主編龐之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太空雖然浩瀚美麗,但不具備人類生存所必需的條件,到處潛伏著致命的危險。這些危險包括高真空、缺氧、極度的溫差變化、可怕的宇宙輻射和隨時光顧的微流星以及空間垃圾。
1971年6月30日,前蘇聯“聯盟”11號飛船返回地球時,返回艙一個與外界連通的壓力閥門被震開,空氣迅速漏光。艙內三名航天員暴露在真空中,急性缺氧,液體沸騰(液體的沸點隨著氣壓的降低而下降,真空可導致液體迅速沸騰、汽化),在幾十秒內停止了呼吸。
為了確保首次太空行走的成功,中國不僅做了精心準備,而且將發射時間推遲了將近一年。
2005年神舟六號成功完成載人飛行返回,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唐賢明曾對外界宣布,“2007年我們要實現航天員出艙,在太空行走”。

此后不久,當時的國防科工委(現國防科工局)主任張云川在向決策層匯報進展時表示,從技術方面考慮,2007年11月就可具備發射飛行的條件。但國務院高層批示,“不搶時間,各方面的工作要做細做好”。發射時間因此推遲至次年三四月間。
“到了2008年4月,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包括環境因素,再次推遲半年。”一位知情人說。
盡管做了周密的準備,但并不意味著到時的太空行走會變得輕松。
太空中沒有路。龐之浩說,航天員移動身體更多的是靠手,而不是腳。因此,把出艙活動稱為“太空行走”或“太空漫步”并不準確。
在太空中活動也不像看上去那樣輕松自如。有一次,美國航天員戈登,打算走出“雙子星座”飛船,將一根繩索系在飛船頂端。由于沒有手腳固定裝置,戈登半天也沒完成任務。最后,他不得不“騎”在飛船上,用腿來固定身體,被艙內的指令長戲稱為“騎飛船的牛仔”。
戈登后來回憶說:“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操作,我在地面進行過多次訓練,最多30秒就能完成,但在太空行走中竟然花了30分鐘。我知道太空作業比地面要困難得多,但沒想到會如此困難。”
“這是因為在太空行走沒有著力點,體力消耗很大,而且沒有任何辦法減少這種體力消耗。”龐之浩說。
據悉,航天員將在神舟七號附近進行40分鐘的太空行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飛船系統原總設計師戚發軔說,出艙后,航天員將“一手拉著艙外的扶手,一手進行操作”,取回事先放在艙外的科學實驗裝置。屆時,飛船還將釋放一顆小衛星,同步傳回航天員在艙外活動的畫面。
一套衣服一艘船
“艙外航天服是最難的一個,它的研制進度決定了發射時間”
美國人在登月之前,曾搞了一個雙子星座計劃積累經驗。這項計劃前后共進行了5次太空行走,為阿波羅航天員最終在月球上行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確保太空行走的安全,最好的手段是提供可靠的艙外航天服”。
龐之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艙外航天服就像一艘五臟俱全、功能完備的“柔性小飛船”,不僅可以把航天員與太空的惡劣環境隔開,防止強輻射、微流星和空間碎片對航天員的傷害,還能提供一個確保航天員生命安全的生存環境。

艙外航天服的氣壓調節是關鍵,不能出現一絲漏氣,否則將危及航天員的生命。龐之浩,即使俄美在實現太空行走40多年后的今天,他們的艙外航天服仍時常出現問題。
美國航天員塞爾南一次執行太空行走任務,用力過猛,導致艙外航天服的背部外層破裂,他的后背很快就被強烈的太陽光灼傷。最后,塞爾南不得不在另一名航天員的幫助下才得以返回艙內。
2007年,美國“奮進”號航天飛機的兩名航天員在艙外作業,其中一人發現自己左手手套出現一個小洞。雖然沒有穿透到里層,但地面人員還是要求他返回密閉艙。這名航天員不得不提前兩小時結束他的太空行走。
一位航天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神舟七號需要攻克的難關中,“艙外航天服是最難的一個,它的研制進度決定了發射時間”。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新聞發言人近日對媒體說,中國自主研制的艙外航天服,已經過專家嚴格評審,各項技術指標完全滿足神舟七號飛行任務需要。這位發言人還透露,艙外航天服每套總重量約120公斤,造價3000萬元人民幣左右。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盡管中國自主研制的艙外航天服已通過評審,但為了航天員的安全,仍向俄羅斯購買了一套艙外航天服。最終選哪套出艙,還要根據最后性能對比的結果決定。如不出意外,神舟七號航天員將穿著“中國制造”的航天服出艙,完成具有歷史意義的太空行走。
根據航天員出艙時是否系帶,太空行走可分為“臍帶”式和“自主”式兩種。
“臍帶”式行走是用一條系帶把航天員與航天器像嬰兒與母體一樣連接起來,航天員在艙外活動時所需的氧氣、壓力、電源和通訊等生命保障系統都由這條“臍帶”提供。
這種方式簡單、安全,技術容易實現,但缺點是受“臍帶”長度的限制,航天員只能在航天器附近活動,太遠容易出現“臍帶”纏繞,使航天員像嬰兒一樣窒息死亡。
蘇聯在太空行走第一人列昂諾夫出艙以后,美國從“阿波羅”飛行開始,航天員在太空行走時都不再使用“臍帶”式,而采用“自主”式,即航天員在太空行走時使用一種外形像一個大背包的便攜式生命保障系統。
1984年,美國航天員布魯斯?麥克坎德利斯二世背著噴氣式發動機,完全脫離“挑戰者”號航天飛機進入太空。
麥克坎德利斯二世背上的噴氣式發動機看上去更像是一把椅子,也有人稱它為“太空摩托”。它屬于載人機動裝置,能夠為航天員移動提供動力,并可控制移動的方向和速度。
“自主”式行擴大了航天員的活動半徑,使他們可以到遠離航天器100米的空間活動。但這也增加了危險,一旦發生事故,航天員可能就再也回不來。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神舟七號航天員將采用“自主”式太空行走,不需要“臍帶”為航天員提供保障。但為了安全,仍會在航天員與飛船之間系一根安全繩。
穿越生死之門
開關艙門這項看似簡單的活動步驟卻多達幾十項
航天員進行太空行走時,最麻煩的事要算進出氣閘艙了。一般沒有兩三個小時,根本沒法通過,即便只是出去幾分鐘。那么,氣閘艙有什么用呢?
氣閘艙又叫氣壓過渡艙,它像一道位于飛船與太空之間的閘門,既可阻斷兩邊氣體的自由流通,又可讓航天員進出。
航天員出艙時必須要打開艙門,如果艙門直接面對太空,兩邊巨大的壓力差,不僅會使艙內的空氣立刻泄漏掉,而且還會讓航天員像炮彈一樣沖出去,非常危險。
龐之浩說,目前經常執行太空行走任務的國際空間站和航天飛機,均設置有專用的氣閘艙。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神舟七號的氣閘艙并不是專門添加的,而由此前的軌道艙改造而成,改造后的軌道艙有兩扇艙門,內側的與返回艙相連,外側的通向太空。
神舟七號航天員出艙時,兩名航天員首先由返回艙進入氣閘艙,然后關閉氣閘艙內側的艙門,接著在氣閘艙內穿好艙外航天服;給氣閘艙逐步泄壓,并吸氧排氮;直至真空狀態——與太空中一致;最后,再打開氣閘外側的艙門,一名航天員出艙,進行太空行走,另一名航天員則留在氣閘艙內協助。
返回時,則正好相反。整個過程如同船舶通過江河上的水閘。
氣閘艙的另一個作用是航天員在出艙前,要坐在這里吸一兩個小時的純氧。這主要是為了預防減壓病。
艙外航天服盡管可以提供適當的大氣壓力,保障航天員的生命和工作需要,但如果壓力過大,會使航天服僵硬,穿上后行動不便。因此,艙外航天服內的壓力要比身體承受的正常壓力低很多。
壓力降低后,原來溶于人體組織和體液中的氮氣就會析出,形成氣泡(氣體在液體中的溶解度隨著壓力的降低而減少)。這些氣泡如果出現在皮膚,會像螞蟻爬一樣,瘙癢難忍;如在關節及其周圍組織,會引起關節疼痛;如在肺小動脈或肺毛細血管,會引起咳嗽、呼吸困難;如在神經系統或血管內,則會導致死亡。這就是減壓病。
因此,航天員在進行出艙活動時,必須吸足一兩個小時的純氧,把體內氮氣的含量降到最低。
在太空飛行中,飛船的艙門被稱為“生死之門”。如果關閉不牢,就有可能導致船毀人亡,歷史上曾有過教訓。因此,開關艙門對于神舟七號而言也是一個生死考驗。
搭載神舟六號的航天員費俊龍曾介紹說,開關艙門這項看似簡單的活動步驟卻多達幾十項。據了解,神舟七號的艙門已做過數百次試驗,3名航天員也進行了訓練,都可獨立完成開關艙門的操作。
事實上,在進行太空行走的過程中,操作的步驟和程序極其重要。“神七”上的艙門密閉快速自動檢測裝置,也能隨時監控艙門密閉狀況。
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步”入太空
中國發射神舟七號進行太空行走的最終目的,正是為建造自己的永久性空間站做準備
自從40多年前列昂諾夫走出飛船的那一刻起,人類迄今已進行100多次太空行走。
作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第二階段的首次飛行,神舟七號此次升空的主要任務有三項:航天員出艙活動(即太空行走)、進行空間材料科學實驗和釋放伴飛小衛星。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分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將航天員送入太空并安全返回;第二階段完成出艙活動、空間交會對接試驗,發射空間實驗室;第三階段建造永久性空間站。
我們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步入太空呢?
事實上,在載人航天初期,人類自身對這個問題也不甚清楚。最大的初衷或許只是為了證明人類能夠在宇宙真空中生存和工作。
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蘇聯“禮炮號”“和平號”空間站的建成和美國航天飛機的使用。太空行走開始用于空間維修、布設衛星和進行空間試驗。
尤其是搭載航天飛機的航天員,經常執行“放”衛星和“抓”衛星的任務。他們將有問題的衛星帶回來,維修后再送回去。比如耗資25億美元的“哈勃”望遠鏡,自1990年送入太空,一直故障不斷,多虧了航天員出艙維修,才得以工作至今。
自從國際空間站計劃實施后,太空行走又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組裝、對接這個龐大的空中城堡。今天,各國已經認識到,離開太空行走,空間站就無從建起。此次,中國發射神舟七號進行太空行走的最終目的,也正是為建造自己的永久性空間站做準備。
也有人批評說,完全可以讓成本低廉又干得不錯的機器人替代人類進行太空行走,為什么一定要提心吊膽地讓人去冒險呢?
載人航天飛行的支持者爭辯道,只有人類才具有柔韌的身體協調能力和靈活的頭腦,能搞從太空行走中獲得最大的收獲。
最有說服力的論據,可能仍然是最初的動因——太空探索,歸根結底是人類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