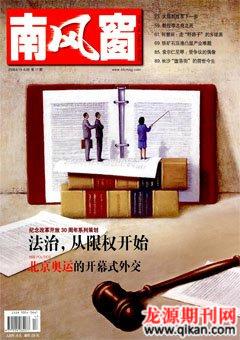給警察權帶上“拳擊套”
陳統奎
公安機關不是一般的行政機構。對公安機關進行適當的分權,可以從體制上給高風險的警察權減負。
白手套、頭盔、警棍,這是如今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門衛的新裝備。此前的7月1日,28歲的北京青年楊佳闖進這棟大樓“暴力襲警”,連刺11名保安、警察,死亡6人,重傷5人,驚動全國。
7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經過9天的“深入偵查和廣泛調查取證”,將該案移送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7月17日,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楊佳涉嫌故意殺人罪。然而,原定于7月29日下午開庭的楊佳襲警案并未如期進行,開庭時間可能推遲至奧運會之后。
在7月7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公安局稱,2007年10月5日晚,楊佳騎一輛無牌無證自行車途經閘北區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時,遇閘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邏民警盤查。因其拒絕出示身份證件和提供所騎自行車來源證明,造成市民圍觀、影響交通,被帶至派出所作進一步調查。
那一夜,在派出所究竟發生了什么?

“楊佳到底生殖器被打壞沒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教授劉仁文被好幾位京城法學專家如此詢問,這讓他感到很可悲,“只要網上一流傳,大家寧可信其有,不信其無。為什么?因為過去公安機關確實做過這種事情,要推翻別人的懷疑,卻沒有法官作證,也沒有律師作證。”
有識之士已經公開呼吁,上海警方應該公布楊佳的投訴材料,并公布派出所監控錄像的音像資料。
7月底,在閘北區公安隊伍建設暨政風建設大會上,區委常委、區公安分局局長童永正表示要領會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講話精神,處理好三大關系:一是要繼續堅持執法為民思想,處理好方便群眾和提高警惕的關系;二是要繼續糾正各種錯誤思想,處理好依法管理、嚴打犯罪與文明執勤、規范辦案的關系;三是要繼續堅持從嚴治警思想,處理好關愛干警和嚴處違規的關系。
“閘北這個案子,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韓國權痛心地說。韓曾是上海市第一警察學校、上海公安專科學校的公安概論教師,上海公安理論研究所專職研究員,現在是一名專職律師。在他看來,常態下,一般老百姓騎個自行車警察不必去管,管了,又作為過頭了。
檢方亦認為,楊佳要求閘北公安分局開除事發當晚的責任警察和索賠精神損失費1萬元等要求“未被公安機關接受”,與楊佳襲警是因果關系。
“慎獨”難
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是,大部分網絡民意同情楊佳,哀悼無辜警員的評論很少。襲警新聞中的任何一個漏洞,都會被挖出來放大,作為抨擊警察隊伍的口實,比如楊佳的動機,甚至說楊佳是英雄。
不過,“一個人不能強調有別的原因就做出這樣的行為,否則的話,任何一個人都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找到一個理由,那社會就亂套了。”劉仁文教授一面批駁上述網絡民意,一面提醒,“這說明楊佳的行為迎合了一種逆反心理,是一種挑戰官方的行為。”
再仔細研讀公眾在互聯網上的言論,我們發現,絕大多數公眾的不滿并不是對楊佳殺人的支持,而是對警方不能公開楊佳作案的動機、不能公開案件事實真相、不能依法辦案的抗議。一言以蔽之,這是輿論對警務公開的監督,公眾不僅期待警方擁有公權力,還要擁有公信力。
事實上,近年來暴力襲警在上海并非零星個案,據來自上海市檢察院的數據,2007年1月至8月,檢方共向法院提起公訴暴力襲警案件41件320人。截至去年8月,上海市公安民警及受委托從事公務活動的社保隊員在執法中遭受暴力侵害情況突出,暴力襲警案件造成遇襲民警、社保隊員1人死亡、2人重傷、16人輕傷、256人輕微傷的嚴重后果,“已經出現了有預謀、有組織的報復性襲警案件”。
不難發現,楊佳襲警案的暴力程度遠超以往。從警察角度反省,劉仁文認為警方在社會矛盾多發時期,對社會的“閱讀能力”不強,欠缺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抗的策略和方法。警方存在著“重大案、輕小案的傾向”,面對楊佳這種小人物的申訴不予重視,久而久之,矛盾由小變大,直至不可收拾。
“個人的積怨深了,就難免出現偏激行為。”劉仁文說。
此外,有研究者從深層矛盾來查找暴力襲警頻發的原因,指出,暴力襲警是警察權威弱化的危險信號,“暴力襲警就是不服從警察權威的極端形式”。
相較警察權力,警察威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軟實力,包括認同、服從、信任、支持和協助五個方面。顯然,如果沒有這些軟實力,警察權威就得付出更大的代價來完成對社會的外在整合,需要采用強力手段才能達到維護秩序的目的。警察本來是和平時期最危險的職業之一。
多年來,警察執法工作作風問題重重,權錢交易、徇私枉法、濫用權力等現象又屢有發生,特別是基層警察部門的非警務活動泛濫,警察權威嚴重受損。上海市公安局曾做過調查,基層警察部門的非警務活動占去警察工作量近30%,“各條線自上而下布置工作,一味索取,使得派出所工作透支”。
“商業動遷,動用警察;企業勞資矛盾,也動用警察……用警用濫了以后,警察就沒有權威了。如果在老百姓心目中警察不是保護人民權利的,而是貪官污吏的爪牙,哪還有權威啊?”韓國權反問道。
韓國權的很多學生現在都是上海各警察機構的頭了,不論是當初的公安概論課,還是現今閑談,韓國權都督促自己的學生“依法治警”,將警察權力放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行使,“抓住自己的主業,種好自己的自留田,我當時上課,在黑板上寫‘慎獨兩個字,整整講了一節課”。
可是,很少有學生能照他說的去做,有學生回來告訴他:“韓老師你說話容易,我這個派出所長,抵制非警務活動以后,下一屆所長我當不了了。”現在,上海一個街道辦事處主任都能調動派出所所長,雖然上海市公安局也嚴禁非警務活動用警,但沒有機制保障,武寧南路128號(上海市公安局辦公大樓)也沒有辦法。
警察權的邊界
慎用警力。這是甕安事件和楊佳襲警案的共同警示。
除了規范地方政府非警務活動濫用警力外,制度設計中警察權力過大問題已經成為警民關系緊張的“活水源頭”。法治社會,警察權力的行使必須要控制,對警察權力進行制約,是法治國家時代的重大命題。不受監督與制約的權力會自發地向外和向內尋求擴張,導致越權和濫權、擅權。以“協助調查”為名變相限制人身自由的事情,也不是沒發生過。殷鑒不遠。
在國家權力體系中,公安機關一直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相比國外警察權普遍受制于司法權而言,中國警察在實體和程序兩方面均具有較大的獨立執法權,前者如治安拘留和治安罰款等治安處罰,后者如刑事拘留以及對犯罪嫌疑人是否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決定權。事實上,公安機關是一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合一的混合型執法機關。
劉仁文介紹說,在法治比較健全的國家,警察抓人,要提供一下免費電話,讓當事人給家人打電話,給律師打電話,而且,還可以要求法官聽審。“我們現在抓到以后,不容許跟外界聯系”。“從體制上反省,警察要不要受法院的制約?公安機關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要經過法官,要經過律師,這是國際人權公約最低的標準。”經過這兩把篩子,真的需要被逮捕的被逮捕,不需要被逮捕的放掉,“老百姓的怨氣就沒有了嘛”。
警察好比一個拳擊手,警察權是刀把子,輕易不能用;而司法審查好比拳擊手套,給拳擊手戴上手套,即使不小心打到一般老百姓,殺傷力也會減輕不少。因此,劉仁文提出建議,對公安機關進行適當的分權,將涉及剝奪人身自由的實體處罰和強制措施統統納入法院的審查范圍,從體制上給高風險的警察權減負。
韓國權提醒記者說,建國之初,一個警察在人民心目當中,代表著人民政府,當時一個戶籍民警,管工作、管生活……什么都管。現在,國家實施依法治國方略,警察再也不能代表同家,公安機關只是政府下面一個專門負責治安行政的職能機構,但這是一個不同于一般行政機關的行政機關。“但我們卻把它當作一般行政機關在建。”韓國權說。
“公安機關本來是刀把子,不能隨心所欲地動用警察,它不是一般的行政機構,警察一出錯就兩樣了。”韓國權說,行政機關首長負責制,下級無條件服從上級這條原則不適用于政府首長跟公安局長的關系,“動用警察,要有制約條件”,“什么情況下能用,什么情況下堅決不能用”,為公安機關拒絕政府首長錯誤指令建立保障機制。韓國權的建議,實際上是“限權”,動議立法設限使用警察權的邊界。
法治國家的兩大原則是行政限權和司法控權。過去,人們常說,警察權受命于國家,受制于法律。顯然,這還不夠。權力必須要有監督與制約,也唯有權力才能制衡權力,愈重要的權力,愈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權力來進行制約和監督。要之,依法限權、以權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