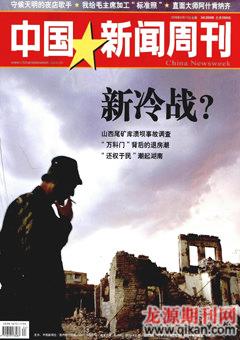“北京新市民”:城市生存之憂待解
北 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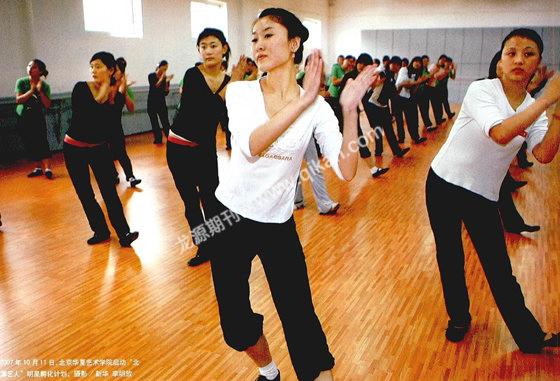
十多部地方法規規章限制北京新市民民生權利,導致城市的健康持續發展或存隱憂,律師學者聯名上書,力促新北京人獲享市民待遇
在北京,蘇琪生活了8年,她是一名電腦程序員。
每一次打電話回家,親戚都會羨慕地說:“妮子啊,你現在是北京人,不簡單啊。”
蘇琪便會呵呵笑兩聲,讓對方感到自己的謙虛。其實,她知道,這完全是自嘲。
蘇琪只是所謂的600萬“北京新市民”中的普通一員。他們遠離故鄉,在北京長期工作、生活,一直被視為“暫住人口”。在他們中,定居趨勢與被排斥感同時與日俱增。
近年來,以同城待遇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呼聲日高。
2008年8月28日,知名公益律師李方平和中國問題學者胡星斗,向北京市政府提交一份七千余字的《公民建議書》。
“我和這座城市,永遠在兩條平行線上”
李方平,北京市瑞風律師事務所律師。
住在北京的10年中,他獲得了很多榮耀。2006年,他代理河北邢臺輸血感染艾滋病案,被評為“2006年河北省十大法治事件”,“天津乙肝歧視第一案”被評為“2006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之首。
與自己的現實難題相比,這些榮耀不值得一提,至少在他看來是如此。自1998年6月進京工作生活以來,李方平的戶籍一直留在外地。李方平感到麻煩事很多。
2006年,李方平報裝固定電話,發現北京網通規定,“客戶戶籍所在地或注冊登記地不在北京市的,客戶應按北京網通要求辦理相應的擔保手續,或者辦理預付費的業務(服務)”。李方平找不到也不愿求有北京戶籍的市民辦理所謂的擔保,選擇辦理預付費業務。
李方平沒有想到的是,預付費業務與后付費業務一字之差,讓他在北京網通推廣的一系列優惠活動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
性情溫和的李方平終于爆發。2008年8月1日,他以歧視對待之名將北京網通公司訴上法庭。
蘇琪在報紙上看到李方平這場官司,“都是異鄉人,我完全能理解,也有切身體會。”她到北京第二年,想把戶口辦過來,興沖沖地去派出所詢問,一位警員懶洋洋地問道:“在北京連續3年,每年納稅達到80萬元了嗎?”
蘇琪詫異地搖頭。
“或者,你能證明自己是一個近3年納稅總額達到300萬元的私營企業主?”警員繼續問。
蘇琪依舊搖頭,他覺得自己“好卑微”。
那位警員終于抬起頭:“回去吧,看你這樣,也就一普通北漂客,全北京好幾百萬。”
在北京,外地人遷入戶口而完全享受北京市民待遇,需要較高的條件——文化藝術名人、體育明星;國內大型企業(集團)、各類金融機構在京注冊的總部董事長等高管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或者留學歸國的急需人才。
仿佛受了羞辱的蘇琪,在接下來的一年多中,不再提與戶口有關的事情,“省得煩”。“我和這座城市,永遠在兩條平行線上。”蘇琪低沉地說,如同一位落魄的吟唱詩人。租住的小屋窗外,南三環上的汽車川流不息。
律師李方平也有類似的煩惱。這位曾經發表多篇“公民建議書”的律師,終于決定和胡星斗一起,向高層提交有關北京戶籍問題的公民建議書。后者是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失衡的公民權利
“一次選舉都沒有參加過。”蘇琪說,“在這里,我儼然成了喪失政治權利的人。”
她詢問居委會,被告知,“戶口在外省市而現居住在本市的人員,一般應當在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不能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的,由本人提供戶口所在地出具的選民資格證明,也可以在現居住地進行登記。”
小蘇很無奈,“離家那么遠,誰會大老遠跑回老家去參加選舉或者開張證明?”
“選舉權或許還有些形而上的,房子,卻是實實在在的形而下難題。”蘇琪說。
2008年年初,蘇琪想買房子,但被居高不下的樓價弄得有些心灰意冷。她的一位摯友,因為是北京戶籍,已經開心地住進新房。“她買的是‘兩限房,很便宜啊。”

所謂兩限房,是指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此類房屋較普通商品房更低廉。
北京官方文件規定,“兩限房”的銷售對象為“具有北京市戶口的中低收入家庭”。2007年4月,北京市開始集中開發 “兩限房”,以調控不斷快速攀升的房價。
“長期在北京居住、生活的新市民卻被‘兩限房排除在外,這不公平。”李方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買不了低價的“兩限房”,買不起高價的市場房,蘇琪覺得,“將來幾年的單身生活里,繼續租房,靠譜些。”
奧運開幕前一個月,房東卻找到蘇琪,提出加價,“都奧運了,怎么著也要跟著漲點。”蘇琪不服,用豪氣干云的語調表示:“會在一個月內搬走。”
很快,她還是屈服了,“都在漲,相比之下,住在原地,還能省去一筆中介費和搬家費。”
蘇琪向一個好友訴苦,對方的話讓她“差點吐血”。“他是北京人,他說自己可以弄到廉租房,便宜得很了。我的煩惱在他看來居然成了笑談。”
北京市政府關于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兩個管理辦法,都是根據《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簡稱《若干意見》)制定的。
《若干意見》顯示,廉租住房的受眾是“城市低收入家庭、農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難群體”。
“很顯然,部分外來在京工作人員也應該包括在‘農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難群體,可是北京市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對此只字不提。”李方平和胡星斗說,“這不合理。”
“當然,北京市也做了些努力。”李方平說,他所指的,是所謂的“北京綠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證”。
持有“北京綠卡”,可以“在購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學等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異鄉人從“北京綠卡”上看到了在這座城市長久生存的信心和熱情,蘇琪也打算辦一個。很快她發現,“綠卡不是靈丹妙藥”。“綠卡”族的孩子雖然一直在北京就讀,卻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而此時試圖回到老家報考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孩子的學籍不在老家。”
“部分一時想不開的孩子無奈自殺,讓人不免唏噓。”李方平說。
蘇琪還是單身,尚無子女就學的擔憂,就業上的不平等遭遇卻是經歷過。在成為電腦程序員之前,她曾打算做一名京城的出租車司機,“可以賺錢,又可以跑遍京城,四處玩玩。”蘇琪很快就放棄了。她看到《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和《北京市小公共汽車管理條例》中都規定,駕駛員應當具備的條件之首便是本市常住戶口。
“北京戶口、北京戶口……”蘇琪回憶往事,突然爆出一句字正腔圓的北京話,“你大爺。”
除了司機等市場化的職業外,“北京戶籍”也卡住了外地在京者跨入公務員隊伍的腳步。
李方平和胡星斗認為,北京市招考公務員惟戶籍論不妥,這與《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人員暫行規定》中的原則存在沖突。
居住制度改革期待
蘇琪感到困惑,自己在北京生活工作,“每個月工資得交個人所得稅,平時消費要交消費稅,不比北京本地人少,怎么享受的待遇就少了很多呢?”
北京市沒有勞動能力的戶籍老人人數在400萬左右。外地進京的600萬~700萬人絕大多數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中青年。
新華社曾報道,2007年北京GDP總量9006.2億元,按北京常住人口1633萬人計算,人均GDP達到56044元。這已經處于世界“中上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顯示了北京市具有較強的生產力和財富創造的能力。
不能忽視的是,北京人均GDP計算的人口基數是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計算的,并非北京市約1200萬的戶籍人口。分析人士稱,外地人給北京帶來的GDP總值將近北京市總值的1/3強,約為3000億元。
“但,在這里,福利管理和GDP存在失衡。”李方平說,“這種失衡在觀念上根深蒂固。”
經典案例發生在2006年。當時北京市朝陽區人大代表耿素玲建議,對在京居住兩年以下的外地人員單獨征收商品房稅,理由是:北京的公共設施是北京納稅人的錢建設起來的,非北京人購買北京房產,使用圍繞房產的一系列公共設施,應該盡納稅人的義務,否則就是對北京人的不公平。
此言一出,嘩然一片。
我國稅制雖說是以流轉稅和所得稅構成的雙主體,流轉稅占總體的60%左右,所得稅不到20%,余者是財產稅、行為稅。
流轉稅具有轉嫁性質,其稅負基本都是由最終消費者承擔。這一性質在商品增值稅那里最能體現,其價稅在設計上就是分離的,消費者可以從企業和商家開據的發票中清楚地看到自己具體承擔了多少稅款。
盡管北京的納稅人(工商企業、個體戶)向北京市繳納了若干稅款,但這些稅收的真正負擔者,可以是北京市的消費者,也可以是來北京的外地消費者,還可能是北京的產品銷售所及地的消費者。
蘇琪月薪5000元,北京市政府把規定的補貼也加到扣除數之中,這些補貼包括交通費、洗理費、書報費、市內誤餐費、獨生子女費、托兒補貼費、奶費和煤火費,因此,每月她由公司財務部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370元。
如果有額外的收入,包括實物或有價證券都要納稅。比如公司過中秋節發幾箱飲料,也要扣數十元稅金。“這么下來,一年繳稅怎么也得四五千元。”蘇琪說,“另外我每月平均存款2000元,一年下來的存款利息也要繳稅的。”
2007年3月,蘇琪曾接到一張“流動人員登記表”。在這份北京市官方下發的登記表中,除了要填“綽號”之外,還要寫“高危信息”,填寫有哪些“違法可疑行為”“被打擊處理情況”;還要對“散發過小廣告,兜售盜版淫穢光盤,從事封建迷信、非法行醫”等項目進行選擇。
“明顯的歧視。”蘇琪當時就表示抗議,非京籍員工不應該不被尊重。
“同樣在納稅,同樣是經濟貢獻者,就不應該有這么大的差別。”李方平說,“如果北京現行居住制度維持不變,新市民承受的差別待遇將繼續存在,并進一步代際繼承。”學者胡星斗則說,千頭萬緒的新市民居住制度已經積弊多年;越是延后,改革的難度也越大。
“居住制度改革應當分兩步走。”在《公民建議書》中他們提出,第一步,把戶籍制度中人口流動信息登記職能和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教育、經濟福利等權利分開,確立戶籍自愿流動登記制度。
“北京市居住制度改革可以借鑒美國社會安全號碼制度,建立一種利益誘導型而非治安防控型的社會管理體制。”
新市民的居住登記應該與其今后享受公立教育、公共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等社會公共品供給有機結合起來。
李方平說:“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統一啟用一人一號、長期有效并可實現電腦聯網的‘北京新市民居住及社會保障卡,申領范圍為在北京居住超過半年以上并滿16周歲的北京新市民。”
他認為,居住及社會保障卡可以動態地記載持卡人申報的身份信息、居住現狀、聯絡方式、婚姻狀態、教育履歷、家庭構成的基本信息,以及銀行、稅務、公安聯網的信用、納稅、違法違章記錄,以上信息只是作為相應的職能或銀行機構對口查詢的公民隱私信息,北京市政府應該同時立法保護此類隱私信息在非法定條件下不被泄漏。
“十年”之遇
目前九成以上的流動人口在京居留半年以上,五成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平均來京時間接近6年,舉家遷移的比例超過四成。北京市計生系統發布的數據也顯示:北京新生兒六成是流動人口所生。
很多時候,蘇琪幾乎都覺著自己是北京人了,“8年了,抗戰都結束了。”她已經一口地道的京腔,對京城的好玩有趣之地早已了然于胸,“在這,一大幫朋友,與老家比,這里已經更適合我了。”
蘇琪覺得,在北京居住的時間越長,人際網絡越廣,擇業機會越多,社會競爭力越強,抗風險能力越大,生活穩定性越高,家庭團聚愿望越強,離京代價越大,定居傾向越強。
這并非蘇琪一人的感受,“隨著時間的推移,絕大部分新市民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定居人口。”李方平說。
因此,李方平和胡星斗上書中建言:“一、居住六個月以上至三年為‘短期居住,賦予部分市民權利;二、居住三年以上為長期居住,賦予更多的市民權利;三、居住十年以上視為永久居住,可以同享所有市民待遇。”
“一個現代的城市首先要開放和包容,讓每一個在此生存的人享受到公平合理的制度保護,權利得以伸張。”李方平說,《公民建議書》已經成功上呈給北京市政府。
“只有更加寬容和具有活力,北京才堪稱宜居都市。”8月末的一個下午,蘇琪在北京宜家一邊挑選書櫥,一邊說:“我還是很愛北京的,希望北京也能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