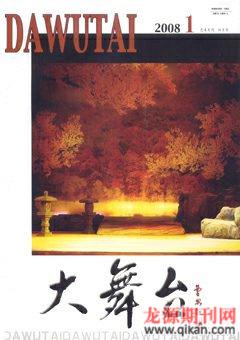淺析感性與理性的交融與碰撞
【內容摘要】本文就《傅雷談音樂》中傅雷感性與理性認識相結合的觀點為依據,從心理學角度出發,論述感性與理性之間相輔相成、互相滲透的理論關系,分析、舉例、證明感性與理性對音樂家的影響及在作品演奏中的滲入,使演奏者形成自己獨特的演奏風格,正確詮釋音樂作品。
【關鍵詞】感性 理性 碰撞 交融
傅雷(1908—1966),我國著名文學藝術翻譯家、藝術鑒賞家、評論家。早年留法受羅曼·羅蘭影響酷愛音樂,三十年代中期對中外音樂已頗有研究,而時日愈長,修積愈深,音樂藝術上的造詣更見豐厚。其撰寫的音樂述評、樂曲賞析,與傅聰及世界大師們的音樂通信,無不語中竅要,真知灼見。
《傅雷談音樂》一書經傅雷之女傅敏遴選有關論及音樂藝術和藝術修養的內容,重新整合,2005年由當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全書編成“音樂述評”、“音樂賞析”、“音樂書簡”、“與傅聰談音樂”、“音樂筆記”五部分。“與傅聰談音樂”這部分,編入了“音樂筆記”,其中有他對音樂藝術的心得體會,也有經他翻譯并加批注的研究某些作曲家的資料,不遠萬里郵寄兒子(傅聰),使其不斷從成長走向成熟,不僅成為國際知名的鋼琴家,更是一位德藝具備的受人尊敬的藝術家。
一、“感性認識是初步印象,是大概地認識。”[1]
感性認識是認識過程的初級階段和初級形式,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關于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外部聯系、事物的各個片面的認識。感性認識包括相互聯系、循序漸進的三種形式:感覺、知覺和表象。
感覺,是人對事物的最初反應,是主體的感官對內外環境適宜刺激物的反應形式。每位音樂家的作品都是從情感出發,不同層次、不同強度、不同境界的感情色彩,經過不同的表達手法將熾熱的情感、悲傷、幽默、歡樂等感性因素表現出來。例如:威瓦爾第的自然流暢、清新幽雅;莫扎特的入世寧靜、天使一樣的純潔;貝多芬對命運的反抗和對人類的熱愛;舒伯特的惆悵;肖邦赤熱的愛國之心等各種真摯的情感。演奏者須熟悉作曲家的風格特征和情感因素,才能對作品有更深刻的反映。然而,同一時代、同一背景下,不同的作曲家也有不同的風格。如:同時誕生于1685年—巴洛克后期的三位偉大的音樂巨匠:巴赫、亨德爾和斯卡拉蒂,卻各自擁有獨特的、迥然不同的風格。巴赫深厚典雅,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亨德爾率直坦白,不流于庸俗;斯卡拉蒂則是優雅高貴,遺世孤立。由此不難得知,演奏者若只是單一的知道作曲家的風格還遠遠不夠,要更進一步的分析形成這種風格的外界因素,方可從整體上對作曲家的風格有深刻地認識。
知覺,是對客觀事物表面現象或外部聯系的綜合反映,它為主體提供客觀對象的整體映象。形成作曲家風格的外界因素包括:作曲家生活時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音樂歷史的發展,樂器的改進狀況,以及作曲家本人的身體狀態、精神動態、家庭婚姻。每個作曲家的精神氣質都是其社會生活背景的一個客觀反映,他們的作品不僅僅局限于藝術領域,更多地涉及到了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重要領域,如哲學、歷史、文學、美學、社會學等,使其不僅有音樂天分,還具有社會良知。貝多芬若僅僅作為作曲家,就不會寫得出《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里的《歡樂頌》合唱,因為這首合唱的偉大藝術已經超出了音樂,表達了貝多芬對人類的愛、對惡劣命運的勝利。這種胸懷不是僅注重音樂的人就能具有的。所有偉大的藝術家都是人道主義者,音樂只不過是用來表達他們人道主義思想的工具,整天在工具上下功夫的認知是“機器”級的人物。
表象,是在感覺和知覺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感性形象,是感性認識的高級形式。演奏者正確地感受作曲家情感特征,最主要的是要把曾經作用于自身感官的事物的外部形象在意識中保存、再現或重組,也就是轉化為表象,使自己在對作曲家藝術氣質形成因素的探索研究后能擴大視野,增強修養和處世,更加豐富音樂的創作和演繹。由感覺到知覺再到表象,是人的認識由個別的屬性和特征上升到完整的形象,由當下的感知達到印象的保留和概括的再現的過程。但是,從人的完整認識過程來看,這些感性認識形式是對事物的表面特征的描述,還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要過渡到更深境界的理性認識。
二、“理性認識是深一步的,了解到本質。”[2]
理性認識是認識過程的高級階段和高級形式,是人們憑借抽象思維把握到的關于事物的本質、內部聯系的認識,包括三種形式:概念、判斷、推理。
概念,反映事物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是構成科學體系核心的邏輯要素。演奏者單靠感性認識是不能科學的理解作品的,還需要從理論方面、邏輯方面、史的發展方面的知識來充實。理論方面是指音樂的表達方法,如和聲、曲式、對位等作曲手法;邏輯方面指結構和風格上的對比和統一,也就是美學范疇里的元素;史的發展指樂曲在音樂發展史上的地位、背景和價值,以及樂器進化改革的現狀。對作品概念的學習可使演奏者提高樂句分析水平,加強句法處理深度,強化音符記憶能力。
判斷,反映事物關系的思維形式,是對事物的狀況和性質有所判定的思維形式。演奏者弄清作曲家的創作手法,還只是基礎,要懂得如何使用正確的技巧訓練,即要學會并經常用腦,一切技巧的訓練都要講究方法,不能盲目的機械練習,要用高度的腦力活動尋求科學的方法,在技巧練習過程中,可結合老師的教學方法,每個人都有本身個性的特點和缺點,老師的教學方法也因人而異,可能其指導不能起一針見血的作用,但學生可結合實際情況,思索并實踐,求同存異,尋得更適合自己的一種奏法,以達到樂曲所要求的技巧程度。敏銳的聽覺也是腦力勞動的一個重要因素,要能冷靜、理智的分辨音符的色彩、音質的特色,以至于裝飾音、連音、半連音、斷音等的處理,都是構成一個作曲家的特殊風格的重要元件。如:古典時期作家的音講究圓轉如珠;印象派德彪西的音多數要求含渾朦朧;浪漫派舒曼的音則追求的是濃郁深沉。
推理,由已知合乎規律地推出未知的思維形式,是通過對某些判斷的分析和綜合再引出新的判斷的過程。演奏者即使已經對每個月章、樂段、樂句、樂節以及音符的徐疾輕緩、意義和感情有了深刻了解,并且按照譜上寫定的音符的長短、速度、節奏,極其嚴格的彈奏也不可能完全表達出作品的原貌,事實上,每個小節的音樂,演奏的人不由自主地會在句節、休止、高潮、音樂、節奏等等作一些特殊的處理。因此,演奏家要反思自己對音樂的要求、理解和體會,在頭腦里刻畫出內心想要的是一種什么境界,這種思想是否接近于原作的精神,在處理時須有嚴謹的態度和邏輯的手法,不能“太過”或“不及”,前后要統一,成為一個整體。要令人覺得既表現了原作的精神原貌,又能反映演奏家的個人理念。
三、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輔相成、互相滲透
“藝術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認識,還不能限于理性認識,必須要進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3]傅雷認為演奏最好的境界是演奏者能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如果過分的注重感性,就會脫離原作的情感,不能如實的表達原作的內在含義。純理性的演奏者也只是彈琴的工具,不是真實的人的情感,必須要將感性和理性交融互助、相互滲透,才能真正的實現情感的表達。人的感性是有理性的感性,不滲透著理性因素的感性認識是不存在的。如果演奏者過分的注入情感,忽略理性的因素,就無法透徹的表達作品的精神境界,喪失樂曲在專業范疇里的顯著特征。反之,缺乏以感性認識為基礎的理性認識,就不是完整地認識。一味的追求作品的技術技巧,過于冷靜、死板,只是人化了的機器,就更不能完美的表現作品的風格特征,因而,演奏者要同時擁有感性與理性雙重認識,并將這兩種認識相互作用、互相交錯、相輔相成,既能擁有感性認識的初步印象,又能通過理性認識了解事物的本質。
但是對藝術的領悟還不能僅限于此。必須在深入進去,在感性與理性認識相結合的基礎上,用心靈去體會,使原作者的悲歡喜怒轉化為自己的悲歡喜怒,使原作者的每一根神經的震顫都在自己的神經上引起反應,感受他的脈搏與心跳,使他活在自己的心中,與之產生共鳴。感之深,愛之切。一切偉大的藝術家都兼有獨特的個性和普遍的共性。演奏者只要能發覺自己心中的共性,找出、抓住與原作者的共同點,建立溝通的橋梁,細心揣摩,就能體味出作曲家獨特的個性。當然,也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和感受一模一樣,無論在任何方面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出入,演奏者自身的性格特征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演奏者要以真誠的態度去體會作曲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用一顆坦誠的心、放下高傲的虛榮心了解自己,打開自己的心扉,以寬闊的胸懷了解自己、了解別人,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
演奏者不能只是作為演奏的機器和操縱演奏工具的工匠,要有思考、有想法的表現作品的內涵、傳達作曲家的創作理念,以真誠、敏感、堅定、虛心、好學的態度,在感性與理性相互碰撞與交融的基石上深入感情,使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演奏家。
注釋:
[1]《傅雷談音樂》,傅雷著,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47
[2]同上
[3]《傅雷談音樂》,傅雷著,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148
作者簡介:
王相如(1982-)河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在讀研究生,河南省周口師范學院音樂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