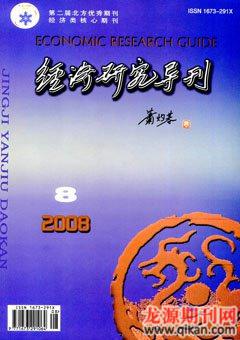中國(guó)隱逸文化中涉政現(xiàn)象初探
張兆林 紀(jì) 祥 宋 濤
摘要:中國(guó)隱逸文化中的涉政現(xiàn)象,并不是對(duì)隱逸文化的背叛,而是恰恰是使隱逸文化更具有多樣性的原因。分析隱選文化中的涉政現(xiàn)象,有利于擴(kuò)大傳統(tǒng)隱逸文化的內(nèi)涵,更清晰地分析清楚中國(guó)隱逸文化與政治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隱逸文化;涉政;雙重性格
中圖分類(lèi)號(hào):G05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文章編號(hào):1673-291X(2008)08-0192-02
任何社會(huì)都是經(jīng)濟(jì)、政治和文化的有機(jī)結(jié)合,文化歷來(lái)是社會(huì)生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文化多種多樣,千差萬(wàn)別,有古今、地域之別,也有先進(jìn)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對(duì)經(jīng)濟(jì)、政治的影響是不同的,對(duì)社會(huì)的發(fā)展也起不同的作用。
中國(guó)隱逸文化作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分支,是社會(hu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勢(shì)必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政權(quán)政治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而文化對(duì)政治產(chǎn)生影響的主要途徑就是靠在本文化領(lǐng)域有一定素養(yǎng)的人通過(guò)涉政,從而發(fā)揚(yáng)光大。中國(guó)隱逸文化的主體大都是飽學(xué)之士,深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他們同樣面臨著進(jìn)與退的兩難選擇,入世王侯將相,出世則漁樵耕讀,寄情于山野。中國(guó)文人向來(lái)有以天下任為己任的傳統(tǒng)思想,這也決定了隱士會(huì)積極的參與政治,每個(gè)時(shí)代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涉政現(xiàn)象。
一、中國(guó)的隱士是否討厭政治
中國(guó)古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標(biāo)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窮則獨(dú)善其身,達(dá)則兼濟(jì)天下”,作為文人的一個(gè)部分,隱士也不能例外。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我們看到了隱士在兩難選擇的十字路口的一種悲哀和無(wú)奈,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們?cè)凇斑M(jìn)”與“退”的人生旅途中顯現(xiàn)的超凡智慧。
儒家文化教育人們“學(xué)而優(yōu)則仕”,這種思想在封建社會(huì)居于主導(dǎo)地位,而隱士大多是飽學(xué)之士,對(duì)儒家文化更是崇拜。儒家文化提倡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要求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人們面對(duì)生活的艱難和坎坷的時(shí)候,要保持樂(lè)觀(guān)向上的心態(tài),所以也就有了隱士們積極參與政治的現(xiàn)象。孔子的積極人生觀(guān)告訴我們,積極進(jìn)取、樂(lè)觀(guān)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不僅是一種心態(tài),而且更是一種智慧,命運(yùn)與機(jī)會(huì)常常青睞于那些積極樂(lè)觀(guān)向上的人。
當(dāng)然,并不是所有的隱士都喜歡涉及政治,但多數(shù)希望通過(guò)“入世”來(lái)施展自己的才學(xué),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抱負(fù)。中國(guó)任何一個(gè)朝代的隱士都試圖參與政治,并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田園詩(shī)人陶淵明曾多次“人世”,先后官拜江州祭酒、劉裕的參軍、劉敬宣的參軍、彭澤令。浪漫詩(shī)人李白也為“入世”不懈努力,由道士吳筠的推薦,被召至長(zhǎng)安,供奉翰林。久居深山的商山四皓在漢太子劉盈的盛情相邀下出山成為他的輔佐大臣,從而鞏固了劉盈的太子地位,后為漢惠帝。人稱(chēng)“臥龍”的諸葛亮在隆中臥龍崗隱逸十年[建安二年(197年)建安十二年(207年)],在劉備“三顧茅廬”后,出山輔佐劉備,后成三國(guó)鼎足之勢(shì)。
二、中國(guó)的隱士能否在當(dāng)時(shí)的政治舞臺(tái)上施展拳腳
中國(guó)的隱士能否在當(dāng)時(shí)的政治舞臺(tái)上施展拳腳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們?cè)凇叭耸馈焙竽芊窦皶r(shí)的抓住有利的機(jī)會(huì),得到當(dāng)權(quán)者的支持。張良,字子房,漢初三杰之一。《后漢書(shū)注》云:“張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毫州市東南人。張良曾隱于下邳(今江蘇睢寧北)數(shù)年,潛心研習(xí)《太公兵法》,俯仰天下大事,終于成為一個(gè)深明韜略、文武兼?zhèn)洌阒嵌嘀\的策略家。在輔佐劉邦過(guò)程中,張良得以大施拳腳。通過(guò)“降宛取蟯,佐策人關(guān)”、“諫主安民,斗智鴻門(mén)”、“明燒棧道,暗渡陳倉(cāng)”、“下邑奇謀畫(huà)箸阻封”、“虛撫韓彭,兵圍垓下”、“勸都關(guān)中,諫封雍齒”不但幫助劉邦得了天下,而且使得漢朝初期呈一派祥和景象。劉邦盛贊張良:“運(yùn)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寫(xiě)詩(shī)贊道:“漢業(yè)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義韓彭地,復(fù)道方圖雍齒封。”
當(dāng)然,在政治舞臺(tái)上,許多人無(wú)法自保。文人出身的隱者,更多的是考慮下層社會(huì)的利益,有著“天下歸仁”的情懷,但他們卻不能找到或不能遵從于官場(chǎng)的定律,因此常常受到非議和排擠。如杜甫、白居易等。當(dāng)隱者的政治觀(guān)和其他政治觀(guān)一旦發(fā)生碰撞。敗走的就往往是這些隱者,這樣一來(lái),隱者就只得遠(yuǎn)離政治,并由此產(chǎn)生和豐富了隱士哲學(xué)。
三、中國(guó)的隱士能否在政治舞臺(tái)上全身而退
中國(guó)的隱士因個(gè)體的差異使其在政治舞臺(tái)上的結(jié)局迥異。田園詩(shī)人陶淵明終因不滿(mǎn)時(shí)政黑暗,棄袍掛冠,拂袖而歸。李白雖文章風(fēng)采,名動(dòng)一時(shí),頗為玄宗所賞識(shí)。后因不能見(jiàn)容于權(quán)貴,在京僅三年,就棄官而去,仍然繼續(xù)他那飄蕩四方的流浪生活。但是成功亦不乏人,漢時(shí)張良,自從漢高祖入都關(guān)中,天下初定,便托辭多病,閉門(mén)不出。隨著劉邦皇位的漸次穩(wěn)固,張良逐步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wú)、時(shí)進(jìn)時(shí)止的處事原則。論功行封時(shí),按級(jí)頒爵,漢高祖劉邦令張良自擇齊國(guó)三萬(wàn)戶(hù)為食邑,張良辭讓?zhuān)t請(qǐng)封始與劉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蘇沛縣),劉邦同意了,故稱(chēng)張良為留侯。張良辭封,自請(qǐng)告退,摒棄人間萬(wàn)事,專(zhuān)心修道養(yǎng)精。此時(shí)的張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再次開(kāi)始了自己的隱逸生活。呂后在劉邦死后,強(qiáng)勸張良結(jié)束學(xué)道生活,回朝做官,張良聽(tīng)從了勸告。惠帝元年,張良病死,謚號(hào)文成侯,終得善終。
所以涉政之人,在功成名就之后,應(yīng)該保持謙卑平和的心態(tài)。張良與諸葛亮等做得較好,在他們輔佐君主成就大業(yè)的前后,都是謙卑與平和的,這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隱者的智慧。
通過(guò)上述事例,我們不難看到隱者的悲哀與痛苦,但我們還應(yīng)該看到他們超脫的智慧,那就是,他們既力求保全自身,又要選擇自由的個(gè)性。所以李白既能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也能夠低吟“自古圣賢皆寂寞”。包括李白在內(nèi)的隱者都明白,選擇政治就必須隱藏個(gè)性,退隱山林則可能清貧一世。沒(méi)有人愿意選擇第二步,而這種選擇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想人世為官,身居顯赫,想為民請(qǐng)?jiān)福瑸閲?guó)出力,但他們幾乎都是“政治文盲”。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相對(duì)豐厚的官場(chǎng)學(xué),他們一無(wú)所知。秉天而行的性格,只能讓他們?cè)谡挝枧_(tái)上步履維艱,進(jìn)退維谷,他們不懂得左右逢源,阿諛?lè)畛校谑牵幪幣霰冢谶@種情況下,明智的退卻就是一種超凡的智慧,這種智慧保全了中國(guó)隱者的自然天性,也成就了他們?cè)谥袊?guó)文化當(dāng)中的輝煌。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隱者在實(shí)現(xiàn)自己政治目標(biāo)的過(guò)程中肯定會(huì)觸犯其他人乃至君主集團(tuán)的利益,一旦如此,他們只得選擇退隱山林,尋找他們冷漠的人生終歸,他們對(duì)政治的叛離并不是無(wú)情的,而是無(wú)奈的。他們遠(yuǎn)離政治紛爭(zhēng),與山間明月為友,與石上清泉為伴,或登高望遠(yuǎn),或臨溪汲水:或仰望長(zhǎng)空,或低酌淺飲。其實(shí),這種出世的選擇是隱者們不情愿的,他們寧愿躋身于朝堂之上去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也不愿意歸隱山林,孤獨(dú)一世,清平一生。所以,出世是隱者無(wú)奈的選擇,也是隱者悲哀的宿命。
在進(jìn)與退的兩難選擇中,我們看到了仰天長(zhǎng)笑的豪者,采菊東籬的閑者,獨(dú)釣寒江的適者,凝視逝水的智者,感嘆命運(yùn)的明者。隱者用這種詩(shī)意化的生活方式蕩滌塵世蒙在自己身上的污垢,洗濯心靈的浮華,還原生命的本真,他們不甘愿泯滅個(gè)性,依附政治,就只得將政治悲劇帶回自然當(dāng)中,或遺憾,或反思,或?yàn)⒚摗K麄兓蛞髟?shī)作賦,或?qū)飘?dāng)歌,只有此時(shí),隱者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這種本真的生活中,我們看到了一種純真的智慧,回歸真實(shí)的生命本元,歸附自然的原始心態(tài),那才是大智若愚的真正人生。因而我們可以說(shuō),及時(shí)歸隱的智慧是一種明智的退卻。
古代隱者的雙重性格使得自己面臨著進(jìn)與退的選擇,不管他們?cè)谏穆猛局惺莿诳啾疾ǎ€是疲于奔命;也不管隱者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中是悠閑自得還是怡然自樂(lè),懂得如何把握好進(jìn)與退的分寸,懂得如何把握好得與失的度,懂得如何把握好政治性格與自然性格的關(guān)系,那才是關(guān)鍵。很多隱者面對(duì)涉政時(shí),因?yàn)樘淌赜诓缓线m宜的個(gè)性,太過(guò)于堅(jiān)守著某種不合適宜的原則,所以屢屢碰壁。但當(dāng)他們一旦面對(duì)山林,傾聽(tīng)百鳥(niǎo)鳴叫,親睹花開(kāi)花謝,天性就找到了真正的歸屬,他們也就釋然了。他們也明白人生一世,沉浮不定,禍福無(wú)常,生死不虞,何不隨波逐流任其自然呢?又何必在塵世的紛爭(zhēng)中將苦苦的掙扎當(dāng)作人生的本質(zhì)呢?不能,因?yàn)樵谒麄兊墓亲永铮魈手钭匀坏奶煨裕嬖谥钤嫉奈娜饲閼选?/p>
明智的隱者當(dāng)知進(jìn)退之由,當(dāng)知名成身退,明哲保身。這看似“無(wú)為”,實(shí)則“有為”,而且是“大為”。這正如草木枯榮一春秋,生物繁衍一生死,皆為正常之象。然秦之李斯,漢之韓信,唐之陸機(jī)等皆沒(méi)真正理解功成身退之意境。真正的文人政客如范子、張良、劉基等進(jìn)可輔國(guó),退可保身,既能人世,又能出世,實(shí)為明智隱者之典范。
綜上所述,隱者涉政,并非不可能。但要在政治舞臺(tái)上走多遠(yuǎn),走多好,就要看他們是否有大智慧。無(wú)論他們涉政結(jié)果如何,中國(guó)的隱逸文化都將因此而更為絢麗。
[責(zé)任編輯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