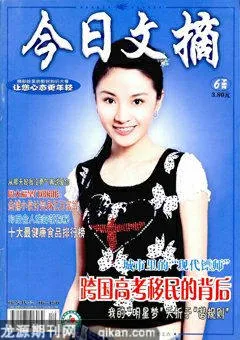澳大利亞農民不簡單
我在澳大利亞一座五萬多人的小城沃加住過一年。之所以叫小城,是拿中國標準來說的,而當地人總愛說沃加是新南威爾士州最大的內陸城市。
那一年時間里,為了工作,我整天開著一輛農用小卡車在野外搜集土壤標本。我要做的土壤分析圖覆蓋2500平方公里,有4個新加坡那么大,有起伏的牧場和一望無際的農田。剛到鄉下,你會贊美牧場農田的遼闊。時間一長,你就想念城市了,整天在野地里見不著幾個人的感覺,真是難受。
一次,我正和一個當地農民搭話,聽見遠處“啪啪”的槍響,一聲接一聲,不緊不慢,沒個完。
“這是在干什么?”我問。
他說:“槍斃羊呢。”
看我挺吃驚,他趕緊解釋說,這個農場主特別仁慈,不愿看著羊受罪,別的農場主呢,活活讓羊餓死。
那是個大旱年,地里光禿禿。買草料,沒錢。賣羊,沒人要。想槍斃羊吧,一顆子彈還要幾角錢呢,所以就看著羊餓死。我就見過剃完最后一次毛的羊,皮包骨頭,晃晃悠悠,一跟頭栽倒就再起不來。所以,他的話我能理解。
有一天,我在野外誤了返程的時間,回到停放車子的農場,門已經鎖了。這里的農場一般都很大,守農場的農民早已下班回城里的家了。怎么辦?實在不行,只能在露天睡了。正在做著最壞的打算,看見遠處有隱隱約約的燈光,我運氣還不壞,這家農場離鄰居不算遠。
我摸黑走了一個小時,到了鄰居家。狗已叫成一片,我不敢進院,怕讓狗給撕了。屋門一開,出來個老太太,喊住狗,把我領進屋,給我倒茶。老太太知道我餓了,端過一盤餅干。我趕緊說明白怎么回事。一會兒工夫,她兒子開著車來了,他帶我回到農場大門,從車上拿出扳子和改錐。
我以為他要撬鎖,誰想,他把整個大門給卸了,從合頁那頭卸的。我把車開出來,再幫他把大門裝上。我心里琢磨,光說謝謝不夠吧,人家費那么大勁,還有汽油,我是不是該問問人家收不收點服務費呢?可又怕說出這么冷的話,反傷人家,只好暗示著問:“還有什么事嗎,我是不是可以走了?”他露出驚訝的神情,說:“你不走還干什么呢?”
那一年里,我也記不清碰見過多少農民,反正越來越覺得他們不簡單,更不容易。他們會養牛羊,會種各種莊稼,會操作大大小小的農機具,農機具有點小毛病還會修。
農產品市場近幾十年都不景氣,農場稍稍經營不善就要虧本破產。他們還要預測市場,明年是養羊還是養牛,是種小麥還是油菜。可誰能估得準明年的羊毛價格?誰知道明年美國中部的小麥主產區會不會連陰雨大減產,然后國際小麥市場價格大漲?
最讓人著急的是天氣。每到播種期,農民一天聽10回天氣預報,問自己20回:今天播不播種?他們提著心播下種子,盼著三五天內下場雨。要是兩三個星期沒一滴雨,完了,種子瞎了。干脆下了雨再播種?外行話。地里泥乎乎的進不去拖拉機。進去也是攪和泥巴播不了種。
想想吧,他們肩上有多大壓力。可你看不出來,舊氈帽下曬得紅紅的臉總是那么平靜。你更料不到這些衣服又舊又臟的人,居然有那么多的知識、那么多的技能。■
(蔡爾平薦自《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