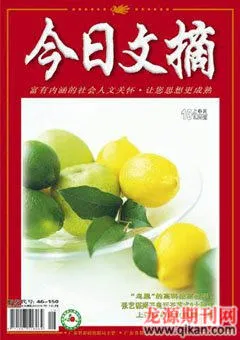愧疚終生的一次惡作劇
我的父親,是從一個很遙遠的窮山村“倒插門”(男到女家落戶)來到這個平壩小村的。過了不到半年時間,二舅娘就慫恿二舅鬧分家。在外公外婆的主持下,我們一家和二舅一家分住到了后院,后院有一個水泥地面的壩子,用來翻曬糧食,是兩家共用的。對于這樣的分配,父親是滿意的,也不敢有什么不同的意見,畢竟在農村,“倒插門”的女婿受點兒氣,是常有的事。
我很小的時候,就深切地感到,我們家和二舅一家的關系鬧得非常僵,僅隔十幾米相對而居的兩家人,大人們碰面從來是不打招呼的,好像母親和二舅原本就是陌生人,更談不上一絲一毫血脈相連的手足間的親情。
我小學六年級的那個秋天,雨水特別多,父母冒雨收回的濕稻谷全堆在屋子里等待晴天進行翻曬。天終于晴下來的那天,母親起了個大早,在泛紅的晨光中一簍簍將水分很重的稻谷搬到屋外的水泥壩子上,散開,等待太陽升高。母親很自覺,散開的稻谷只占了壩子靠我們家這邊的一半,另一半留給二舅家。
大約八點半,蜷曲在被窩中的我被窗外不堪入耳的辱罵聲驚醒,我趴在窗口向外望去,看見二舅娘一邊謾罵一邊揮舞大掃帚,狠狠地將我家的稻谷向我家的墻腳掃來,有些飛起來的稻谷散亂地落在了滿是污泥的陰溝里。不一會兒,整個壩子全部曬滿了二舅家的稻谷。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年幼的我無能為力,眼淚無聲地流下來。我想起每年因二舅家強占曬谷的壩子,使我們家的糧食一部分要發霉爛掉,想起他們常常占了我家的小便宜還有意無意欺負我的父母,我一雙拳頭捏得緊緊的,仇恨的火苗越燒越旺。我在心里對自己說:“等著吧,總有一天,我會報復你們的!”
報復的機會總算來了。那天,我從窗口偷偷看見二舅娘在家里脫下鞋子,準備赤腳到田間打理農活,我抓起早已預備好的工具,提前跑到二舅娘必經的田埂上,我把釘在一塊薄木板上的鐵釘釘尖向上,上面蓋上一層用來偽裝的雜草,之后便跑到遠遠的竹林中躲藏起來,看一場即將發生的“好戲”。
一陣聲嘶力竭的號叫伴隨裂心慘痛的聲音傳來,二舅娘滿地打滾,渾身糊滿丑陋的泥巴。這渴盼已久的景象,讓我激動萬分,又解恨又痛快異常,緊接著我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段時間,我每天最開心的事,就是放學后欣賞到對面二舅娘痛苦的愁容和她腳上纏著的厚厚的紗布,每欣賞一次,我就快樂一次,心中還嘀咕:“蠻婆娘,看你今后還怎么欺負我們。”
不久,我以優異成績考取了縣中,到四十多里外的縣城讀書去了。暑假回家,我與二舅娘正巧在壩子里碰了個正面,我看到她笨拙地使著拐杖,被刺傷的左腳下面一截褲子竟是空空的。二舅娘極不自然地沖我笑笑,一副好想說話的樣子,可最終也沒有吐出來一個字。我沒搭理她,徑直回屋去。
晚上,母親告訴我說,二舅娘的腳后來膿腫潰爛得厲害,被送到縣城醫院截肢了。聽完母親說的話,我仍然是滿腹幸災樂禍,還為自己建立的“豐功偉績”而得意,認為二舅娘是應得的,惡有惡報嘛。只不過那個天大的秘密我是不敢告訴母親的,也不敢告訴任何人,我叮囑自己,一定要將它只埋藏在我一個人的心里,永生永世埋藏得深深的。
上高中的時候,父親有一次在寄來的一封信中談到了二舅娘,他說二舅娘對我們家態度早已變好了,兩家的關系也基本正常,開始打招呼說話了。只是二舅娘現在的日子過得非常凄慘,幾乎成了廢人。這幾年二舅的脾氣越來越暴躁,常常打罵二舅娘,打得還挺狠,二舅娘知道自己變成了廢人,呼天搶地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常常地,她只有蜷縮在屋檐下痛哭流淚,罵自己命苦。父親在信中要我摒棄前嫌,忘掉過去,因為,畢竟二舅娘始終是我的長輩,這點是無法改變的。
我接到重點大學錄取通知書時,全村都轟動了,村長號召全村所有人家為我捐款,二舅娘也拄著拐杖一顛一跛走進我家,當著我的面,摸出手帕里包著的200元交給母親。母親高興地接過錢,要我叫聲二舅娘,我咽了咽口水,只費力地吐出“謝謝”兩個字。
我去上大學那天,全村很多人都來為我送行,一直送到村口,這其中也有拄著拐杖的二舅娘。我和在場的每一個人告別,聽他們的叮囑。輪到二舅娘,她搶先說話:“你……路上小心點兒啊!”那一瞬我的內心翻起一陣陣隱痛,終于情不自禁,主動抓住二舅娘的手,在眾目睽睽之下平生第一次順利而生動地喊出了三個字——“二舅娘”。
現在,我已成年,清楚明白我骨子里其實并不是一個殘忍的人,我崇尚善良,并且還是一個非常看重親情的人。但少年時一次懵懂的惡作劇,犯下的大錯已不容更改,因此,我注定要把愧疚遺憾背負終生。■
(刁維維薦自《城市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