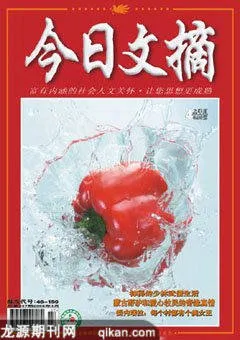空姐的“飛人”生活
周日大清早7時,剛從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畢業的艾維已經化好妝、穿上整齊套裝趕赴航空公司的招聘會,投考她的夢想職業——空姐。
“做空姐可以接觸不同的人,又可以見識新事物。”跟大部分應征者一樣,艾維抱著可以拓展眼界的心態前來應征。為準備面試,她事前不斷以英語跟自己練習對答,結果成功進入第二輪面試,向“夢想”邁進一大步。
然而,有現職空姐看到招聘會的情況卻不以為然:“我聽到他們說做機艙服務員福利好,又有人說因為交上一個空姐女友而樂上半天,聽完真要吐血!這一行并非大家看到的那么風光。”
在航空公司任職空姐7年、兼任工會代表的嘉瑪說,做空姐最辛苦的是要應付長途飛行的勞累。“我們有一條飛行路線長達8天,要連續飛幾次十多小時的路程,去到每個地點的時間都會好亂。”
地獄之旅難入眠
嘉瑪所說的“八天團”,是由香港出發,先到溫哥華,再飛紐約,然后回到溫哥華,再返回香港。雖然到達每個地點之后都可以稍事停留,但打從香港夜機起飛的一刻,便是痛苦的開始,因為既要面對十多小時的挨夜旅程,又要被混亂的時差折磨得頭昏腦漲。
“雖說空姐可以到處去,但其實不會有心情和精神去玩,飛這8天已會習慣失眠,所以一定要帶安眠藥同行。”嘉瑪說最初不知道時差的可怕,結果那幾天只能“眼睜睜”地度過,并沒有真正休息過。
除“八天團”外,航空公司的空姐路線圖中,還有一個公認的地獄之旅,便是由香港來回迪拜的路線:5天之中共要飛行6次,第一天由香港經曼谷到孟買,經過12小時飛行后,休息24小時,翌日由孟買飛抵迪拜再回到孟買,24小時后再由孟買飛往曼谷才回到香港。
“由迪拜到孟買的一程,抵達后已是凌晨四五時,一覺睡到當日中午,很快又要強迫自己再睡,因為接著凌晨3點便要回到機場,準備凌晨5點起飛,再整整工作12小時才回到香港。每個站都有人上飛機,乘客準備去旅行,總是抱著興奮的心情,但其實空姐熬到那個時候都累得好像行尸走肉一樣,賺再多錢吃再多補品都沒有用!”嘉瑪訴苦道。
她坦言,當年入行是被空姐可周游列國的憧憬所吸引,一做7年,現在要轉行也非易事,“不可能轉行過回朝九晚五,因為已經習慣了多假期但密集的工作模式。”而對45歲退休年齡的限期,嘉瑪坦言常為未來煩惱,經常憂慮將來可換什么工作。
很多人以為做空姐容易在機上“釣得金龜婿”,但樣子不俗的嘉瑪卻仍是單身一族。“我們好難認識男子,雖然接觸的乘客很多,但真正認識的卻很少,而且大部分空姐都很獨立,不需要依賴男人。”
降格為“有翼的侍應”
同樣在航空公司工作的關笑華屬老臣子級,工作了近30年,又是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她真正體驗了空姐多年來的辛酸崎嶇路。
“以前做空姐真的令人羨慕,上班好像去玩一樣。”關笑華說,從前飛機班次不如現在頻繁,即使東南亞的短程航線都逗留四天三夜,“我們一到機場便叫司機用車載我們去芭堤雅玩,玩夠兩天才施施然回港。”
但時代變了,她說現在一天已有5班機飛曼谷,不是即日來回便是連飛多個站,想忙里偷閑玩幾日,簡直是異想天開。
她還指出,外界對空姐的尊重和“仰慕”之心漸漸降低:“我曾在巴黎免稅店被店員稱為flying waitress(飛行侍應),以前做空姐好有優越感,但近年就被人叫做waiter with the wings(有翼的侍應),很無奈!”
不過最令關笑華無奈的是不增反減的薪酬。現在她公司的薪酬被公認為全行最低,1996年以后入職的空姐并非月薪制,而是以飛行時間時薪約100元來計數,多勞多得。
辛酸不為外人知
某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潘蕓妮則說:“現在很多航線都是短途飛行,大部分是當天往返,或者只逗留一兩晚,工作比較累人,而且也難有私人生活;就算當日可以返回,空姐們因為怕航班延誤,也不敢與人約會。”
潘蕓妮說:“跑短途飛機動作一定要快,當飛機起飛后還在爬升時,空姐們就要把餐車拉出來開始派飲品,否則飲品還沒派完,飛機可能就到站了。但最慘的是飛機上經常人手短缺,很多人以為做空姐只是派發餐飲,沒什么事做,其實我們最重要的角色是‘開門’,萬一有什么意外發生,一定要及時把逃生門打開,能不能救到人就看我們空姐的了。”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主席Card說,現在各航空公司的流失率都很高,所以公司經常要搞大型招聘會吸納新血。“我們經常要離鄉背井,即便是有親友離世也不能換班,這些辛酸外人又怎么會知道呢?”■
(姚慕蕓薦自《海外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