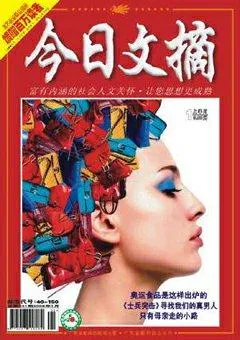有多少草可以在城里扎根
草是城市的匆匆過客,只有一小部分被城市留下來,大部分被拒之城外。
草坪是草在城里可以名正言順扎根的地方。能夠生長在草坪里的草都是草中的貴族,渴了有水喝,餓了有飯吃,頭發長了有人梳理,身上臟了有人打理。但貴族也有貴族的規矩,自然不能像長在鄉村的草那樣爭噴競涌放任自如,它們經常會被這條條那框框束縛著,不能越雷池,也不敢越雷池。
旁逸斜出、鶴立雞群是不可能的事。它們必須按照城里人的意愿去生存,一個個整整齊齊地站成一片,像一大群被封了口的小學生。值得稱道的是,得地利享人和的它們姿態優雅,色彩華麗,鋪排出一面遮天蓋地的綠綢,說不出有多么詩情畫意。
狗改不了吃屎,牛改不了吃草。在鄉村與草廝混了十幾年的我,每望見這樣一片碧綠的草坪,雖不能像一頭牛一樣猛撲過去,大塊朵頤,但我可以在綠草中徜徉一陣,也是一種滿足。你經常會看到一個人背著雙手圍著草坪轉圈,像一個老農心滿意足地看護自己的糧囤,那個人往往就是我。
草在鄉下用途廣泛。一是喂牲口。我小時候干得最好也是最多的活兒就是割草,喂牛喂豬,溝旁渠畔蔓延的野草豐收著我的另一塊莊稼地。二是作柴草。秋末,把它們連根拔起,塞進灶堂,就是一把好火。三是代替糧食救急。青黃不接或災荒之年,茂茂密密長得興旺的野草就是救命糧。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有誰沒吃過野草呢?
而草在城里主要是為了養育城里人的閑情逸致,因此更多的草被驅逐在城市外,它們的葉子不好看,也開不出好看的花朵,對城市來說就不是點綴,而成了丑化和負擔。
馬馬菜、乞乞牙、灰灰菜們偶爾也會進入城里人的菜籃子,那是城里人吃膩了魚肉,想換換口味。熱潮一過,很快無人問津。
但再惡劣的環境也不能阻擋一株草的生長。
高高的墻根,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必生長著一叢叢野草,只要能得到一點兒濕潤和泥土,就在這里安家落戶。葉嫩嫩的,莖細細的。在低谷中求生存的它們,更有一種攀登峭壁的勇氣。夏天到了,它們羞羞澀澀地綻放出一朵朵茸茸的小花,悄悄扮亮了一方天空。
城市的人行道喜歡鋪著彩色的地磚,夏天的雨后,常會從縫隙間伸出一兩株細細的草來,處在地磚夾縫中的它們,一方面要擺脫磚的壓迫,一方面要承受高溫的炙烤。惡劣的環境使得這些草一律是細細的莖軟軟的身軀,因為長得太瘦弱,我常常不能準確地叫出它們的名字,也許是灰灰菜,也許是狗尾巴草,只是沒等它們長粗自己,表現自己,就消失了,不是死于干旱、高溫、冰雹,而是毀于人手:或是被行人踩碎莖葉,或是被城市的養護者一把除去。
它們明知自己的結局不過如此,但第二年這時候,還會不屈不撓地頂開磚塊,伸出腰桿,一株,兩株……長一回,黃一回,再長一回,再黃一回。沒有鄉下那種漫坡漫野的恢弘氣勢,沒有那種生命的放縱與狂野,只是默默地、不聲不響地獨自長成一簇自己的風景———被不被人關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在生長,即使死去也絕不是孬種。望著它們的身影,一瞬間我竟莫名地感動起來,覺得它們真偉大。
我在城市的街頭會碰到許多像草一樣在城里謀生的農民,他們拘謹著,勞作著,“一鎬一锨”地,承受著千辛萬苦,試圖從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夾角中求得一席之地。只是最后又有多少能扎根城市?
我們的城市現在愈來愈干凈漂亮,而草也就越發地沒有了立足之地。
草一輩子扎根一個地方,無怨無悔,不言不語。假若城市沒有了草,也許不會有什么缺憾,我卻覺得,少了一道能刺激我們靈魂的風景。■
(曹庚薦自《都市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