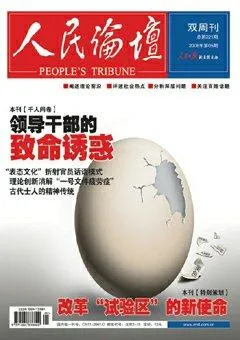古代士人的精神傳統(tǒng)

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是我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格,正是由于有這樣的品格,他們不屈不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
中國古代士人具有強烈的社會責(zé)任感。他們?yōu)樯鐣倪M步,文明的傳播,科技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士階層產(chǎn)生于社會動蕩、政治斗爭尖銳的戰(zhàn)國時期
在商周時期,士的含義十分廣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級制度上,士是各級貴族的通稱,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個等級,處于宗法貴族等級序列的最末一等。漢人賈誼說:“古者圣王制為列等,內(nèi)有公、卿、大夫、士……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許多士在諸侯公室中擔(dān)任職務(wù)。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職之人”。
在士擔(dān)任的職事官中,可以看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態(tài)。當(dāng)時,在王室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禮儀、占卜、記事等活動的文職官員,稱“作冊”、“巫”、“卜”“祝”、“史”等。他們掌握文化知識,具有文人的特征。不過,與春秋戰(zhàn)國活躍的士階層相比,他們不是獨立的知識群體,其知識還沒有形成理論學(xué)說,沒有達到以知識為資本與社會進行交換的程度。商西周時期,宗法分封制保證了士等級的穩(wěn)定和不斷擴充,嚴格的等級制度又使士縱然有知識和技能也無法充分施展,“士之子恒為士”,從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識主體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士擺脫了宗教等級的束縛,獲得了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躍的階層。
這時,士的身份已不再世襲,不再是貴族的一部分,那些通過刻苦讀書,擁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為士。如蘇秦,家境貧寒,為改變生活狀況,他決心努力學(xué)習(xí),增長本領(lǐng),讀書累了,甚至“錐刺股”,終于學(xué)有所成,后來到各國游說,受到歡迎,曾擔(dān)任六國國相。
由于士階層產(chǎn)生于社會動蕩、政治斗爭尖銳的戰(zhàn)國時期,他們所思所想多為針對天下如何統(tǒng)一、國家如何富強、社會如何治理等問題,所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成為士人的明顯特征。
許多士人是懷著對“道”的追求和憧憬而從政的
古代士人具有很強的歷史使命感即積極的入世精神。孟子說:“如欲平治天下,當(dāng)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論語·泰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言代表了廣大士人的心愿和呼聲。古代士人把參與國家政治視為自己的“天職”,把“治國平天下”當(dāng)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們關(guān)心社會現(xiàn)實,“風(fēng)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參加國家管理,清正廉潔,執(zhí)法嚴明,成為賢相、清官,至今為人稱頌。有的人雖遭貶謫,仍懷報國之志;許多人在國家、民族危難之時,挺身而出,從容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充分體現(xiàn)了士人中優(yōu)秀分子的高度社會責(zé)任感和英勇獻身精神。
戰(zhàn)國時期,許多士人是懷著對“道”的追求和憧憬而從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就是“從道不從君”,仁義之道重于君主之位,應(yīng)該用道對專制君權(quán)加以節(jié)制。他們在國君面前敢于據(jù)理力爭,甚至指斥國君的不道行為。孟子周游列國,常常尖銳地批評國君,他站在維護仁義之道的立場上,毫不留情地指斥了梁惠王“率獸而食人”,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他的責(zé)備常常使得國君無言答對,“顧左右而言他”。孟子的行為不僅顯示了士人對政治的關(guān)心,還表明孟子具有可貴的社會良知。他以社會擔(dān)當(dāng)為己任,關(guān)注民生,反對戰(zhàn)爭,仗義直言,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優(yōu)秀品質(zhì)。
從賈誼上疏和葉伯巨之死看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來源于讀書人對社會、民族、國家前途深切的關(guān)懷。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古代士人的憂患意識常常表現(xiàn)在對事物的發(fā)展具有預(yù)見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穩(wěn)定時期,他們見微知著,察覺到潛伏的危機和面臨的困境,表現(xiàn)出“超前意識”或“危機感”。
比如漢文帝時,賈誼上疏,針對匈奴強大、諸侯勢力膨脹等問題,認為,漢王朝像病足一樣,“一脛之大幾如要(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漢書·賈誼傳》)。當(dāng)時,社會處在平穩(wěn)發(fā)展階段,賈誼之“危機感”似乎是危言聳聽,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預(yù)感是對的。
明初,地方教官葉伯巨上書朝廷,認為朱元璋分封諸子為王將來會造成“尾大不掉之勢”,難免骨肉相殘。果然,朱元璋死后,發(fā)生了爭奪皇位的戰(zhàn)爭。但在當(dāng)時,朱元璋卻認為他的話有蓄意挑撥離間之嫌,不少大臣也認為他無中生有,葉伯巨被抓,死于獄中。
很多士人具有知識階層所特有的對問題觀察的敏感性,能比較清楚地發(fā)現(xiàn)某種趨勢的發(fā)展前景。然而,在現(xiàn)實中,超前的危機感往往不為當(dāng)政者認同,甚至被懷疑別有用心,這就釀成了許多個人的悲劇。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強烈歷史使命感
在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驅(qū)動下,中國古代許多知識分子雖身處逆境,但堅韌不拔,正信彌堅,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而繼續(xù)奮進。司馬遷被漢武帝動腐刑,蒙受了奇恥大辱,雖然處于痛不欲生的境況,但是他寫作《史記》的決心沒有動搖,他用歷史上那些處于逆境的先賢激勵自己,以超人的毅力,最終完成了這部偉大的史學(xué)名著。
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是我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格,正是由于有這樣的品格,他們不屈不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甚至甘愿以身殉道。明朝末年,宦官專權(quán),朝政腐敗。東林書院的主講顧憲成帶領(lǐng)志同道合之士與宦官惡勢力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被稱為東林黨。由于東林黨人的斗爭矛頭直指腐敗朝政,熹宗時,被閹黨頭子魏忠賢殘暴鎮(zhèn)壓。東林黨精神的最大特點是關(guān)注社會政治,憂國憂民,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可貴精神,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士人的依附性,使他們的知識價值取向和人格的獨立性都大打折扣
應(yīng)該看到,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和參政意識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強化了做官意識。在專制的家天下時代,士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過入仕為官來實現(xiàn),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官員的名額有限,于是,無數(shù)儒生士子擁擠在“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狹窄通道上,為入仕,他們刻苦攻讀,皓首窮經(jīng);為保住官位,他們爭寵獻媚,甚至互相傾軋,最終成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馴服工具和掌中玩物。
其二是重政治,輕科技。古代士人迷戀仕途,熱衷參政,加之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輕視自然科學(xué),認為科學(xué)技術(shù)不過是“器”,是“藝”,是等而下之的東西,因此,中國古代無官職的自然科學(xué)家、發(fā)明家的社會地位不高,他們至多在正史的“方伎傳”中留幾筆,而不能與政治家相提并論。這種觀念造成了中國古代士人知識結(jié)構(gòu)不合理,更造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發(fā)展緩慢。
其三,古代士人缺乏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他們只能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依附體而存在,如果不去依附統(tǒng)治者,不僅沒有社會地位,甚至連生計都成問題。士人的依附性,使他們的知識價值取向和人格的獨立性都大打折扣,保持正直的品格和社會良知都有相當(dāng)?shù)碾y度。(作者為南開大學(xué)教授)